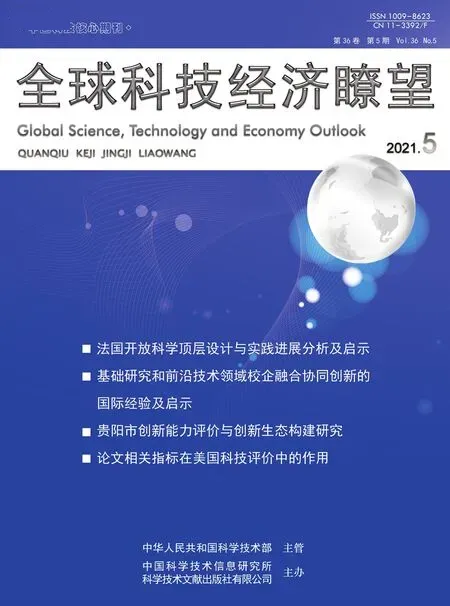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薛 姝,何光喜,张文霞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促进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是各个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和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产学合作有多种形式,如果把传统上大学与企业间以“技术转移”为主要目标,一事一议性、临时性和短期性的合作称作“产学合作1.0”版,那么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大学以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为主要目标,依托项目、机构和人才等平台,在战略和组织层面上建立的深度融合、长期协作的合作研究关系,可被视作“产学合作2.0”版,主要形式是校企融合协同创新。当前,中国已经有少数领先科技企业开始探索和布局“产学合作2.0”,但大多数企业与大学的合作仍然停留在“产学合作1.0”阶段,对在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与大学合作的需求不足、基础薄弱;政府在国家科技计划、科研组织和人才计划等层面也有推进产学融合协同创新的探索,但对“产学合作2.0”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许多深层次理论议题尚有待澄清,若干重要的潜在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规范。本文在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分析及对中国相关调研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推进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校企协同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及国际经验
从国家创新系统视角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创新体系都包括企业、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三大创新主体,各国在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界限已经成为主要趋势,创新主体之间正逐步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在创新的各个阶段建立相互支持关系[1]。协同创新是将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合作创新的过程,从本质上超越了以往各种产学二元创新、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创新等创新模式[1]。校企融合协同创新指高校与企业通过组织和战略层面的实质、深度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创新活动。它是通过整合高校和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不同于传统上政府主导下大学为产业提供人才或技术服务,或大学教授与企业之间私人层次上的合作,从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下游环节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都是校企融合创新的范围。归纳国内外实践,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校企融合协同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1 共建合作研究机构
共建合作研究机构指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高校和企业共建研究机构,协同开展研究创新活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有此类合作形式。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自1973年开始,支持组建了大批“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Research Center, IUCRC),通过促进产业界创新主体、世界级学术团队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密切和持续合作,产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加强基础研究的影响力[2]。合作研究中心一般隶属于大学,企业作为会员加入并交纳会员费(会员以企业为主,占80%,其余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单位等);经费以企业缴纳的会员费为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大学提供资助;一般根据企业需要开展研究活动[3,4],研究领域集中在前沿的工程和应用科学领域,包括先进电子技术、先进制造、先进材料、生物技术、民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境、健康与安全、信息/通信/计算科学、传感和信息系统、系统设计与仿真等[5]。2001—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支持建立了76个合作研究中心,2017至2018年度,共有1 164家会员单位[4]。合作研究中心中影响较大的有麻省理工学院复合物加工研究中心、加州大学集成传感器研究中心等[6]。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支持在大学里组建“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ERC),针对产业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把基础科研与工程系统需求结合起来,同时培养产业所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工程研究中心经费最初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和会员费构成(会员既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有大量中小企业,此外还有地方政府等非企业会员),此后逐步实现自收自支;几乎覆盖了所有工程学领域,其中前沿电子通信和生物医学类工程研究中心占了近4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设立的工程研究中心已达数十家,影响较大的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微电子机器人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通信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和哈佛大学系统研究中心等[6]。在最新的量子信息科学等领域,美国也通过公私联合融资等方式,支持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建研究机构。
日本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推动在大学设立“(地区)共同研究中心”,配置专任研究人员和通用研究设备,除与企业共同开展研究或接受企业委托研究外,还对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咨询培训[7,8]。还有不少大学或国立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组建了财团法人性质的联合研究机构,如东京大学尖端科技研究中心、电子项目共同研究机构、新一代电子计算机共同开发机构、国际超导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等[8]。
1.2 科研项目合作
科研项目合作指校企间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开展合作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委托研究”,即企业提供研究经费,委托大学以科研项目的方式开展研究,企业一般不派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研究;二是“共同研究”,即大学研究人员和企业研究人员以对等的身份,共同确定研究课题和方案,共同开展研究,经费可能来自企业、双方共同分担或第三方。
在美国,大学通过合同方式接受企业委托开展研究活动十分普遍,研究成果专利权一般归大学所有,但企业有优先购买权;大学和企业对某一课题开展专项联合研究(各自派出研究人员、共同承担经费、共同制订研究计划)也很常见。此外,美国财政科技计划项目也会鼓励支持企业与大学共同承担研究项目、开展研究,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SBIR)支持信息技术、材料、能源和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领域小企业有商业化潜力的研究项目,项目可以由企业单独执行,也鼓励小企业与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实施;“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STTR)则是强制要求小企业和大学等非营利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研究开发;“先进技术计划”(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ATP)则是通过项目支持生物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与化学以及制造技术等领域具有较高风险和外溢性的共性技术开发与商业化,项目可由单一企业(既有大企业也有中小企业)单独承担,也可由企业联合或与大学等共同承担。为鼓励大学、联邦政府研究机构与企业的联合研发,美国还通过《拜-杜法案》《国家合作研究法》等,确立知识产权分配原则,建立联邦实验室与其他政府、大学及企业间的合作研发协定(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CRADA),放松对合作创新的反垄断管制等[9]。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委托研究制度”和“(国家与民间)共同研究制度”。其中,委托研究制度允许国立大学和科研机构接受企业委托开展研究;共同研究制度允许国立大学和科研机构接受企业研究人员,与企业协商选择研究课题,使用双方研究设施共同开展研究。共同研究的课题一般集中在公用性较强且所需经费较大的领域(如基础性、先导性领域以及防灾、安全、医疗等公益领域),所需经费一般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取得的科研成果则由国家和企业共有。此后,日本企业委托大学以及与大学共同开展的科研项目迅速增加,成为产学合作研究的重要形式[10, 11]。
1.3 人才交流合作
人才交流合作指校企之间以研究人员的交流为纽带,实现科研知识和成果的转移与流动。例如,美国在大学与企业之间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旋转门”机制,研究人员可以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实现无障碍的人员流动。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学术休假”制度到企业开展研究也日益成为潮流,如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教授利用学术休假机制在“谷歌云”担任首席科学家职务长达两年时间,目前虽已重返斯坦福大学,但仍兼顾在谷歌的工作,从人才流动的角度强化了学术界与产业界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联系。
日本在国立大学建立了“受托研究员”制度,允许企业派遣研究人员到国立大学接受培训和进行研究,以提高企业人员研究水平[8]。从2004年开始,日本在充分发挥国立大学、研究机构和民间企业三者互补性的基础上合作设立协作研究生院,为校企双方研究人员的有效交流提供了条件[12]。
1.4 其他形式
在美、日等国,许多大企业还通过与大学签署长期合作协议、为大学提供巨额科研资助,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持。企业向大学捐赠研究讲座或研究部门,或设立由企业支付薪金的教学研究职位,也都是校企融合协作的常见形式。
2 当前中国推动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主要做法
中国重视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创新,把产学研合作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从政策角度,依托国家重大专项、国家实验室等平台进一步鼓励大学与企业形成协同战略体系已经有所实践。
2.1 依托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引导和支持企业与大学共同承担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项目。例如,在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协同组织全国范围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不同类型的研究主体全力攻关,大力鼓励和支持具有良好基础的企业协同高校联合开展攻关,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任务部署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2.2 依托科研机构和组织
通过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等方式,推动校企融合协同创新。如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已依托企业建设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关键技术国际发展前沿,有效组织应用基础研究和竞争性前沿共性技术研发,取得了高铁、大飞机等国家重大装备和重点工程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2.3 加强对校企协作人才的培养与支持
通过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支持高校和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施以来,加大对企业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等的支持,对来自企业的人选适当放宽推荐条件。加强针对企业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研修。在政策上明确允许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兼职兼薪,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或离职创业,鼓励、激励科研人员转化科研成果。
2.4 营造有利环境
完善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实施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全流程知识产权管理,引导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加快推动重点任务,促进成果转化。制定出台《关于新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相关政策,重点支持培育壮大主体规模、强化政策完善落实、加大财政金融支持等。
在前述政策推动下,发达国家主要的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形式在中国也有所发展。在共建合作研究机构方面,中国也有类似机构,如清华大学与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09年共建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并于2020年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开展暗物质粒子探测科学研究提供国际领先的基础研究平台[13]。近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成立的许多新型研发机构中,不少就是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的。在科研项目合作方面,企业以项目方式委托大学进行研究或技术开发,或与大学共同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已经是常见的合作形式。人才交流方面,也有类似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如研究机构在企业设立院士工作站,企业聘请大学或院所研究人员提供研发支持,以及企业和高校共同培养研究人才等。
3 当前中国校企融合协同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高校和企业是创新系统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加强这两个主体的深度协同,有利于发挥“1+1>2”的创新效果。当前中国大学与企业各种形式的合作已经比较普遍,一些高水平研究性大学纷纷建立校企平台,积极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但大多数校企融合协同创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合作领域集中在技术咨询、成果转化(如技术/专利转让)、委托开发等研发链条后端,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等研发链条前端的较少;二是合作方式以一事一议的临时性、浅层次合作为主,在项目、组织和战略层面的长期性、深层次融合协同创新合作较少。具体而言,仍面临以下突出问题和障碍。
3.1 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能力不足
从创新主体创新能力角度来看,多数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与大学融合协同创新的基础薄弱、动力不足。调研显示,大学普遍认为产学融合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企业有明确的需求和意向,就比较容易把合作推向深入持续的层次;反之就很难。虽然中国也出现了华为、阿里等少数在科技发展水平上进入“无人区”(处于“并跑”或“领跑”阶段)、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有强烈需求的领先企业,但大多数企业的科技发展阶段仍以“跟跑”(技术跟踪)为主,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需求并不强烈,对与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合作研究也缺乏相应的人才和资金基础。因此,大多数校企合作仍处于研发链条的下游,主要局限于具体的产品和工艺研发创新,缺乏长期可持续、不求短期回报的战略性合作,更谈不上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
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校企合作从研发链条下游的浅层次合作,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融合协同创新,需要一个长期逐步演化的过程。目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开展校企融合协同创新所需的内在需求、经济实力和研发团队支撑,这主要是由大多数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可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逐步推进校企协同创新。
3.2 创新主体内外部管理制度限制
从创新主体内外部管理角度看,国有企业受制于现有考核指标等硬性要求,对校企协同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热情大打折扣。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作为我国经济和产业技术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的独立研究以及校企融合协同创新方面具有更好的科研基础和潜力。但调研中有企业反映,现有的国企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审计监察制度体系,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支持和激励不足,制约了其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14]。例如,现有针对国企的考核评价过于注重产值和利润指标,而相对忽略其创新绩效和创新投入指标;监察审计等部门在监督角度也往往要求国企研发投入在短时期内取得可见收益,这不利于企业进行长期的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周期长,成果产出不确定性大,要推动国企成为这些领域的研发生力军,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国企的相关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3.3 协同创新政策环境不完善
从创新政策环境角度来看,校企融合协同创新向基础研究领域延展的趋势已经出现,但尚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华为等少数领先企业,已经从自身需求出发,与北大、清华等高水平高校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框架,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布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校企融合协同创新[14]。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以及华为这样的领先企业的逐渐增多,产学研合作也将从原先的注重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逐步迈入融合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新阶段。
如前文所述,相关部门虽然在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组织、人才计划等方式促进校企深度合作方面有所探索,但针对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有效政策支持工具仍然不多。此外,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科研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考核评价等管理制度也相差甚远。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事、经费管理制度以及科研组织方式等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与企业融合创新的需求。
3.4 协同创新理论研究有待深入
从创新体系理论研究角度看,产学融合协同创新的深层次理论问题仍有待研究和规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模式的变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问题也相应产生变化,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展。近年来,一些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组建,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生产、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科技企业孵化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提供了产学深度融合的有益案例,对这些产学融合创新的新模式以及相应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目前尚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
此外,美、日等发达国家经验显示,产学融合协同创新并非只有“正功能”,也有可能带来相应的“负功能”,如:因企业资助导致的“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学术自由”传统及研究公正性、客观性的侵蚀问题;因校企、企企合作研究带来的潜在垄断问题;国家财政支持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边界问题(在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摩擦加剧的今天尤其重要),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相应的深层次法律问题,美、日等国一般都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予以规范。我国目前对这些问题尚未给予充分重视,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也相对滞后。
4 启示与建议
为进一步促进大学与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结合国际经验的启示,提出如下建议:
(1)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坚持以企业为主导、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方针。
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创新平台建设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增强企业的作用和参与度。特别是在重大产业共性技术、前沿技术的联合攻关以及重大、前瞻性、应用性基础研究方面,要坚持企业的主导地位,围绕技术和产品的可应用、可产业化、可市场化目标部署和组织创新力量和资源。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等财政手段,精准鼓励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的产学合作研发投入。建议研究制订并及时完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清单,对该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激励。
(2)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和长效合作机制。
扭转大学和院所在科研人员考核、职称和岗位评审中的简单量化评价方式,支持、引导高校和院所调整优化评价激励方式,鼓励科学家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凝练科学问题之外,从企业和产业发展中寻找研究方向、研究题目和研究灵感,把企业技术问题转化成科学问题。
鼓励大学与企业分享研究资源和知识、共建孵化器、联合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加大联合培养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力度。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或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建议设置校企(院企)合作奖励基金,以支持和鼓励那些在校企融合协同创新方面做得较好的高校、院所、企业和团队持续开展高水平、长期性的战略性合作。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以及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的部署中,优先支持具有良好产学研合作基础的企业和高校,鼓励联合攻关,提升协同创新效果。
(3)优化协同创新环境,加强政策、部门协调,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投入及校企(院企)协同创新。
加强科技部门、国资管理部门、审计部门以及纪检、巡视等部门之间的协调,统一有关政策口径,给予国有企业开展基础研究较大的宽容空间和相对较长的考核时间段。对企业效益的考量应充分考虑无形的科学知识产出效益以及国家和企业发展的战略需要和长远影响,克服唯产值和利润等实体性指标的倾向。
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考核评价制度,把科技创新与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等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把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费按照一定比例折算作为利润的一部分,以激励企业加大研究投入。
(4)鼓励和支持新型产学融合协同创新载体和平台发展,完善法律制度,规范融合协同创新行为。
积极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通过高端资源链接、高峰论坛等方式,加强各类创新主体的交流合作;支持面向企业为主的新型产学研融合创新载体建设,进一步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大学科学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创新载体建设,形成创新全要素集聚、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区域创新体系。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形成一批面向市场和应用、引领和支撑地方产业技术发展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平台;支持发展较好、科研实力突出的新型研发机构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技术联合攻关项目,建设校企联合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加强对产学融合协同创新法律问题的研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管理和学风作风建设,保障产学融合协同创新中的“学术自由”,避免资本介入对研究客观性、公正性的负面影响;防范产学合作带来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问题,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国际争端与摩擦。■
-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的其它文章
- 德国构建科研大监管体系情况研究
- 论文相关指标在美国科技评价中的作用研究
- 征稿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