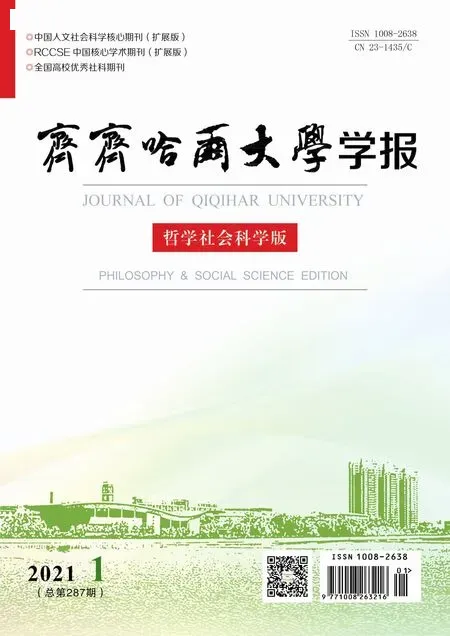地缘因素与周秦两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
孙 俊, 张晓梅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问题。[1]从理想的圈层政治地理结构[2]到现实的政区划分[3],其中都有深刻的族群因素存在。而且,中国古代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主流态势,是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夷之辨”民族观影响之下进行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族群分布空间与政治地理空间具有明显的重合,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存在明显的“内地区”与“边疆区”结构性特征。[4]在此种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华夏群体如何建构统摄“四夷”群体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即“中国”如何与“天下”重合,并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始终是王朝国家建构、治理的重大问题。[5]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必然涉及到不同族群的政治空间整合问题,地缘因素也就成为历朝开边、治边的主要因素之一,叶自成、[6]马大正、[7]方铁[8]等学者对此问题已多有阐释。地缘因素影响开边、治边,则必然对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也会产生深刻影响。西南地区(在大一统王朝国家层面上,本文涉及到的秦汉“西南地区”区域范围当前有争议,本文认同并采用王文光、[9]朱映占[10]的意见,即“西南地区”包括汉中、巴蜀、西南夷地区)是“中国”与“天下”重合问题涉及到的重要区域,且自宋以来郭允蹈、[11]顾祖禹、[12]刘逢春、[13]萧映朝[14]等就其不同区域的地缘意义及影响进行过较详的讨论。本文的旨趣,则在分析和讨论地缘因素对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所谓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指的是不同族群分布、活动、治理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政治空间,是王朝国家疆域建构、王朝国家认同表达的重要甚至核心内容之一。[15]
就周秦两汉西南地区的情况而言,其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包括地域性和政区性两种类型。总体上,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国家建立前,不同族群间的政治联系缺乏政治上的大一统基础,但又有“天下”这一共同的空间,族群政治地理空间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地域间关系,其表现形式是“一点四方”结构。[16]秦汉大一统王朝国家建立后,有限“天下”国家观念形成,相应的王朝疆域观念产生,[17]族群间的政治联系也就具有了大一统政治空间基础,且直接反映在是否政区化的政治地理空间层面上,其表现形式是“中心—边缘”结构。
一、西周至战国前期汉水地缘关系与地域性族群政治地理空间
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族群演进“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元,虽说其时西南地区族群演进是自在地进行的,但不同区域间的族群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联系。在此层面上说,西南地区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应当是一直存在的。不过,在地缘政治的层面上,考虑到大一统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时,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可能不晚于商周之际。夏商时期,从有限的出土文字材料来看蛮、夷、戎、狄的族群名称虽已出现,[18]204但使用并不稳定,也未完成蛮、夷、戎、狄与“四方”的配位,而且夷夏在文化上也没有二元性的关系,[19]42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整齐划一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西周春秋时期“夷夏之防”观念的不断强化,以及与之并行的蛮、夷、戎、狄与“四方”搭配结合的成型,[16]则意味着整齐划一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可能性。
具体到西南区域来说,西周春秋时期,其族群身份也有一个明显的“方位化”过程。一般认为,西南族群的“方位化”发生于战国中期,如司马错将蜀视为“西辟之国”。[20]102东汉时期班固将巴、蜀、广汉视为“南夷”,[21]卷二八:645也是西南族群“方位化”的表现。不过,西南地区族群在大一统观念层面上“方位化”的最早情况,应是《尚书》中所称的“西土”问题。商周之际,武王欲东征,曾动员西部“八国”参与,“八国”包括庸、蜀、微、髳、羌、彭、卢、濮,被称“牧誓八国”。“牧誓八国”群体并未被称为“南夷”或“西戎”,而是被称为“西土之众”、“西土之君”、“西土之人”等。[22]卷一:182-197“牧誓八国”被称为“众”、“君”、“人”而不是“蛮”或“夷”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似乎反映了当时“夷夏之防”在西南地区的淡化。不过,这种“淡化”可能存在地缘因素的影响。钱穆曾指出,周人立国以西部为根基,向东扩展其政治空间。[23]45与周人此种立国态势有关,“牧誓八国”是周人东征依靠的力量之一,在《尚书》之《仲虺之诰》《泰誓》《牧誓》中均提及了“牧誓八国”。
“牧誓八国”为周人立国及周初治理“天下”的依靠力量,则称其为“夷”或“戎”便不太合适。不过,“牧誓八国”在周人立国过程中的地位,也并非十分重要。在前述提及的“牧誓八国”材料中,“牧誓八国”均被列于司徒等职官之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清人张邦伸在讨论前文已引述过的“西土之众”、“西土之君”、“西土之人”时有“称之曰人,不以诸侯待之”的解释,[24]卷一五:862也可见“牧誓八国”的特殊性。此外,上博楚简《容成氏》篇记载了武王东征的过程,[25]89-90其中没有提及“牧誓八国”的任何一国,也颇为值得注意。李零认为,《尚书》所载情况与《容成氏》所载情况的差异反映了周人立国过程中西部族群参与性的逐步降低问题,即“牧誓八国”的重要意义只存在于周人构筑周人政治地理空间的阶段。[26]
与李零的解释相应。周人立国后,“牧誓八国”也并未进入周王朝的核心地带,而是边缘地区。春秋后期,诸侯竞相征伐,昭公有巴、濮、楚、邓为“吾南土”的说法。[27]卷四五:1268所谓“南土”,是“四土”之一,已是王朝边缘地带。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南土”中的巴、濮,可能并非蛮夷群体。例如,其中的巴指的是宗姬之巴,[28]是分封于巴地的华夏群体,与史籍中作为蛮夷的巴国群体并非同一群体。
巴、濮为周王朝政治疆域的极限,其西、其南则为蛮夷区。在华夏与蛮夷之间的边缘地带,西周开始即有同姓封国“以藩屏周”。[29]242与“以藩屏周”的目的相关,西周建立了“监之于外”的“应监”之制。[30]274-276“以藩屏周”及“监之于外”的“应监”制度实施可视为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初步建构,因为西南地区族群与周集团的区分不再仅体现在文化上,还体现在政治地理空间上,而且是有区隔性的政治地理空间。
西周“应监”实施的西限应在汉水一线,前述涉及到的“西土”、“南土”诸国,大致也以汉水一线为界。周以汉水一线为“应监”的西限,实与汉中的地缘因素有关。关于汉中的地缘关系,蜀汉时期黄权、杨洪等曾谓汉中为“蜀之股臂”,“益州咽喉”;[31]卷四三:1043宋人郭允蹈也认为南郑是“蜀之扞蔽”,并指出汉中为四争之地;[11]9清人顾祖禹、[12]2660今人刘蓬春[13]也曾得出与郭允蹈相似的结论。这些观点清晰地阐明了汉中地区的特殊地缘意义,但尚需注意到这些观点大多反映的是大一统思想下的汉中地缘关系,特别是大一统王朝国家下的地缘关系。而在西周春秋时期诸国林立的态势下,汉中的地缘关系主要是“蜀之扞蔽”的问题,即汉中是屏藩西土、南土蛮夷群体的重要区域。
汉中在地理和制度的层面上均具有屏藩的功能,则相应的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也已建构起来,形成了“五方之民”视野下以汉中为分界的“华夷”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此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因主要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但缺乏大一统王朝国家政区性的政治地理空间基础,可视为地域性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与后世形成的政区性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二、战国中后期巴蜀地缘关系的凸显与巴蜀华夏化
汉中地区在春秋时期尚能为周王室所控制,但随着楚文王时期楚国的西拓,汉中遂成为秦、楚、巴、蜀间争夺的焦点。楚文王初,楚国向西扩展疆域,导致江汉间小国“皆畏之”。[32]卷四○:2047此事件的发生表明周王室对汉中地区的控制力已大为减弱,周王室也未强制制止楚的西拓行为,而是对楚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32]卷四○:2048战国中期,秦楚开始试图控制巴蜀,史籍有“昔巴、楚数相攻伐”的记载,[33]卷三四:405秦则在惠公十三年取得南郑。[32]卷五:254不过,在秦定巴蜀之前,秦、巴、蜀、楚的相对平衡格局长期存在,汉中天险为秦、楚、巴、蜀所共享和争夺的区域。例如,周显王时(前368-前321)蜀已有褒斜、汉中西部部分地区,并继续与秦争夺汉水谷地。[34]卷三:187-188楚威王(前339-前329)也曾提到,秦素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20]509战国中后期,楚、秦、巴、蜀均对汉中有充分的关注。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秦定巴蜀后,汉中地区的地缘平衡关系被打破。秦定巴蜀时发生过著名的司马错与张仪之争,司马错认为巴蜀地区具有劲卒、战船的优势,加之有水道可通往楚地,“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34]卷三:132秦惠王十四年(前311)关东诸国连横以弱秦,张仪就以地缘因素劝说楚王与秦结盟,因为秦由巴蜀攻楚只需三月,而关东诸国救楚则需半年才能到达。[20]514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0)秦攻楚汉中地并置汉中郡后,[32]卷五:263更使楚完全丧失了巴蜀、汉中屏障,形成了秦由巴蜀沿长江“五日而至郢”,由汉中沿汉水“四日而至五渚(诸)”的钳形攻楚态势。[20]129而在汉中、巴蜀的战略地位方面,于秦而言巴蜀更为重要。例如,秦惠文王十三年秦已有汉中之地,但却长时期与楚相争,张仪与甘茂均建议将汉中归于楚以换取楚与秦的结盟,只不过在何时归汉中于楚的问题上有异议,[20]106可见汉中确实重要,但其首要意义在于楚而非秦。比较之下,巴蜀对秦国更为重要。
秦定巴蜀后大力经营巴蜀地区,包括大规模移民、重新营造城镇、改革政治制度、大规模兴修水利系统等举施,最终形成了“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的态势,[32]卷七○:2776使巴蜀地区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战略空间。与巴蜀地区战略空间的重要性有关,秦定巴蜀后即大力推进其华夏化进程,在汉人杨雄、晋人常璩和左思、唐人卢求等看来,巴蜀地区文化的转型及繁荣均与北方移民有密切的关联。[35]而巴蜀之所以成为接纳大量北方移民的区域,也与其地缘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史籍说“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之”,[32]卷五:403“道险”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巴蜀远离关东且能为秦所控制。
族群结构的变动是巴蜀地区华夏化进程的主要指标,但这一进程的具体情况史料未详。由现有的史料和考古材料来看,巴蜀地区的华夏化进程在族群结构的层面上受北方移民、土著群体华夏化的双重影响,且土著群体的华夏化影响意义要更为重大。秦国时期,入川的秦民及关东群体大多集中分布在交通沿线,[36]且真正的北方移民群体数量应是较为有限的。两汉时期,战争及自然灾害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北方群体入川,且入川的汉族群体向成都平原中心区域移动,[37]901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汉族分布地域。不过,由砖室墓、崖墓分布格局演变及其数量的情况来看,巴蜀地区的华夏化更多地是由土著群体的华夏化推动的。[38]
巴蜀地区的华夏化可视为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过渡时期。一方面,秦定巴蜀后虽实现了巴蜀地区的郡县化,但却缺乏完整的大一统王朝国家政治地理基础,且因巴蜀地区仍处华夏化进程中,西南地区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仍然主要是“一点四方”的模式,只不过巴蜀与后来所称的西南夷地区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华夷”之分;另一方面,巴蜀地区的华夏化,则使巴蜀地区开始脱离“蛮”、“夷”身份,逐渐被视为华夏之地,奠定了后世“巴蜀—内蛮夷—外蛮夷”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基础。
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区域的华夏化,并不等于族群的华夏化。事实上,晚至东汉时期甚至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地区仍可见为数可观的典型土著群体墓葬,甚至在豪族大姓文化中也见有明显的古蜀文化遗存,[39]20、24、56、78、207可见巴蜀地区族群并未完全华夏化。特别是,巴蜀地区的巴郡是板楯蛮长期生活的区域,直到东汉末年板楯蛮仍然是巴郡的主要族群,[40]卷八六:2842但巴郡在秦汉时期并不被视为“荒服”之地(秦汉时期的西南“荒服”区域是西南夷地区),而是华夏之区。板楯蛮的特殊性表明秦汉时期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完全是从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立场出发的,这就使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与真实的族群在空间的分布上存在差异。
三、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地缘关系与政区性族群政治地理空间
秦汉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变化在于,西南夷中的部分群体被纳入到了大一统王朝国家中,其生活区域也成为王朝国家的郡县。这一重要的变化,其初也与地缘因素有关。前文已讨论过,秦楚争霸时期汉中、巴蜀均为要地,在此态势下,楚也曾试图控制滇、黔地区,以牵制秦的扩张意图。[32]卷一一六:3626楚人庄蹻定滇本有牵制秦的意图,但因秦定巴蜀、楚黔中,阻断楚对滇池地区的治理,滇池地区也未能实现郡县化。不过,后来所称的西南夷北部地区,则在秦通五尺道后初步实现了郡县化。
秦汉之际统一战争集中在北方,未能顾及西南夷地区。刘邦为汉王时,“虽王有巴、蜀,南中不宾也”。[32]卷一:128而由“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实为“关”[41])蜀故徼”的记载来看,[32]卷一一六3627汉朝建立后还放弃过秦已置吏的部分西南夷地区。高后时期,“城僰道,开青衣”,[32]卷一 128部分西南夷地区复又置吏,但范围当比较有限。
西南夷地区大范围的郡县化发生于汉初武帝时期。而且,此期西南夷地区郡县化的初衷并非为了国家疆域的开拓,而是与南越、匈奴的问题有关。与南越有关的郡化区域是南夷的夜郎地区。南越反叛时,唐蒙认为由牂牁出兵可收出其不意之效。[32]卷一一六:3628唐蒙的建议为武帝采纳,唐蒙由符关南下与夜郎侯多同等“约为置吏”,[32]卷一一六:3628一部分夜郎地区得以郡县化。不过,因筑道困难,加之有西南夷反叛,需“力事匈奴”等原因,初置的郡县未几旋废,只保留了两县一都慰。[32]卷一一六:3629及南越破后,汉军回军途中才“行诛头兰”,威服南夷置牂牁郡。
西夷大部分区域的郡县化则与匈奴问题有关。建元时期,司马相如曾尝试在西夷地区建立初县,并取得成效,有部分西夷群体“约为置吏”。不过,“约为置吏”的西夷地区不久之后同样因“道不通”、“力事匈奴”等原因而被放弃。元狩元年(前122),张骞从大夏为武帝带回了两条重要信息:其一,西域诸国中部分群体受匈奴压迫,可借机与西域诸国结为昆弟以断匈奴右臂;其二,由蜀有道可通身毒,进而通西域。[32]卷一一七:3843-3846张骞同时认为,由蜀使大夏能够避免羌人、匈奴的阻挠,建议武帝遣使由蜀通大夏。武帝“以骞言为然”,派遣使者由駹、冉、徙、邛僰四路通大夏,但均为氐、筰、巂、昆明所阻。[32]卷一一七:3844元鼎五年(前112)汉王朝平服南越并诛杀且兰、邛都、筰都等首领后,冉駹等群体才“请臣置吏”,[32]卷一一六:3631汉王朝顺势在邛都地区置越巂郡,在筰都地区置沈犁郡,在冉駹地区置汶山郡,在白马地区置武都郡。南越破后武帝也曾使王然于以破南越的兵士迫使滇王入朝,但未能成功。元封二年(前109),汉王朝以巴蜀兵士击灭滇国附属的靡莫、劳浸群体后,滇王才请置吏,益州郡得以设置。
武都、汶山、沈黎、越巂、益州、牂柯等郡设置后,武帝仍希望“地接以前通大夏”,但前后派遣的十余批使者均“闭昆明,为所杀”。[32]卷一一七:3849元封二年,汉王朝派郭昌、卫广率三辅罪人并巴蜀兵士数万人攻昆明,虽取得了军事胜利,但昆明仍未归附。此后数年,西出使者仍为昆明所阻,道不得通。[32]卷一一七:3849元封四年,郭昌再次征昆明,无功而返。[32]卷一一七:3862昆明地区郡县化的具体时间史籍记载不详,只知道在郭昌第二次征昆明后数年“并昆明地”属益州郡。[40]卷八六:2846
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化过程展现了其独特的地缘关系,即由之可加强对南越地区的治理,与西域诸国的结盟,甚至一定程度上有牵制匈奴的地缘意义。此种地缘意义尽管有地理层面上的失误,但却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化。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绕道南方“断匈奴右臂”完全是一种“错误地理”,但这种“错误地理”却使西南夷群体“逐渐纳入‘中国’的版图”。[42]42方铁也指出过,汉朝开拓西南夷地区,其初衷要么是为了开通通南越的道路,要么是为了打通通往大夏的道路,不仅体现了一定的“功利目的”,也表现出决策的“随意性”。[43]78
东汉时期设置的永昌郡,理论上说在郡县化前也应是汉王朝西出的主要障碍。不过,武帝时期大破匈奴并在西域地区设置都护府后,西夷地区特殊的地缘关系在北方及西北问题上便失去了意义。与之对应,东汉时期永昌郡的设置并非汉朝主动开边的结果,而是永昌群体内附所致。
西南夷地区郡县化之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随之建立,形成了“巴蜀—内蛮夷—外蛮夷”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其中,巴蜀地区不仅为华夏区域,而且在武帝广关后被正式纳入到政治地理涵义中的“大关中”区域内,成为治理西南夷地区的前沿。[44]29-36西南夷地区终于两汉仍主要是蛮夷所居区域,但在西南夷地区郡县化过程中,形成了作为王朝国家疆界的“外徼”和作为华夏族群与国家疆域内西南夷群体相区分的“内徼”两条重要的族群政治地理区分界限,使得郡县化的西南夷群体在与巴蜀汉族群体有明确政治地理区分的同时,西南夷群体也有明确的政治地理空间区分,即“内蛮夷”与“外蛮夷”的问题。
结语
在大一统思想的层面上,周秦两汉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过程,呈现出“由内而外”逐步推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深受政治地理空间性质转变、郡县化态势、族群分布演变的影响。就政治地理空间性质的转变而言,西周至战国末西南地区由地域到政区的转变过程,表征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就郡县化态势而言,西南地区不同区域是否郡县化,是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最现实的政治地理基础;就族群分布演变的影响而言,“华夷”格局的演变,是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最现实的族群地理基础。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西南地区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总的来说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西周到战国末,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主要表现为“五方之民”视野下的“一点四方”模式,即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主要问题是“华夏”与“蛮夷”地域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性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秦汉王朝时期,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视野下形成的“中心—边缘”模式是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主要表现,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主要问题是“内”与“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政区性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
周秦两汉西南地区空间性质的转变、郡县化态势、族群分布演变,均又明显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商周之际“西土”地缘意义的出现,西周春秋时期汉中地区地缘意义的存在,是西周春秋时期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秦、楚、巴、蜀对汉中地区的争夺,秦、楚对巴蜀、汉中、部分西南夷地区的关注,均与西南地区不同区域特殊的地缘因素有关。此外,巴蜀地区特殊的地缘关系,还对其族群结构的变动特别是华夏化的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大一统王朝国家时期全新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奠定了基础。秦汉大一统时期,西南夷地区特殊的地缘关系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化,作为国家疆界的“(外)徼”界不断外推,“巴蜀—内蛮夷—外蛮夷”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最终得以构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