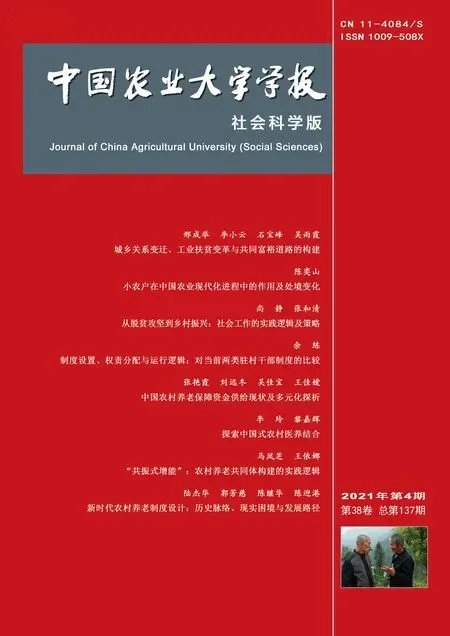苏区革命再认知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王 震
一、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从《寻乌调查》说起
1930年代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已然成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讨论有关于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重点区域。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已经淡出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但是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对于中共中央此后一系列有关于土地革命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首先强调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对于中共中央一系列决策的重要性,以《寻乌调查》为引,勾勒出中共中央对于苏区阶级分化、土地关系的实质判断。相较于非实地所作的《兴国调查》,毛泽东立足于实地状况的《寻乌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寻乌乃至赣闽粤边区社会生活的风貌,具备相当的客观性。通过《寻乌调查》,可以了解到苏区土地革命中人口及土地占比情况。相关数据显示,寻乌全县地主人口成分占比为3.445%,土地占比为30%,连同富农在内的农民人口成分占比为92.255%,土地占比为30%[1]105。该调查结果很容易将苏区土地革命爆发的原因导向苏区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这一推论。然而《寻乌调查》的土地占比数据实质上忽略了地权分离这一特殊因素。基于这一观点,黄氏从《苏区部分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福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等相关数据得出了苏区土地集中有限性的结论。例如,“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2]162。“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唯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3]96。与此同时,黄氏运用自己独特的历史认知方式阐释了中央苏区土地分散与这一地区实际存在着的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的关系。通过与《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统计》的比对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虽然苏区呈现土地分散的态势,但地主人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10~30倍(1)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12-13。。地主与贫农之间人均土地占有的差距,实际上暗示了苏区土地革命发生的诸般可能,它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苏区土地革命源流的多样性。
随着苏区土地革命的持续推进,地方豪绅很快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此状况下,农村人口和占地比例最大的农民成为苏区土地革命的重点关注对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将注意力转向富农群体。他将这种富裕的农民视为“半地主性的富农”。这一论断的出现实质上与党内“富农路线的发展”[4]200密切相关。对于富农群体的重点关注,使得苏区土地革命往往忽略了中农的影响力。而对于强调阶级分析的中共党人而言,中农的划分实际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基于此,黄氏首先阐述了苏区土地革命对于中农的实质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农形象的逐渐鲜明。其中毛泽东给中农下的定义是:“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5]128,该定义表明中农实质上是作为中共联合对象的身份存在的。此外,黄氏也注意到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话语中,中农作为联合对象的地位和紧密度往往随着中共中央判断的变化而改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不但发现了中共对于中农群体的重视,因为尽力使中农成为主流阶层,符合中共的战略需求;而且通过相关数据敏锐地觉察到由于中农和贫雇农具备不同的经济地位和利益诉求,二者之间必然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对福建14个县22个村耕牛占有状况的调查显示,中农占有耕牛总数的55.69%,贫雇农占有32.63%[6]189。江西九江县石门乡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分别达到46.6%和50.47%[3]146。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来看,中农具有更大优势。而一旦二者发生冲突,贫雇农实质上具有绝对强势的地位,查田运动后苏区甚至一度形成了普遍打击中农的局面。阶级话语下中农与贫农的尴尬境遇正是由于苏区社会政治的排异性所造成的,而中农命运的浮沉不由让人体会到具体历史情境的复杂性。
此外,苏区土地革命虽然处在一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中,但是整体来看,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区土地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要点便是中共对于土地的实际分配与利用。《寻乌调查》也涉及了苏区土地革命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公田问题。《寻乌调查》对于传统中国公田运作制度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央苏区的公田制度提供了相应的材料。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将公田分为祖宗田、神道田、教育与社会公益性质的公田三类。毛泽东有意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公田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1]108。在此基础之上,黄氏结合公田制度以及相关史实,从另一角度综合考量了公田对于重组农村社会权力结构、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实际上都是公田比例较高的地区,其中,“闽北、闽西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赣南公田通常也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6]109。对于公田的平均分配一方面可以打破中央苏区聚族而居特征下宗法家规的制约,从而形成及时有效的新型农村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使用权,将公田本身效率低下的集体利用方式转化为高效的个体使用方式。黄氏将这一举动称为“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妙棋子”,它对于中共苏区土地革命的进行实际上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
通过作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在一种复杂轨迹上逐步推进的。黄氏基于《寻乌调查》中所折射而出的土地革命问题,从苏区土地分散程度、中农认知、公田利用价值等方面对苏区土地革命展开了全面而又细致的思考。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中央苏区革命历程中的种种阻力与问题。然而除却土地革命外,苏区革命制度的建设在苏区革命历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走进1933—1934年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具体过程,深入了解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中央苏区制度建设造成的影响。
二、中央苏区的制度建设:军事推行的制度特征
毫无疑问,《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中论述最为精彩的篇章便是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有关内容。本书以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的党建问题、政权建设问题、文教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妇女、群众及红军等多角度呈现了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特征及问题。实际上,从 1930年苏区建立起,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与民主性特征往往处于一种此隐彼见的状态,直至第五次反“围剿”结束,基本划定了中央苏区发展的限界。1933—1934年由于国民党产生的外部威胁以及党内高层领导人共识的形成,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始终坚持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的指导方针,军事力量在苏区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建设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苏区制度建设中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也为苏区的党建、政权建构、文教宣传等工作带来了些许弊病。
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中央苏区党员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赣西南会议记录》所言:“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到达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7]628。黄氏明显注意到了军事力量对于政治力量发展的大力推动作用。其突出的表现便是中央苏区党员数量急剧增加,然而短时期内扩大党员数量必然会造成党员质量下降,这实际上是中共在苏区建构庞大组织网络必然付出的代价。面对这一问题,黄氏展开了思考。他一方面发现中共保持强大组织力的秘密——高质量的干部队伍培养,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军事力量主导地位下党建工作的弊病。黄氏发现军事推行的特征使得“无产阶级纯洁性”成为党组织发展的首要因素,“成分论”开始大行其道。这使得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据统计,经过1932年初的“肃反”,“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8]696。这个问题虽然在之后引发了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重新思考,使得从政策方面知识分子被排斥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遏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特定历史时期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以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唯成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央苏区的政权建构后会发现,军事力量主导下的政权建构实际上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在言及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原因时,黄氏便注意到了中共苏维埃革命实际上是社会政治领域的全新转换。共产国际代表对于中共初期苏维埃政权状况的描述,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观点:“试图躲在自己的区域内,用万里长城将自己同外界隔开,建立一个摆脱赋税、摆脱地主统治等等的国家”[9]510。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首先体现了“人民性”的特征。而在实际的制度构建中,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沿袭了苏俄的体制和经验,实行代表会议制度。地方政权往往实行“议行合一”制度,其中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是其首要原则。黄氏对于苏区“村代表”制度以及工农检察制度的强调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央苏区政权建构的新变。然而这种新变实际上一直处于苏区军事推进这一基本背景之下,其造成的后果便是红军极度强势地位的生成。这就导致了初期苏维埃政权反而处于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来自中共内部的报告指出:“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所以这个政权还是脱离群众”[7]377。
事实上,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武装革命、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种思想革命、社会革命”[10]126。因此,在整个中央苏区的革命制度建设历程中,除却党建、政权建设工作,军事推行的主导特征对于文教工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区内部往往将宣传与教育相结合,这大大提高了苏区内部民众的文化水平。据统计,1933年底,苏区共设有夜校6 462所,受教成人达94 517人,尤其是“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11]330。民众基本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妇女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求平等、求解放的宗旨。中央苏区妇女教育水平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很好地体现了民主性的特点。这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12]283-284。然而受限于以军事推进为主导的时代背景,妇女运动受重视程度于后期开始明显下降,特别是妇女平等问题中暴露出来的“性错乱”问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不无关联。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苏区妇女地位的提高,使其在后方生产与安全警戒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各地在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积极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1934年春耕期间,瑞金能够参加生产的妇女达到3 104人,仅下洲区就有1 019人(2)定一.春耕运动在瑞京.斗争,1934-04-07。。兴国全县参加生产的妇女更高达两万人以上(3)王首道.模范红军家属运动.斗争,1934-08-16。。通过黄氏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苏区文教工作下妇女地位的提高、群众武装组织的改造以及红军队伍宣传系统的建设都受到了军事力量推进的极大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都是为军事力量主导下的苏区革命服务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1933—1934年苏区制度建设过程中军事推进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苏区军事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中央苏区面临空前的困难,无论是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封锁,还是苏区内部人力、财力的持续消耗都迫使苏区的制度建设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军事推行下的制度建设固然有许多弊病,但是它很好地解决了中共首先面临的生存问题。因此,如果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苏区的革命史,我们就会发现苏区革命的推进往往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
三、革命的张力与界限:新历史观下的苏区革命史
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研究在此前实际上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在充分掌握相关史实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突破传统革命史观的固定架构,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书中对于苏区土地革命以及军事推行特征多角度的考察不禁让我们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产生思考。对于客观化史学立场的研究者来说,历史往往首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史料的掌握是研究历史的基础。但是对于秉持新历史观的黄氏而言,除却对于史料的呈现,《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最想向我们传达的观念是一种全面还原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者在对中央苏区革命历史进行书写时必须带有自我思想的光芒。在这种新历史观的引导下,本书首先跳出历史学单一学科的局限,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全面考察了原初历史中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苏区土地分散这一推论实质上是作者通过苏区大量的经济数据比对分析得出。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土地面积数据、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比数据、生产资料占比数据等,通过对数据的处理,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我们才能够对土地革命的复杂性进行全面的反思。
与此同时,这种新历史观也体现在本书创造性地考虑到了农民具体历史情境下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感受。虽然土地革命作为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其地位不可动摇,然而当黄氏诉诸事实,我们会发现农民实际从土地获利较少。正如陈赓雅实地考察后写道:“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结果殊与愿望相反”[13]12。在此状况下,贫穷实际上成为农民渴望寻求革命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土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传统的生产资料,实际上也是农民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黄氏敏锐地把握到了农民对于土地渴望的心理。例如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14]77而这实际上也印证了土地革命之所以成为苏维埃革命旗帜的深层次原因。此外,黄氏还指出“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11]72。在这里,黄氏关注到了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心理变化的影响,其中重要的表现便是普通民众参政热情提高。此前论述中妇女地位的变化实际上印证了这一观点。早在1933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在召集省党代表大会的有关通知中,便明确规定:“出席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工人成分应占百分之四十,劳动妇女至少要占百分之十”[15]4。妇女及普通农民具备参政可能的结果表明了其实际上已经被纳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且成为主要成员。
全书运用新历史观的最大体现在于摆脱了传统史观主导下由结果展开逆向推论的问题。本书的诸般推论往往是从原初历史出发,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政治话语所带来的真相遮蔽。这点可以从本书对于查田运动的新论断中窥见一斑。查田运动向来被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干扰的集中反映,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寻找和制造敌人的过程。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打击造成了苏区群众的普遍恐慌,极大地损害了我党与革命群众之间的关系,甚至使得苏区社会发生严重动荡。而黄氏通过大量资料,深层次分析了查田运动的成因与现实。
首先,查田运动的开展实际上与此前得出的苏区土地分散的相关结论有关。苏区的土地占有较为分散,导致地主、富农的有限资产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改善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均平的旗帜下,生活高过平均水平的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其次,由于土地分散,阶级关系不明晰,在苏区的现实环境中,公式化的农村阶级分析往往不是当地农民真实状况的写照。例如,《黎川梅源概况》中也体现了土地革命运作中的诸多问题:“其已分配者,耕作之后,仍将其所收之谷,按佃户例,送还原主。土匪因此怀疑分配不实,于是一再举行分配,并有所谓查田运动之新花样出现,但举行结果,依旧如故”(4)黎川梅源概况. 汗血月刊,1934-04-20。。而除却土地革命相关因素的影响,查田运动的开展实质上也离不开中央苏区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历史背景。事实上,查田运动包含着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更为迫切的需求是支持苏维埃的财政需要。在中央苏区发展早期,一个极其重要的财政来源渠道便是没收地主、富农财物。但是由于苏区军事力量的持续推进,地主、富农阶级逐渐被完全清理,加之国民党后续采取的封锁政策,使得中央苏区的经济变得十分窘困。在此情况下,查田运动虽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多是经济的。运动中特别重视对地主、富农的财务没收,为此中央苏区专门设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用以完成经济目标。而在查田运动开始后的三个月内,仅博生、乐安、石城、胜利四县,就利用没收财物和强制捐款“筹到了十八万元”(5)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陈诚档案缩微胶卷008·661/6421/0240,江西省各县及中心区财长联席会议(1933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筹到606 919元(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红色中华,1934-01-26。。几个月的罚款收入相当于江西全省一年的农业税收入,查田运动现实的筹款需求在此体现得非常明显。再次回到查田运动的相关历史情境中,作为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开展的社会政治运动,查田运动具有明显的苏区政治印记。正如黄氏所言:“如果说当年的中共中央对运动的恶果毫无了解,未免也太低估了他们的能力,只是有理论和现实脱节的思想基础,加之吸取资源这样的需求的催迫,很多问题的出现就是大概率事件了”[11]305。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革命史书写新趋势的研究,“革命”一词得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本书正是沿着中共在中央苏区革命的步伐,试图带领我们去点亮、触碰历史的暗角。在此过程中,革命,这个曾经震撼中国社会的“幽灵”再一次浮现在读者眼前。正如查默斯·詹隼所言:“研究一般革命或任何特定革命,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革命的研究必须置于它们所发生的社会体系中,对革命的分析和对具有生命力且发挥功能的社会的分析相互交叠,任何割裂这两个概念的企图,都会削弱它们的作用”[16]2。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正是基于此原则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史进行了再认知。事实上通过黄氏对于苏区革命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在改变国家、社会、个体时彰显出的令人炫目的张力,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也会发现革命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这也正是作者想要为我们所展现的真正的历史。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城乡关系变迁、工业扶贫变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
- 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改造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