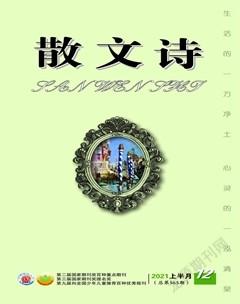秋野之歌
宋晓杰
窗外的小河,通往辽河
——船行水上,你会看到更辽远的风景。
往事蜂拥,那不是虚拟的歌声,是堤岸上被风吹皱的幕布,广场上正在上映的艺术人生。
回忆是黑白的。回忆是甜的,也是咸的。大海滚烫,星辰脆响,是谁被岁月淘洗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虚空?半个世纪过去了,离家的孩子回来了——当我再次归来,意义多么不同。童年的渡口,也是时间的渡口。终生渡不过的河。
河边的芦苇,如幼兽的皮毛,顺着风,我有耐心,等它醒来。辽河,一群上好的羊,一匹滑爽的丝绸。“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内心的啸叫,电闪雷鸣。我却像个哑孩子,只想无声地哭。
灯塔。斜阳。紫蝶翻飞。海鸥鸣叫。泥泞的小水洼。童年的太阳雨。码头。粮站。栈桥。渡船。被服廠。豆腐坊……我们在沙滩上喊叫着呼引同伴,赤足奔跑,小鱼篓敲打着屁股,微微地痒。刚刚买了两分钱的“海奔儿奔儿”,在衣袋里乱串,我紧紧捂住,不让它们出声。企图逃跑,更不可能。
诗人说:“我向阴柔的万物承认/我给它们平添了/年迈的模样;/我承认,并且致歉。”但我并不以清贫、苦难的童年自责。我就是那水面上的不系之舟,在一场淅淅沥沥的细雨中,入港,终生于此停歇。每一条小河,都有来路;每一朵浪花,都有初衷。我不是仁者,也不敢说是智者,在奔涌的流水面前,唯有低头,让路。“纪念那死在海上和即将死在海上的人。”太多的纪念碑,没有纪念。而最痛的纪念,无迹可寻。
多年以前,一位朋友的爸爸病故。他含泪听从了爸爸的遗嘱:把爸爸的骨灰,撒进辽河……多年以后,他茫然四顾:“到哪里去找爸爸呀?”于是,每年,他都要在紧邻辽河岸边的酒店里,住一住,呆一呆。星垂平野,大河奔涌。生死契阔,阴阳两隔。隔空的对话,流云、逝水是否忍听?
风行水上书。云在青天,水在瓶。你看那高翔的雨燕,它的翅膀因热气蒸腾,而兴奋;也因看到更远的天空,而颤抖。窗外的小河因通往辽河,使胸襟和胆识,无限增容。
去年的稻草人
——你还好吗?你于田野中忽然现身。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吗?
日子用什么结网?又以什么方式被记忆?不分季节的编织,持续发生。翻飞的指尖,缘于问候。是驱赶,也是招引——时辰不到,你隐于遗忘的断层。时钟般的忠贞,使你成为信赖的象征。
水稻田沙沙作响,倾诉的愿望得以成全。面具只是一种身份,死亡与生殖的秘密昭然若揭——煮豆燃豆萁;用剑者伤于剑。你以陈年的稻草为肌肤之躯,并委以重任,你与飞鸟时而横眉冷对,时而握手言和,目的只有一个:让稻米自由地成长,让每一粒稻米颗粒归仓。
不久,沃野苍穹,秋风转凉,给你几个响晴的好天气吧。高头大马的收割机在田垄间,划着横平竖直的线条游戏。人们戴着草帽,不用再弯腰费力地捆扎稻束。机器行过田垄,稻米的归稻米,稻草的归稻草。没有规矩,如何制胜?
稻粒被均匀地吐出,你现出惊诧的面孔,或木然没有表情。松软下来。那么由衷。麻雀叽叽喳喳的闲言,于你无用。
荒野上,刮起一丝丝凉风,你垂下空空的衣袖,在缅想中兀自饱满、深情,虽然,你越来越瘦……
——歌剧《田垄之上》 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