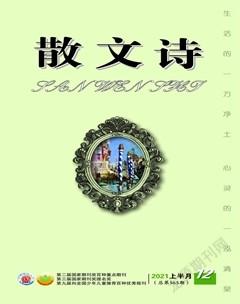时间的寓意
张泽雄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首届“七个一百”文学人才成员,鲁迅文学院湖北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作品见于《诗刊》《星星》《散文诗》《长江文艺》《芳草》等刊物,并入选多种选刊、选本。获诗刊社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诗歌月刊》杂志全国爱情诗大赛特等奖、首届全国“绿风诗歌奖”二等奖、首届汨罗文学奖现代诗九章奖等多种奖项。长诗《汉于此水》入选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秦巴植物园
秦巴的风,正从一个山坳、一个隘口,吹拂——
时间只是一个概数。昨天万亩荒山,仿佛一夜间被风吹走。
越过秦岭寒冷的界限,一年四季把十堰的山水装点:中国花田、七彩梯田、杜鹃岭、紫薇林、紫藤花廊、芙蓉塘……
秦巴各色植被、石径和水湾,借了这个山谷,跌下,再宕开,它像埋伏在城里的一只布谷,每日提醒返乡的人。
它又像在我们的隔壁,替我们除尘降噪,去掉生活的败笔,将人间的炊烟袅袅升起。
大片的油菜花,才谢在半路,三百亩郁金香竞相绽放。还有梅花、月季、牡丹、角堇、鲁冰花、金鱼草……会在自己的节日里,轮番出演。
秦巴加上汉水,光阴泄了一地。一个植物园,不单单是一个物种基因库。它还试图替我们写下时间的病历;替我们解开另一种生存密码。
西关映象
每一座城,都有一两个关隘可以把守;每一间房子,都有它的秘密。在梁柱间,在屋脊,在落日的背影里。
案几上,一杯酒、一碟菇,一些唐人留下的果壳。
戏楼里高亢或低回的嗓音,在一截截楠木上,缠绕、跌宕……
更多的市井逶迤于世间角落,它们都是时间的寓言。难以述说。太多场景难以复原。包括使用了千年的读音、称谓和服饰。
地名翻来覆去,最终还是回到原址。山中这块平地,适宜砌屋盖房、建市,也适宜皇室流放。
敞开一条老街的美,需要有持久的勇气和耐心。褪色的时间,仍有老西关、棚户区,停滞的喘息声。
暮色里,一张忧郁、沧桑的脸颊,倚门而立。
我取下灯影,将你折叠、归拢。
房县西关街
城西——太阳落下去,自有接收它的隘口和格局。如果不是县衙,就一定有个街市。
难得有一块山中平地,四周都在坐北朝南。风是它唯一的败笔。筑城的人已一水穿城。时间将一切埋葬,又将一些记忆翻新。
而今,西关街旧址,成了网红打卡处。游人自然也不会少。
壮观的戏楼,显然杵在这条街现在的核心。戏有没有,我没看过,现在,屏幕上正放映广告片。
楠木立柱太粗,像是假的。
路人都在掷一枚硬币,猜它的正反面。
还有俄罗斯红松。更多的构件似曾相识,像这条街,模拟了各地风味小吃,大多没有开张。
旧时的药铺、杂货店、盐肆、钱庄、客栈……此时也已闭门谢客。可能缺少流量商贾,抑或是我错过了季节。
那些大坛御制的黄酒,挨家挨户,仿佛满街都在排队沽酒;被皇上惦记的小花菇、唐时的野菌,置于门楣,像在等怀旧的人。
饮品小屋,墙上挂满祈福的小纸片,像秋风给落叶的题词;至于根雕烙画,遗落民间的手艺人,正将一方野史清点、抒写。
各类收藏、旧物,更像停止的时间,搁在案几上。
这条仿古街,我们看到了时间落下的灰尘,以及它的背面,在暮色笼罩的灯火里,好戏这才开场。
瞬间,觉得梦回唐朝,觉得时间并没留下破绽。
一阵恍惚。晨练和暮游,都像在旧时光里;仍有廊燕、麻雀在飞,仍有蝙蝠在飞。旧时的风,没有走远。
光阴论
一个人来过,他留下痕迹。读书生活、谈恋爱,一生的成长和枯萎,其间是一大段光阴。
珍惜也好,浪费也罢,你只拥有属于你的部分,用完就完了。你,不能用别人的。
宇宙洪荒之外,人亦具有光阴的属性。光阴从我们身上流淌,又被我们使用、完成。
老祖宗们一直在说,珍惜会让它增长、变长;挥霍浪费,迫使光阴减少和停止。
光阴的长度,就固定在你的身体里,你存在的长度就是它的长度。至于你将一瓣掰成两瓣,这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你还是花光了。
有的人,他的光陰用完了,为什么还能长久留存于世?
那是光阴留下的影子。光阴有影子,身体死了,影子仍在。影子是身体的回声,一路相互牵扯、攀比,若即若离,又不离不弃。
有人说,活得精彩高大,有益于世的人,给影子增加了高度和重量。
那些尘埃一样平凡的草根呢?他们匍匐的光阴是已戛然而止,还是应年年枯荣?
光阴没有贵贱。不会贵人的光阴花不完,穷人的光阴就贱卖。
我一直想问:光阴会不会被耽误,折断了能否还能再接续上?光阴能不能开花结果,能不能保鲜?
光阴没有答案。光阴无法等你,它来时即来,走时即走。
光阴为什么会被我们轻易打发?光阴在流水中永无止歇,一直向前。而梦里的光阴总是倒流。
取下光阴的某个断片,让它静止在瓶子里,等远方打开。
一棵树相信另一棵树能够长大,它应该禁得住季节的雾霾和过眼烟云。从光阴里坠落,没人能活着走出自己。泥土献出它最后一个休止符。
坟茔埋葬了一个人的全部时辰与终点;墓碑上,都是光阴刻下的碑文。它的褒贬,早被自己定制、拟好。
流水一路归拢。散落的塘堰,仍有日月星辰在闪烁,仍然有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