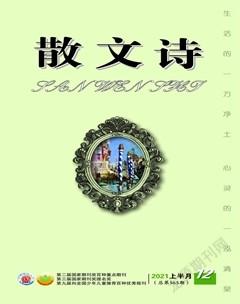住进水乡的月亮 (外二章)
彭润琪
一艘小小的船,是住进水乡的月亮。
云梦泽的春水暖了,急不可耐的,除了鸭子,还有那一条牧鸭船。
门前的水路不知有几道弯?鸭子数过,它也数过。于是,它繞过了365天,却没有绕出日升和月落。
湖垸的石拱桥到底有几座?
它对着桥洞喊:咧喔咧喔——
声音穿过一个又一个桥洞,赶回了一群迷路的鸭子。从此,它不敢轻易交付一声沥干的回音。
它太小了,小到只容下一双脚。
我知道,这是为泽乡缝制的鞋,穿上它,足以让我们任意行走,追赶鸟语,追赶花香。
它太轻了,轻到一个肩头就可以扛下。一根竹竿就可以让它动如脱兔,静如处子。若一片飘落的叶,风一吹,便足以让河水安静,远山静默。
牧鸭的人啊,这是你的战舰!
不管水路多曲折,有它,失群的鸭子也能找回自己的家。
不管有多少石拱桥,有它,水乡的路才绵延不绝。
因为,它是水乡一弯流淌的新月。
二亩八
屋后的稻田,被狭窄的田径划出各自的疆界。每一块都没有名字,除了它的面积。
于是,面积就成了它的名字。
二亩八。对我来说,早已忽略了我对亩的认识。
二亩八是空阔的。
鸟雀可以从容地从父亲佝偻的背脊划过弧线,单腿立于田中,然后扑棱着双翅,在水面留下一声脆鸣。
二亩八是宽阔的。
它容得下数日的月升日落,也繁殖惊人的水蛭和水螅,还有所有的秧苗。
于是,我总是想越过二亩八,越过父母所有的期盼。
二十八年后的二亩八,还是二亩八。依然用稻苗书写自己的四季繁华和世间冷暖。
或许是父亲用脚不停丈量的缘故,连田埂的宽窄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我望它的眼神。
我不知道,二亩八是否还认识我?
于是,我不得不在一株稻子中道明原委。
田 埂
一条被农机和脚板踩踏的田埂,那些泥泞已经板结,静默在天空下。田野开始孕育各种声音,熟悉得让人能分辨出每一个蓬勃的日子。
父亲用锄头在田埂边休整,母亲在田埂边种豌豆。
每一粒油菜籽落下来,你一定可以在田埂捡拾起一束油菜花;就像那些汗水,父母总是能用扁担、箩筐担起一个季节的庄稼。
如今,我那勤劳的父母,再也无法健步如飞。
每一次走在田埂上,他们都姿势虔诚,低头弯腰,仿佛在倾听田埂给他们的新的谕示:
这是一条路,也是一条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