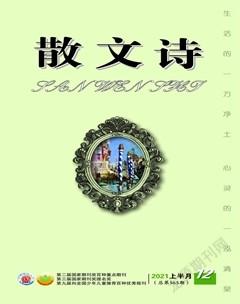浏阳河的题外话
刘炳琪
乌川水库的蓝
乌川水库的蓝,蓝到骨子里,超过我对一座水库的想象。
四月的水库上,天空出奇干净,白哗哗的阳光洒下来,像提前进入夏天。
其实,我喜欢春天。穿过油菜花和桃花李花的缝隙,走过一条绿草如茵的弯弯小道,就能看到同样绿意朦胧的大坝,仿佛一道宏伟的城墙,里面住着它保护的村民。
置身宛如城楼的坝顶。
巍峨远山与近处树木,留下深深浅浅的影子。
我想,假若不是当年几万农民肩扛手提,乌川水库还是山峦围住的一片田垄,还是几个安放在原野之上的小小池塘,那么,我们还会不会慕名而来?久远的锣鼓与劳动号子声,早已消逝于某个年关的午后,听不到一点回音,只有清澈的鸟鸣,荡过波浪而来,像倾诉,又像歌唱。
风似乎想证明什么。
它们在平坦的水面上滑行,勾勒出一条一条曲线,什么意思呢?我若是风,如果也能吹拂到水中的小岛,让时光的船停泊,这多好!我就可以做樟树、枞树、毛竹,对着阳光张开翅膀,领略飞翔的感觉。
可惜,水面遍地的蓝,让我太多的臆想止步于白云,仿佛天空被摁进了水里,或者,是水收留了白云的浪漫,以及天空的辽阔;如果没有云,天空有多单调,水就该有多单调。
云在水里,蓝也就在水里,沿着水库蜿蜒的小路,感觉云在动,而蓝一如既往,反复注视我的走向。
哪儿也没想去,纯粹的蓝足以让我放弃一切非分之想。甚至觉得,做一只游荡于堤边的鸭也挺好,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必为所谓的繁华与舒适而折腰,只享受这漫天的蓝,真的挺好。
一片沙滩,没有掺杂太多的泥石,正传递着尘世的光。
王震故居前
我是幸運的。
避开了纷飞的战火年代,有安居乐业的前半生。
我是快乐的,将有衣食无忧的后半生。
当落叶把我从长沙城带到浏阳北圣,我又是惭愧的。因为,谁能像您一样,抛弃富足的生活,甘愿把青春和热血洒向贫瘠的土地和雪雨冰霜呢?
也是秋天,您离开青山绿水的故乡。
秋天多好!
阳光温暖,南风轻柔,四周的稻田,金色的稻浪翻滚,成群的孩子行走在树阴与稻浪之间,像快乐的燕子。是的,他们就是无忧无虑的燕子,红领巾在风中飘扬,他们,或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全是您和您一样的先辈奋斗得来的。
浏阳、井冈山、延安、新疆、北大荒、大西南,我没有计算过您的足迹,没有丈量过那些苦痛和荒凉;学生、农民、士兵、军官、指挥长、国家领导人,您奋斗的一生提升了我对奉献的认知。我站在门前,学学路旁的柏树和庭院的松,仰望白云一朵朵飘过思想的天空,端详您的照片,重温您的光辉岁月,想象一只雄鹰,是怎样展翅飞过。
我想,换作我,该有多少的难以取舍?父母,兄弟姐妹,故乡的情结,而远方,还有无数的危险和不能预知的艰难,但也只有远方,才能装下您的宏图大志,仿佛阳光如火,燃烧在东方,您从不把享受放在心上。
我该惭愧!怎么能把自己当成门口的池塘,靠几片残荷支撑命运的激情?曾经的小路铺成了大道,还有什么理由,当一棵随风而摆的草,伴着流水的西去而忘却自尊?
都说,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不是白纸,也不能做废笔,把生命的珍贵浪费在光阴中。
即使是落叶,也要在坠落中,划成一条迷人的曲线。
重上大围山
每次登上山顶,总觉得是第一回。
除了植被的翻来覆去。
我特别想在冬天来。大围山的风景照里,数白雪素裹最为迷人。湘东地区唯一的高海拔,每每让愿望停滞在冰封的上山路,错失无限美好。但此刻,坐在木质凉亭的长凳上,好像自己也是雪,正被南风吹得飘飘扬扬。
严格地说,五月的映山红与腊月的雪,都不能替换我对辽阔的期待。
坐在山上看山,你会发现,山都不是山,而是一群奔跑的兄弟姐妹,顶着骄阳,携手并肩,是打死也不会分开的骨肉同胞。
事实上,它们正是以博大的胸怀,容留生活在此的万千子民,以挺直的脊梁,将秋收起义的部队一路送到井冈山。
这些久远的故事,有清晰的脉络和如卷的画面,在绿色视觉里反复播放,又像是某个家长里短的饭后,一杯清茶里,星辰与月亮的对话。
沿着弯曲陡峭的小道,仿佛一条顺流的鱼。归来的路上,小溪里并没有鱼,比我跑得还要欢快。许是流水过于清澈,应验水清则无鱼的哲语;许是更多的鱼,游弋两岸松树与楠竹之下,等待更加宁静时刻的到来。
哪有更宁静一说呢?隐身的石壁,树林里的鸟群,天上的云朵,一直保持空旷而又谦恭的姿势,如果说喧嚣,则是登山和下山的人。
我比鱼更加幸运!
因为,我可以去滑冰场,以冬日的紧凑对付夏天的炎热,一块草地,一汪池塘,一片树林,都是放飞自由的场所,在山峰,在沟谷,在无人光顾的原始森林。
鱼若知情,该情以何堪?
我常想,大围山距长沙城百公里之遥,是什么让那么多人愿意驱车前往?
不是高,不是大,而是对山与水的那份情。
当我选择在一块石头下站立,它是孤立的,但放眼望去,更多的石头抬起了头。
人,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是孤独的,很多的人聚在一起,就是一群人、一堆人,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最终形成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
不愿相信一座山就是一座山。
山有了灵气,就有超越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像山那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