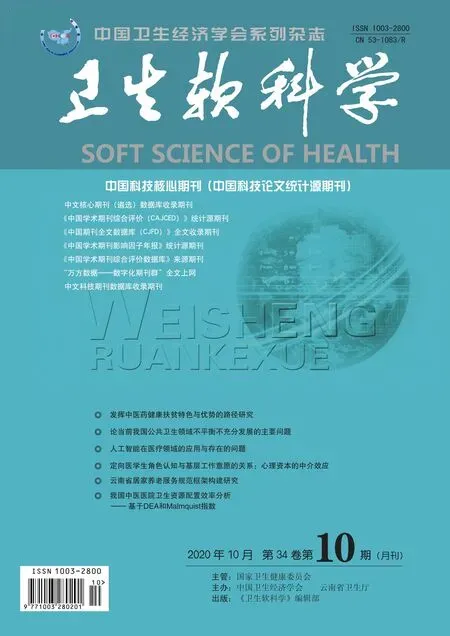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与存在的问题
刘伶俐,王 端
(1.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重庆 400038;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疾病中心,重庆 401120)
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的突破,掀起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简称AI)研究热潮。据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 2018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医疗领域已经成为AI行业重要的研究和应用领域,2013年以来医疗AI创业公司融资43亿美元,领先于其它所有行业。老牌咨询公司麦肯锡则预测,到2025年,全球智能医疗行业规模将达到254亿美元,约占全球AI市场总值的1/5[1]。在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充足的医疗数据、旺盛的医疗需求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国内互联网巨头和医疗创业公司进军AI医疗提供了强劲的动力[2]。2016年以来,在我国大力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深入医疗领域的各个环节,相关研究和应用突飞猛进,但也面临不少问题。本文拟对人工智能在我国医疗领域的主要应用和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1 人工智能概述
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关于机器智能的研讨会上,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人首次提出“人工智能”一词,即:“让机器达到与人类做同样的行为,可以被称为人工智能”。由此诞生了人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经过60多年的演进和发展,人工智能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在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的问题上,科学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一般认为,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3]。它试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能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
由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对智能的不同看法,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了三大主流学派[4]:①符号主义(又称逻辑主义学派),认为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本单元是符号,而认知过程就是对符号的逻辑运算,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机中逻辑门的运算将人类抽象的逻辑思维模拟出来,从而实现人工智能。基于此认识,符号学派把研究焦点集中在人类智能的高级行为,如推理、规划、知识表示等方面,其主要成就是上世纪的专家系统。②连接主义(又称仿生学派),认为智能活动是由大量简单的神经单元通过复杂的相互连接后并行运行的结果,因而主张通过模拟大脑的结构,用神经网络的连接机制实现人工智能。连接学派最主要的成果是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当前炙手可热的深度学习,可以看作是连接学派的延伸,已经在语音识别、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③行为主义(又称控制论学派),则希望从模拟动物的“感知—动作”开始,最终复制出人类的智能。其主要贡献是智能机器人系统。这三大学派曾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如何将三大学派的观点融会贯通,将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突破口。
按照实现的能力,人工智能可分为3个层次[5]:①弱人工智能,即擅长于单个方面或单个任务的人工智能;②强人工智能,是指可以像人类一样认知和思考、在各方面都能模仿人类甚至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③超人工智能,是指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都强很多的人工智能。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都属于弱人工智能,即便有些AI程序或者机器人在某些方面的智能超越人类非常多,它也只是在执行一个闭环任务,本身并不能像人一样全方位思考,也没有意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将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甚至超人工智能发展。
2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主要应用
人工智能与医疗的结合,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专家系统,2011年起开始大规模应用于医疗领域,2016年起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其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2.1 AI虚拟助理
在医疗领域中的虚拟助理,属于专用型虚拟助理。基于特定领域的知识系统,通过智能语音技术和自然语言相关技术,实现人机交互,解决使用者某一特定需求。目前,由国内企业研发的医用虚拟助理已应用于诊前、诊中、诊后等多个环节。①诊前:智能导诊机器人已成为医院的一道风景线。如科大讯飞公司研发的“晓医”导诊机器人,已在国内多家医院“上岗”。它主要通过语音、图像、手势等自然交互方式与患者交流,给出分诊和导诊建议,以节约人力,方便患者就医。更先进的导诊机器人还能通过传感器收集患者的生命体征信息,进行预问诊,提前将患者的基本体征、病情摘要反馈给门诊医生,以提高医生问诊效率[6]。②诊中:AI病历助理可直接将语音转为结构化的电子病历,以实现检查、诊断和病历录入同时进行。如云知声公司开发的智能语音电子病历系统,已在全国100余家三甲医院应用,其语音识别准确率超过98%,大大提高了医生的病历录入效率[7]。 AI手术助理可以让手术医生利用虚拟屏幕、语音识别、手势识别等技术,隔空操作电子设备,从而有效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感染风险。③诊后:患者离院后,AI虚拟助理可对其进行回访及满意度调查,推送医嘱事项、复查提醒、医学科普等[6]。
2.2 智能辅助诊疗
智能辅助诊疗是AI专家系统在医疗领域的重要应用,融合了自然语言处理、认知技术、自动推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其应用模式是将海量的医学知识(包括医学书籍、期刊文献、诊疗指南和临床诊断案例等)导入计算机系统,供其学习、理解和归纳,并自动构建一个类似机器大脑的“医学知识库”,进而模拟医生的临床思维和诊断推理,提出基于患者病史和检查检验结果的诊断和治疗方案[8]。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发的MYCIN系统,是最早用于诊断和治疗细菌感染疾病的AI医学专家咨询系统,尽管它从未在临床应用过,但它的开发原理为专家系统在医学界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北京中医医院与计算机领域专家合作开发了“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首次将医学专家系统应用于我国传统医药领域。进入21世纪后,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逐渐普及,AI辅助诊疗技术发展迅速,各类辅助诊断系统层出不穷,涉及骨肿瘤诊断、胃癌诊断、口腔牙周病诊断、心血管药物治疗等专家系统[9]。其中,IBM公司开发的 “沃森”肿瘤系统(Watson for Oncology),是目前世界上癌症治疗领域最成熟的智能诊疗系统,2016年已入驻中国20余家三甲医院[10]。它可以在数秒钟内阅读患者的文字、影像、病历资料,检索上百万已发表的科学文献及上千万页的肿瘤治疗指南等相关资料,从中提炼出一系列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并同时给出相应的参考文献[11]。目前智能诊疗的核心作用是“赋能医生”,提升其诊疗效率和水平,最终决策权依然在医生[12]。
2.3 智能医学影像
AI在医疗领域应用最热门的场景,当属智能医学影像。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对医学影像进行识别和分析,标注病灶关键信息,以帮助医生快速发现病灶,提高影像诊断效率;二是通过深度学习海量的影像数据和临床诊断信息,不断对AI系统进行优化训练,促使其提高诊断能力,降低复杂疾病的误诊率。目前,AI在医学影像中应用最成熟的领域是肿瘤影像,在肺结节和肺癌筛查、乳腺癌筛查和前列腺癌影像诊断中应用较广,且表现较为突出[13]。从国内来看,腾讯公司作为科技部首批确定的“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单位,自2017年8月推出首款AI医疗产品“腾讯觅影”以来,已构筑起AI医学影像分析和AI辅诊两项核心能力,可辅助医生对早期肺结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结直肠肿瘤、乳腺癌等疾病进行筛查,以及对700多种疾病风险进行识别和预测,实现了从单一病种到多病种的应用扩张[14]。科亚医疗的创新产品“冠脉血流储备分数计算软件” 于2020年1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注册,成为首个获得AI影像Ⅲ类证的产品[15]。该产品采用无创技术,可减少不必要的冠脉造影检查和介入手术,能有效降低诊断成本,减少患者痛苦。
2.4 医疗机器人
1985年,研究人员借助工业机器人PUMA560开展了首例神经外科活检术,成为医疗机器人起步的标志[16]。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医疗机器人已成功应用于外科手术、内窥镜检查、临床康复与护理、医疗救援与转运等多个领域。目前临床应用最多的是手术机器人,以美国的达芬奇手术系统(Da Vinci Surgical System)为典型代表,已广泛应用于心胸外科、泌尿外科、妇科、腹外科等多个领域。该系统是全球最先进、应用最成熟的手术机器人,由外科医生控制台、床旁机械臂系统、成像系统三部分组成。实施手术时主刀医师不与患者直接接触,通过三维视觉系统和动作定标系统操作控制,由机械臂以及手术器械模拟完成医生的技术动作和手术操作。其优点是增加视野角度,减少手部颤动,使手术操作更精细、创伤更小,以减少患者失血量和术后疼痛、组织粘连等。截至2019年10月,全球已有5000多台达芬奇手术系统在临床使用,总手术量超600万例;在中国内地84家医院实现装机102台,香港地区装机8台,共完成手术量达12万例[17]。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患者的增加,康复机器人的应用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分支中外骨骼机器人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如俄罗斯ExoAtlet公司生产的ExoAtlet I,能帮助下半身瘫痪的患者完成基本的行走、爬楼梯及一些特殊的训练动作。ExoAtlet Pro在上述功能基础上,增加了测量脉博、电刺激、设定既定的行走模式等功能[3]。中国也有多家企业进入外骨骼机器人领域,并研发出了新产品,但目前尚无一家企业获得NMPA认证。
2.5 智能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的概念是20世纪60-70年代由美国正式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我国萌芽发展。它是一种前瞻性的健康服务模式,可在健康监测、慢病管理、情绪调节、合理膳食等方面提供医疗护理和咨询指导。传统的健康管理通常在线下进行,效率比较低下,且很难切合用户个性化的真实需求,无法观测和激励用户的健康自控行为,难以达到预期效果[18]。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从门诊和住院电子病历中采集个体化的数据,还可通过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对用户健康数据信息和行为习惯进行监测和采集,并同步传输到医疗健康数据平台进行筛选、提炼和分析,进而预测个体的疾病易感性、药物敏感性等,自动匹配健康管理知识库,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目前国内较为成熟的健康管理平台有觅我(Meum)、Airdoc、医号线、医渡云等,主要应用于疾病风险预测与干预、慢病管理、运动管理、睡眠监测、母婴健康管理和老年人护理等。
2.6 智能药物研发
新药研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从靶点的发现、验证,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和优化,再到候选化合物的挑选和开发,最后进入临床研究,其研发周期长、成本高,且成功率低[19]。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药物筛选的过程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对化合物可能的活性作出预测,进而对比较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进行有针对性的实体筛选,避免了盲人摸象般的试错路径,从而有效缩短研发周期,控制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可建立基于疾病、用药等的数据模型,预测药品研发过程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副作用等,从而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节约时间和成本。目前,美国和欧盟的AI技术已在心血管药、抗肿瘤药、常见传染病治疗药等领域取得了新突破[20]。国内涉足该领域的企业较少,主要提供药物研发的AI技术支持和大数据平台服务,作用于药物研发的一个或多个环节。
3 人工智能在我国医疗领域应用面临的问题
尽管人工智能在我国医疗领域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且在医学影像、辅助诊断、医疗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已较为成熟,正日益展现出高效、便捷、精准、不知疲倦等优势。但就目前来说,我国医疗AI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问题。
3.1 数据利用问题
大数据、算法、计算能力是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石。其中,“海量、精准、高质量”的大数据是人工智能赖以实现的基础。然而,尽管我国拥有十多亿人口、上万家医院,近些年来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积累了大量的医疗健康数据,但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些数据资源的利用率并不高。一方面,医疗数据中绝大部分都是文本、图像、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不同医院之间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即使同一医院的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也可能存在参数设置和图像质量的差异,导致现有数据虽然体量很大,但标准各异,质量参差不齐,经过专家标注过的高质量数据更是有限,影响数据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尽管各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信息化系统,但不同医院的信息化系统由不同的企业承建,企业之间的系统又存在技术壁垒,导致医院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互通程度较低,存在“数据孤岛”现象。由于缺乏合理的数据共享和流通机制,真正能够接触并利用到大规模优质医疗数据的开发者寥寥无几。相当一部分AI企业用于训练的数据只能来自有限的公开数据集或自备数据库,存在着数据量过小、数据质量欠佳、标注不规范等问题,势必会影响机器学习的准确性和普适性,不利于医疗AI的发展。
3.2 算法“黑箱”问题
当前在医疗AI中应用最多的深度学习算法,使用了大规模的神经网络,包含了更多的计算隐层,具备强大的自我学习和自我编程能力,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工智能存在难以捉摸的“黑箱”,即在人工智能输入数据和输出答案之间,缺乏可解释性和透明性。“黑箱”存在的后果就是难以判断人工智能是否出错,且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如果用于算法训练的数据不完整、不准确,或隐含着某些主观偏见或歧视,则有可能在算法训练中复制和放大这些“瑕疵”,最终得出有偏见甚至错误的预测结果,导致某些人群在医疗评估中受到歧视性对待,甚至可能引发医疗安全事故。同时,医疗行业事关人的生命和健康,如果不能让医生了解模型是如何作出决策的,也很难让人们对医疗AI放心接纳。
3.3 标准缺乏问题
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急需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医疗AI的技术标准关系到患者的人身安全,保障人身安全和符合技术规范也是AI投入市场应用的前提。近年来我国已开始着手AI标准化建设,至2018年已发布80余项AI技术标准和规范,但医疗AI的相关标准仍处于在研状态[21]。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应用规范和评价体系,无法对医疗AI的算法模型、产品性能、应用效果等进行验证和评估,不利于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和监管。
3.4 人才短缺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挖掘和培养。据腾讯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白皮书》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约30万人,其中高校学术人才约10万人,产业界人才约20万人,但市场需求却在百万级以上。从人才培养来看,全球共有367所具有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高校(其中美国168所,占45.7%),每年毕业AI相关领域硕博生约2万人,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22]。医疗AI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创新,涉及人工智能和医学这两大复杂学科的深度融合。但目前能通晓这两大学科的人才极其短缺,难免出现AI工程师对医疗领域的问题了解不够,对医疗复杂性估计不足,对医疗流程不熟悉等问题,从而影响AI产品的研发进度和功能设计。从临床应用来看,医务人员对AI缺乏深度认知和相关培训,也会影响其对AI的接受度和规范操作。
3.5 法律与伦理问题
AI的发展和应用是颠覆性的,必然对现有社会秩序和规范带来冲击,产生新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例如:医疗AI在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事实上充当了部分“医”的角色,由此产生了AI的法律地位、侵权责任划分等法律问题,也对医务人员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挑战。数据的采集、传输、储存和应用,带来了患者隐私泄露的伦理风险。当前我国的医疗AI还处于发展初期,产品性能还不够稳定,也不具备情感沟通、逻辑推理、复杂情景决策等高级功能,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存在安全性不够、易用性差、沟通不畅、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要赢得患者信任尚需时日。目前世界各国暂无针对AI技术的专门法律法规,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和伦理规范已不能完全解决医疗AI衍生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以保障医疗AI健康有序发展。
4 结语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无疑提高了医疗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减轻了医生的工作负担,也将为患者带来更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但当前我国的医疗AI还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在应用中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应对。如:从政府层面加强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建设,使医疗AI的发展和应用有所遵循;从研发层面加强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努力破解数据利用、算法“黑箱”等技术难题;在应用层面应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坚持医生的主体地位,并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注重人文关怀,使医疗AI真正为患者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