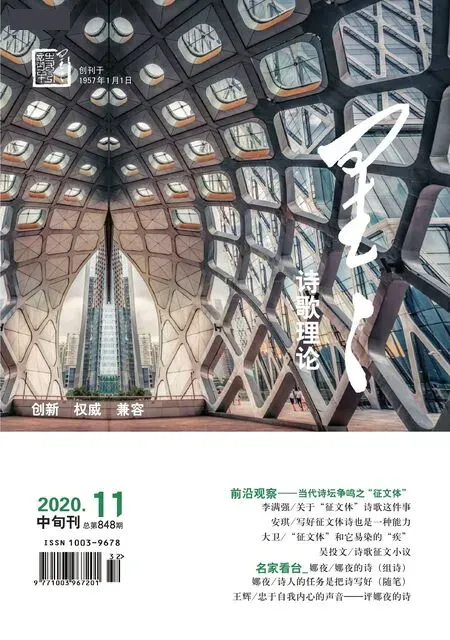当时间成为信仰
——读威廉·斯坦利·默温《关于瞬间的信条》
我信仰普通的一天
此时此地,就是我
我看不见它的途径
我从未看到它如何到达我
它超出一切
我所能感知的知识和真实
它带走此时
离我而去后不知它去向何处
除今天这个地点外我一无所知
只知道环绕我的未知重重
仿佛今天是唯一留下的存在
是属于我的一切,它甚至
赋予我对于今天的信仰方式
只要它在此时此地,是我
(曾虹 译)
关于“信仰”的权威解释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当我们用该定义来对应威廉·斯坦利·默温(1927—2019)这首《关于瞬间的信条》首句之时,会发现不能对号入座。默温所说的“信仰”与思想无关,与宗教无关,只与自己瞬间来临的想法有关。
在很多诗人那里,瞬间的想法的确能转变成一首灵光闪现的诗歌。只是那样的诗歌很难成为诗人的代表作,甚至还不能成为诗人一生中的优秀之作。瞬间毕竟短暂,难说有多少沉淀支撑。大凡有力度和深度的诗歌,要么具有作者对时代的认识,要么具有作者对某一主题的耐心挖掘。从认识和挖掘中诞生的诗歌,会给读者较强烈的打击。诗人自己会重视这样的作品,读者也会在这样的作品里获得心灵共鸣。
默温这首诗与时代无关,甚至与自己一生专注的“深度意象”无关。从诗歌的第一行到最后一行,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意象,通篇是诗人的自我言说。认真细读的话,会觉得这首诗不大像出自默温之手,尽管它带给我们的触动不可低估。默温的朋友和研究者劳伦斯·利伯曼曾建议读者,读默温的诗要以极慢的方式进行。慢读能带来更深的体会。读这首《关于瞬间的信条》同样如此,只是我们会发现,慢读不是我们事先的准备行为,而是默温的诗自有一股内在的幽深之力,它逼迫我们放慢阅读,逼迫我们在诗句中耐心地咀嚼。
当一个人瞬间迸发的力量也能对我们造成逼迫的话,就证明这一力量并非来自瞬间,它经过了诗人不知不觉的酝酿。就这首诗来说,它来自诗人年过八旬后的晚年,这时候的诗人不仅拥有漫长的写作经验,还拥有近乎彻底的人生经验。说诗歌来自经验,就等于说诗歌来自诗人长期的内心积淀。从该诗首行“我信仰普通的一天”来看,进入晚年的诗人已将主题转向了对时间的观察和打量。这不是刻意的行为,甚至可以说,这是任何一个诗人水到渠成的行为。除了时间,再没有比它更重要的晚年打量了。当默温提笔将瞬间当做信条,其实是走过一生后的累积爆发。
我们在童年就被告知要珍惜时间,到晚年时,已经不需要任何人告知,人会对时间有敏锐的感受。每天都值得珍惜,是人到晚年的核心行为。默温这首诗不是想强调珍不珍惜。对人的晚年来说,岂止“珍惜”一词,所有的词在时间面前都变得疲软无力。珍惜是一天,不珍惜也是一天,关键只在于,人对每天会展开怎样的认识。在这里,默温没有将自己摆在倚老卖老的说教位置,相反,他感觉时间始终是人最大的迷惑。“我看不见它的途径/我从未看到它如何到达我”,这样的句子显示了默温对时间的本性揭示和关注。令人惊奇的是,他对时间的感受来自晚年,诗句本身却不像出自老年之手,诗中显示的力量遒劲异常。这让我们体会,诗歌的真正力量不是来自诗人,而是来自诗歌自身的深处。
诗歌的深处也就是人生的深处。若没有站在这一深处,默温不会觉得蕴含时间意味的今天能“超出”“我所能感知的知识和真实”。这的确是晚年的切肤之感,在战无不胜的时间面前,“知识”与“真实”究竟又有多么重要呢?默温的诗句几乎不由自主,沿着感受继续延伸,“它带走此时/离我而去后不知它去向何处”。一个优秀诗人写下的诗句总像是说出我们自己的某种感受。在诗人写之前,我们总是忽略掉很多问题。但被忽略的,不等于不存在。这些诗句让我们陡然发现,那的确不是默温的个人感受,而是所有人的感受,只是我们未能全神贯注地进入。默温不仅挺身进入,还将它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我们会不觉跟随他的感受步步深入,“除今天这个地点外我一无所知/只知道环绕我的未知重重”。这两行诗读来令人惊心动魄。默温在诗歌的行行推进中,也将自己的感受推到核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除了我们所在的今天,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默温令人震惊,是他不仅在年过八旬的晚年依然觉得“环绕我的未知重重”,还唤起所有读者的感同身受。到达“今天”的人,没有谁不被未知环绕。未知所蕴含的,是人在“今天”能拥有什么?在这里,默温的诗句已进入哲学的范畴,他将问题深藏在一个一个肯定句中。这是对认识已达透彻的体现。“仿佛今天是唯一留下的存在/是属于我的一切”。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诗句不乏感伤,但面对人生,感伤是任何人都无法剔除的心灵部分,人迟早要体会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年华流逝,所以“今天”才令人倍加珍视,也令人觉得“今天”的确是自己的全部拥有。
从这里再回到诗歌的第一行,我们不能不承认,默温将“普通的一天”视为信仰,其实是将时间视为信仰,将人生视为信仰。在时间面前,人终将感到自己最终的无能为力。这是时间公平的体现,也是残忍的体现。当默温来到晚年,对时间体会到的深度,不是青年时所能轻易到达。诗歌的结束句是“我对于今天的信仰方式/只要它在此时此地,是我”。若不慢读,读者不一定能体会其中蕴含的巨大悲伤。默温说出的时间认识“是我”,就已将他对时间甚至一生的复杂感受全部说了出来。希望挽留时间的人只是为了活下去吗?我忽然想起默温在另一首同期所写的诗中说道,“我所抵达的并非智慧”(见《没有月亮的夜晚》,曾虹译),这同样是时间赋予的认识。当默温以为自己一生没有抵达智慧是一种谦卑的话,我们会发现,走到晚年的默温起码抵达了太多人一生也抵达不了的认知和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