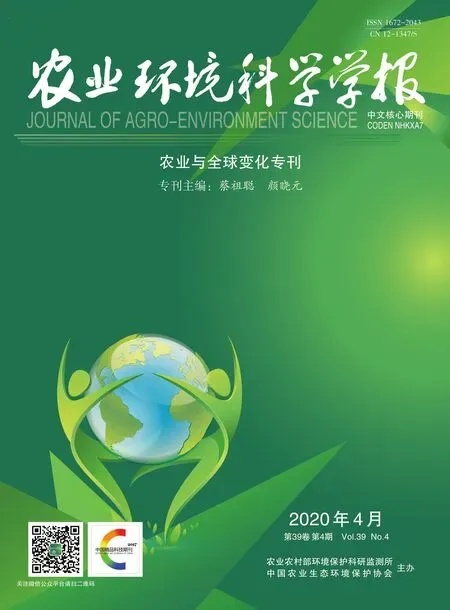土壤有机碳时空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张 秀,赵永存*,谢恩泽,彭雨璇,陆访仪
(1.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210008;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SOC)是土壤肥力形成、粮食生产和土壤健康的基础,适宜的SOC 含量是土壤提供最佳的植物生长条件、养分循环以及有效水分渗入和存储的重要前提条件[1]。同时,全球SOC 库容量巨大(1395~2200 Pg[2])并且较为活跃,SOC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对大气二氧化碳(CO2)浓度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在全球碳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等进程快速发展导致的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方式及强度变化等已经对SOC变化产生深刻影响[3],随着人们对SOC 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土壤健康、发挥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重要性的综合认知逐步加深,SOC时空变化规律研究逐渐成为农业、生态、环境、全球变化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科学前沿[4]。
1 SOC时空变化影响因素
SOC时空变化主要受气候、母质、地形、生物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和管理措施等因素影响[4]。SOC变化的影响因子作用于不同的时空尺度,因此,SOC 时空变化模式也具有尺度效应。大尺度的SOC 时空分布模式主要受气候因素控制,而相较气候因素而言,土地利用及管理措施等人为因素通常在相对小的尺度上影响SOC 时空变化,但其影响强度往往超过气候因素[4]。
气候因素对SOC 时空变化的影响主要由温度和降水变化导致,因为温度和降水影响植被生物量及凋落物分解、土壤温度及湿度,从而影响SOC 的输入和分解过程。温度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性和土壤呼吸而对SOC 含量产生影响[5]。温度升高SOC 分解加速,但温度升高的同时土壤中植物残体分解速率也增加,从而提高土壤碳的归还量,因此,特定环境条件下SOC 对增温的响应可能是正反馈,也可能是负反馈[4-6]。降水则直接影响土壤水分状况以及土壤固、液、气的比例。一般而言,土壤水分含量适宜有利于SOC 积累,但当土壤水分含量偏低时,SOC 分解加速,从而降低SOC 含量[4]。此外,温度和降水对SOC 时空变化的影响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综合过程。
土地利用及管理措施变化是影响SOC 时空变化的最重要人为因素。土地利用变化通过改变土壤理化属性而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及土壤微生物活性等,从而影响土壤碳输入及SOC 分解[7-9]。当森林或草地转变为耕地时,SOC 含量下降高达30%~80%[4],这主要是因为林地或草地转换为耕地后土壤侵蚀加剧、土壤碳输入降低、SOC 稳定性变差、土壤温度升高和通气量增加,而当耕地转变为林地或草地时,土壤可蚀性降低,土壤结构得到改善,碳输入增加,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SOC 累积。传统耕作方式往往导致SOC 含量降低,而少、免耕等保护性耕作对土壤扰动较少,有助于减缓SOC 分解,从而有利于SOC 积累[10-11]。有机肥施用不但可以快速提高SOC含量,而且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及作物生长环境,促进SOC 的积累,而秸秆还田有利于增加农田土壤碳输入,促进农田土壤固碳[12]。
2 SOC时空变化估算方法
基于SOC 时空变化驱动因素认知以及土壤等数据的可获取性,目前SOC时空变化主要采用过程模型模拟和数字土壤制图(Digital soil mapping,DSM)两类方法进行量化估算。过程模型模拟采用整合了土壤有机质(Soil organic matter, SOM)动态机理和过程的模型,以气候、土壤、管理等模型驱动数据驱动过程模型实现SOC 时空演变预测。DSM 方法则通过多时段SOC 样点数据空间预测后再差减或者在DSM 模型中整合时空替代来实现SOC时空变化估算。
2.1 过程模型模拟法
相对于SOC 的巨大库容及固有变异性而言,SOC变化的数量相对较小,同时,SOC 库的变化也比生物量及凋落物碳库慢很多,需要长期观测才能识别SOC变化,因此,长期定位观测是监测SOC 演变的理想手段[13]。然而,目前的长期定位试验及监测网络由于其试验规模、监测点数量、持续年限及能代表的气候、土壤及管理条件等因素限制,还难以通过直接内插或外推的方法来检测大尺度上SOC的微小变化。因此,过程模型模拟依然是大尺度SOC 时空变化估算的推荐方法[13]。
按过程模型是否明确表达了微生物的分解作用,SOC 过程模型可大体分为经典过程模型和微生物模型两大类。经典SOC 过程模型整合了SOM 动态机理和过程,能反映土壤、气候、管理措施等因子空间变异性对SOC 动态变化的影响。经典SOC 过程模型(比如CENTURY、RothC)最初用来模拟长期试验中农业管理措施对土壤碳、氮动态及养分循环的影响,随后被整合到生态系统模型和地球系统模型中用于预测区域/全球尺度的SOC 时空动态[14]。经典SOC 模型将碳库划分为分解速率不同的概念化分库,各分库大都采用一级动力学方程描述SOC 的分解,并通过影响SOC 分解及稳定性的外部环境因子(比如气候、土壤属性、管理措施等)对各分库的分解速率常数进行修正[15]。经典SOC 过程模型中,微生物作为分解者的作用被隐含在不同的分解速率常数中,没有明确表达。目前新出现的微生物模型,比如CON(Conventional model)、GER(German)、MEND(Microbial ENzyme-mediated Decomposition)和MIMICS(MIcrobial-MIneral Carbon Stabilization model)模型等,则直接把土壤碳周转和微生物生物量及生理机能耦合,从而反映了微生物在SOC 分解和稳定化中的作用[16-20]。微生物模型具有解释爆轰效应、环境适应以及土壤呼吸对降水脉冲响应的潜力[21]。同时,微生物模型对探讨全球变暖与SOC间的反馈非常有效,因为温度直接影响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理特性[22]。然而,与经典SOC 过程模型相比,微生物模型会产生显著不同的SOC 动态模式,比如,对扰动的振荡响应以及对碳输入响应的不敏感性等[23]。
2.2 DSM方法
DSM 是实现土壤调查数据由点到面拓展的重要技术手段。多时段SOC 样点数据空间插值后再差减即可实现SOC 的时空变化估算。DSM 模型主要基于Jenny 提出的土壤形成机理clorpt 方程,即:S=f(cl, o,r,p,t),其中S 为土壤类型或属性,cl、o、r、p、t 则分别代表气候、生物、地形、母质和时间,该方程反映了5大成土因素对土壤形成的综合影响。McBratney 等[24]系统总结了现代土壤信息获取手段、土壤环境数据及空间预测方法等,在clorpt 方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土壤制图的SCORPAN 模型框架,即:S=f(s,c,o,r,p,a,n),其中,S 为土壤类型或属性,s、c、o、r、p、a 和n 则分别代表土壤相关的其他信息、气候、生物、地形、母质、时间和空间。随着土壤及环境信息现代获取技术以及数学建模方法的快速发展,SCORPAN 模型框架在包括SOC 等关键土壤属性的土壤制图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验证[25]。
早期的DSM 方法估算SOC 时空变化主要以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MLR)和地统计学普通Kriging 两类方法为主,随后,整合这两类方法建立SOC 空间分布预测混合模型以提高SOC空间表达精度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回归Kriging(Regression Kriging,RK)和带有外部趋势的Kriging(Kriging with external drift,KED)[26-27]。近年来,随着现代土壤调查以及遥感、无人机、近感等非侵入式调查技术的快速发展,土壤信息的获取逐渐呈现多手段、多来源、多尺度、多维度、多类型、大信息量等新特点,使得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NN)等大数据机器学习方法在SOC 等关键土壤属性的时空变化预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5]。同时,以SCORPAN 模型框架为基础,除了可以通过DSM 方法对不同时段土壤采样点SOC 实测数据插值后再差减实现SOC时空变化估算外,还可结合时空替代(Space-for-time substitution)[28]来实现SOC时空演变系列重建及未来变化趋势预测。“DSM-时空替代”的基本思想是,在建立的SCORPAN 模型的基础上,假定土壤类型、母质、地形等“静态”的模型输入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进而通过将模型中“动态”的输入变量(比如土地利用、土壤碳输入、温度、降雨量等)替换为待估算年份的对应变量值,以实现SOC 时空变化的预测。
3 研究进展
准确地量化SOC时空变化是土壤功能、土壤健康及土壤安全评估和碳循环及气候变化研究等的重要基础。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利用方式及不同生态系统下SOC的时空变化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由于大尺度SOC 时空变化研究对于土壤资源管理战略决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的重要性,本文重点介绍大尺度SOC时空变化的研究进展。
3.1 整合SOC经典过程模型的时空变化研究进展
Todd-Brown 等[29]基于温度和湿度敏感性简化的11 个ESM(Earth system model)模型分析了全球SOC时空变化及气候的影响,结果表明,在RCP8.5情景模式下21世纪末全球SOC库变化范围是-72~253 Pg C,其中高纬度地区SOC 库变幅最大,为-37~146 Pg C。Ren 等[30]采 用DLEM(Dynamic land ecosystem Model)过程模型模拟了1901—2010 年间全球农田SOC 时空演变,发现最近10 a全球农田SOC储量及密度分别比20 世纪早期增加了125%和48.8%,其中农田面积扩张及氮肥用量增长是SOC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气候变化仅导致约3%的SOC 储量损失。Wang 等[31]利用RothC 模型及全球0.1°(经纬度)土壤属性数据模拟了1961—2014 年间不同碳输入情况下全球农田表层(0~30 cm)SOC 的动态变化,分析了管理措施变化对SOC 时空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当秸秆还田比例分别设定为30%、60%、90%时,全球农田平均SOC 密度增幅分别为0.22、0.45 mg C·hm-2和0.69 mg C·hm-2,其中,美国中部、西欧和中国北部地区SOC增加显著,南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SOC含量也有一定升高,但赤道地区SOC 含量明显减少。Smith 等[32]采用CENTURY模型模拟了加拿大农田1970—2010 年的SOC 时空变化,发现当前加拿大农田SOC 接近平衡状态,其中,1970、1990 年 和2010 年 的SOC 变 化 速 率 分 别为-67、-39 kg C·hm-2和11 kg C·hm-2,2000 年起由碳源转为碳汇与免耕面积比例的稳定增长密切相关。Ogle 等[33]则采用CENTURY 模型模拟了美国农田1990—2000 年SOC 变化,并基于MC 方法评估了SOC模拟的不确定性,结果表明,1990—1995 年及1995—2000 年2 个时段内,美国农田SOC 增加速率分别为14.6 和17.5 Tg C·a-1,其不确定性分别为±22%和±16%,SOC 的增加与美国实施的休耕保护计划(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密切相关。Xu 等[34]基于DNDC 模型和1:100 万土壤数据库,模拟了1980—2008年中国水稻土表层(0 ~30 cm)SOC时空演变,结果表明,1980—2008 年中国水稻土的平均固碳速率为5.0 Tg C·a-1,28 a 间83.3%的水稻土表现为固碳,16.1%的水稻土丢碳,而0.6%的水稻土表层SOC 保持平衡状态。Yu等[35]则基于Agro-C 模型模拟了中国农田的SOC 时空演变,结果表明,1980—2009 年间中国农田表层(0~30 cm)SOC 平均固碳速率为24.3(11.0~36.5)Tg C·a-1。总体来看,经济和政策驱动的土壤碳输入增强是中国农田土壤总体固碳的主要原因[12]。
3.2 基于微生物模型的SOC时空变化研究进展
微生物模型有助于探讨气候变化与SOC 间的反馈作用[20],运用微生物模型分析全球SOC 时空变化已经成为大尺度SOC 时空变化研究的新趋势[19-22]。Wieder 等[19]通 过CLM4.5(Community Land Model4.5)过程模型和MIMICS 微生物模型模拟全球SOC 时空变化的分析发现,无论是CLM4.5模型还是MIMICS模型,高纬度地区都表现为明显的丢碳,但与CLM4.5模型相比,MIMICS 模型模拟的全球尺度SOC 含量与HWSD(Harmonized World Soil Database)数据库SOC观测值更为接近。Wang 等[36]采用整合了MEND 微生物模型的TRIPLEX-MICROBE 模型预估了21 世纪全球SOC 及微生物量碳(Microbial carbon,MBC)时空变化,结果发现,RCP2.6、RCP4.5 和RCP8.5 3 种情景模式下,全球SOC 库由2013 年的1099 Pg C 分别降低到2100 年的1032、996 Pg 和924 Pg,分别降低了6.1%、9.4%和15.9%,但MBC库则由2013年的20.89 Pg C分别增加到2100 年的23.78、25.13 Pg 和29.16 Pg,分别增加了13.8%、20.3%和39.6%,因此,尽管SOC 降低主要发生在北极等高纬度地区,但随着赤道至中纬度地区的气候逐渐变暖,北半球变成更大的碳汇,有助于补偿高纬度地区的碳损失。与经典SOC 过程模型的应用相比,基于微生物模型的SOC时空变化研究不仅着重分析了SOC 对温度变化的响应,更加关注了SOC 对微生物碳利用效率(Microbial carbon use efficiency,CUE)变化的响应。比如,Allison 等[16]应用AWB 和CON 模型模拟了SOC 对全球气温平均升高5 ℃的响应,结果发现,微生物生物量和降解酶的下降可以解释观测到的土壤碳排放随增温衰减现象,同时CUE 的降低限制了微生物分解者的生物量,减少了土壤碳的损失。然而,微生物的适应或微生物群落的变化也可能导致CUE 向上调整,抵消微生物生物量下降,从而加速土壤碳损失,因此,Allison 等[16]认为SOC 对气候变暖的响应主要取决于CUE。Li 等[37]则通过比较4 个微生物分解模型,阐述了一阶分解模型和其余3 个不同复杂程度的微生物分解模型在土壤碳分解中的作用,以及预测短期到长期的土壤碳的时空动态变化中的重要性。此外,微生物模型扩展至全球尺度时,模型结构评估和CUE 等关键参数优化的重要性也基本形成了共识[36]。
3.3 基于DSM-时空替代的SOC时空变化研究进展
Stockmann 等[38]基于具有明确采样时间的63 503个样点SOC 数据、气象数据、DEM 计算的地形因子及MODIS 土地覆盖数据,采用SCORPAN 模型框架的回归Kriging 方法建立全球SOC 空间预测模型,通过土地覆盖数据时空替代预测的2001年和2009年全球表层(0~10 cm)SOC 含 量 分 别 为3.94%±0.03% 和3.76%±0.03%。采用类似的方法,Yigini 等[39]基于欧盟LUCAS 表层土壤数据库的22 300 个样点土壤数据和气象数据、DEM 及土地利用数据建立SOC 的回归Kriging 空间预测模型,通过时空替代方法分析了未来气候及土地覆盖变化对SOC时空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RCP 2.6、RCP 4.5、RCP 6.0 和RCP 8.5 4 种气候情景以及LUMP(Land Use Modelling Platform)生成的当前(2010 年)和未来(到2050 年林地和半自然土地增加3.08%,农用地减少4.16%,牧草地减少5.18%,湿地减少0.31%)两种土地覆盖情景下,未来40 a 欧洲表层(0~20 cm)SOC 储量总体呈增加趋势,不同情景预估的SOC 库增幅为7~13 Pg,其中仅欧洲南部部分地区SOC 微降。Sanderman 等[40]基于全球标准化土壤剖面数据库WoSIS(World Soil Information Service)以及全球气象、地形、岩性数据和全球环境历史数据库HYDE(History Databas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采用RF 算法建立全球SOC 时空预测模型,通过HYDE 土地利用数据的时空替代分析了土壤的农业利用对全球SOC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过去1.2万a 以来农业利用导致全球SOC(0~200 cm)损失133 Pg,其中最近200 a内SOC损失速率增加最为显著;放牧地和农田的扩张对SOC损失量的贡献大体相等,同时,丢碳热点区与一些主要的农田区及半干旱放牧区的空间分布相一致。Adhikari等[41]基于威斯康星州的280 个土壤采样点数据以及气候、母质、地形和土地利用等17 个环境变量数据建立SOC 预测的回归树模型,通过气象及土地利用数据的时空替代预估了IPCC SRES A1B 情景下表层(0~30 cm)SOC 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到2050 年,该区SOC 总体增幅为20 Mg C·hm-2,而SOC 降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湖区及森林生态区。Chen等[42]基于2017年湖北省1872个农田样点表层(0~20 cm)SOM 实测数据以及气象、DEM 和MODIS 遥感影像等辅助数据,采用GBRT(Gradient boosting regression tree)算法建立SOM 空间预测制图模型,进而通过对气候因子、植被因子及土地利用的时空替代分析了2000—2017年农田SOM 的时空变化,结果发现,2000—2017 年SOM 平均含量总体呈增加趋势,净增幅为0.26 g·kg-1,但SOM 时空变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其中南部地区SOM 增加,而中北部地区SOM降低。
4 研究展望
4.1 加强SOC 周转机理研究是提升SOC 时空变化估算精度的关键
经典过程模型能够有效揭示不同尺度管理措施和土地利用变化对SOC时空变化的影响,但没有明确表达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因此,在模拟SOC 对温度变化响应的敏感性方面仍存在问题,特别是在难分解/惰性碳库对温度变化响应的敏感性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MIMICS、MEND 和GER 等微生物模型则明确表达了微生物作为分解者的作用,这对于探讨SOC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微生物模型没有像经典过程模型那样考虑管理措施对SOC 时空变异的影响,此外,微生物模型还存在振荡效应及对碳输入响应的不敏感性等问题。而近年来在大尺度SOC时空变化估算中应用的“DSM-时空替代”方法尽管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但由于环境因子及管理措施对SOC 变化的影响是一个累积、渐进的过程,加之环境因子影响的“滞后效应”,直接将模型中“动态”的输入变量替换为待估算年份的对应变量值的替代方法,往往导致SOC估算结果在较短的时段内就呈现出强烈的波动性。因此,进一步加强SOC周转机理研究,以便在估算方法中更好地体现SOC周转机理和过程的新认知,是未来进一步改进现有SOC时空演变预测模型结构以提升SOC时空变化估算精度的关键。
4.2 建立统一时空基准的高分辨率模型驱动数据是实现SOC时空变化精细模拟的基础
气象、土壤属性及管理措施等基础数据是驱动模型以实现SOC时空变化估算的基础,模型驱动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估算结果的可信度[43]。然而,目前可用的模型驱动数据,特别是大空间范围内的土壤和管理措施数据的分辨率依然偏低。比如,目前全球土壤剖面数据收集最为详细的全球标准化土壤剖面数据库WoSIS(World Soil Information Service)中有SOC 测定值的剖面点也仅有82 643个,仅占该数据库收集剖面点数量的约40%。而中国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土壤剖面点有10 万多个,但目前用于绘制国家土壤性质图的剖面数据却不超过9000 个,其中能公开免费获取的数据则更少。此外,尽管目前全球尺度上有多个土壤数据库可用于驱动SOC 模型,比如,HWSD、GSDE(Global Soil Dataset for Earth System Model)、Soilgrids、WISE(World Inventory of Soil Emission Potentials Database)等,但由于土壤性质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都具有很大的空间异质性,加之不同土壤数据库中土壤属性测定时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导致统一时空基准的全球初始土壤条件数据仍然缺乏。比如,就土壤黏粒含量及其空间分布而言,IGBP-DIS(Data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与GSDE数据库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44];而WoSIS 数据库中SOC 测定年份明确的仅有69 840个剖面,且测定时间从1900年至2015年不等。因此,建立高分辨率、统一时空基准的模型关键驱动数据,比如初始土壤条件等,是未来实现大尺度、高空间分辨率SOC动态模拟研究的重要基础。
4.3 完善不确定性信息是提升SOC 时空变化估算结果科学性的保障
由于当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认识、土地利用变化判别、人为活动影响、深层SOC 变化以及估算模型的有效性、尺度转换和输入数据误差、空间分辨率及可获取性等因素限制,导致SOC时空变化估算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目前大尺度长时间系列SOC 时空演变估算中所提供的不确定性定量信息依然偏少,而综合考虑模型结构、内部参数、输入数据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评估则更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在不同尺度土壤碳分区管理决策中的实际应用效果。此外,土壤数据作为影响SOC 时空变化估算结果不确定性的最重要驱动数据之一,关于土壤数据聚合(Soil data aggregation)对SOC 时空演变估算影响的不确定性及尺度效应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比如,土壤数据聚合影响初始SOC含量的局部空间变异表达细节及空间变异表达的不确定性,将会对SOC 时空演变模拟结果产生深刻影响。然而,现有基于土壤图的SOC 时空变化研究中,均假定土壤制图单元的初始SOC 含量均值估算没有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全面反映土壤属性信息缺失对SOC时空演变模拟影响的不确定性,进而制约了SOC时空演变的尺度效应研究。因此,完善SOC时空变化估算的不确定性信息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