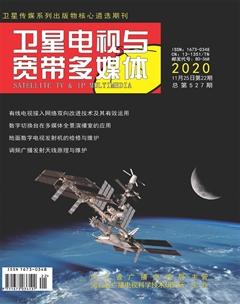论徐浩峰武行电影的追寻与创新
【摘要】在当下武侠电影的现状背景下,徐浩峰带着三部武行电影“开宗立派”。本文以《师父》为例,阐述影片对于传统的继承与保留,突破与创新,在总结其自觉的商业转向和面对历史的尊重与思考上得出结论,认为最终武侠(武行)电影的发展创新应是艺术性、商业性和观赏性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武侠电影;徐浩峰;《师父》;创新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0.22.047
中国武侠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电影类型,可谓是世界电影文化之林中的“一枝独秀”。但当今武侠电影的发展几乎进入瓶颈期,直至徐浩峰带着他的以纪实风格著称的武行电影《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师父》,以“开宗立派”之势闯入大众视野之后,犹如给武侠电影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人看到了新的探索和希望。
1. 武侠电影的窠臼
中国武侠电影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在不同时期的创作背景下,它为中国电影的历史长卷留下了缤纷绚丽的图景。然而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自身和外部的种种原因,都不可避免地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困惑,甚至导致其进入瓶颈,武侠电影也不例外。有评论指出,近年来武侠电影,整体上分析无论是口碑、票房,还是影响力,都较之前有不小的缩水,而且意趣审美水平不高,文化功能有所减退。武侠电影近年来从作品质量到关注度的持续走低,就使有着武侠文化和传统的中国电影不得不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局面,未来的发展又将何去何从?
武侠电影自身价值观的不完善,甚至说是缺失,以及武术本身又与科技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使其真实性存在着争议,这些都影响着武侠电影叙事框架的立足与定位。而且由于电影是艺术、科技与商业的结合,那就不可避免的在创作完成的瞬间即成为商品,商品就需要在市场上流通,就需要受众来买单。而经研究发现,武侠电影的历次发展高潮时期,都伴随着完成观众的心理补偿任务。但现在的国家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人们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那种任人欺辱、战战兢兢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人已经不再需要这种由于弱小而向往强大的心理补偿了。
徐浩峰武行电影的出现,为跳出窠臼提供了可能。他拍“武行”,而非“武侠”,表现的是民国时期一种实在的行业和从事该行业的特定群体。所以体现在人物塑造上,没有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设置,而是性格更加丰满、多元的“圆形人物”,主人公也不是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为行动的原动力,而是以人本身在现实中的生存与发展为基础而进行选择与规避的。“找寻”才是推动着人物做出选择的初衷,而“被判决”是人物最终的结局。就像电影《师父》中,以主人公陈识的个体命运,折射出整个社会时代的纷纭变换。让咏春拳在天津立足是他此行北上的目的,培养徒弟而后牺牲徒弟是他实现目的所采取的必要手段,而陈识最终认清现实并被行业和时代抛弃是他不得已的结局。
2. 徐浩峰武行电影的叙事特点
徐浩峰武行电影不同于传统武侠电影,更多的是在解释什么是“武行”,什么是“武行的规矩”。其作品当中既有委婉蕴藉的东方表达的美学传统,含蓄节制的叙事策略,又有在充分历史研究基础上,有源有头的武术积淀。其中没有程式化、舞台化的武打动作编排。没有威亚、特效等对视觉呈现的加持,有的是纪实风格的影像表达,以及作品所表达出的隽永的武行精神。在大环境的时代激流地冲击下,传统侠义文化的生存困境,给落魄的武林和已逝的江湖,留下最后的血气、高贵与尊严。
2.1 以武代言的叙事方式
在面对已发展了将近百年的传统武侠电影的“旧规矩”面前,他选择了既有所突破发展,又有所继承保留,这便是徐浩峰电影所体现出的分寸感。以武代言,便是徐浩峰武行电影对于分寸感的一种恰当诠释,将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怀寓于人物的武术动作之中。在武打形态设计方面,根据角色身份的不同,设计出富有变化和层次的视觉呈现,将导演对社会制度、礼乐文明、信仰道义的思考蕴藉其中,传递出对武人、武行、武术与武德的深刻反思。
徒弟耿良辰踢馆比武,用单锋剑对八斩刀,用的是标准的民国时期武馆比武的“挟刀揉手”的形式,是以短对短,是遵循武德道义的实力较量。这其中没有制度跨越,等级突破,有的是对一个武术门派的敬畏与期待,是对武人自身实力的考察和认可。而师父陈识在巷战之中,先以八斩刀对阵日月乾坤刀、三尖两刃刀、岳飞刀、方天画戟等,后又以子午鸳鸯钺对阵战身刀,都是在以短对长。表现出在原有规矩和等级秩序中,本就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为什么南方小拳种,就要面对天津武馆十九家的层层刁难?为什么“成就一个门派”就要以“毁一个天才”为代价?在对抗过程中更是步步惊心、困难重重。所有可以交换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弃的。对于陈识而言,在天津开武馆,为咏春拳博身份,是要以牺牲徒弟作为交换的筹码。起初,他认为徒弟是个“小人”,“毁了不可惜”,但后來醒悟并非如此,徒弟被害,他要报仇。在武馆开业当天,他放弃了来到天津蛰伏许久的目的,以“万人敌”的姿态,对天津武行发起了挑战,靠的就是武人对不可放弃的东西——“信仰”的坚守与执着。
2.2 隽永的武行精神
首先源自《师父》中对民国武人,天津武行的真实、细致地描绘。武人高贵优雅,精致体面,处处体现出的仪式感,让人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不由得对武林的生而崇高,感到由衷的尊崇。其次源自片中人物的抗争,郑山傲作为武行老大,他已经发现了武行规矩的弊端——“不教真的”,这件事让他深感危机重重。所以,对于陈识想要在天津开武馆一事,有个条件就是“得教真的”。郑山傲虽然已到了该隐退的年纪,但还想为武行留下些“真东西”。陈识的抗争则是本片的叙事线索,他要重振家业,要报答师恩,要让咏春拳在天津从无到有,陈识在为咏春拳和他自己寻一个身份认同。
其实导演本人也在抗争。在武侠电影领域,面对夺人眼球的特效,面对商业市场的压力,他选择用有史可依的武打招式和一拳一脚,实打实凿的武术功夫,来呈现一个行业真实的生存状态,徐浩峰在为武行寻一个历史归宿。
英雄并不是没有弱点和缺憾,没有顾虑与畏惧,而是面对选择深知结果如何,笃定心中信念,并愿意且能够为此承担一切后果的人。《师父》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着各自性格和利益驱使下所形成的阴暗面,但他们通过信念所做出的选择与决定,使其周身散发出不可磨灭的“英雄之气”。
陈识认为自己是“一个门派全部的未来”,要凭着一己之力,在天津武林为咏春拳扬名立万。外地小拳种要在武行规矩林立的天津搏名,他深知此次北上的艰难,但他丝毫没有退缩。在街巷之中,他一边用“六点半”棍法对战众人,一边于长椅之上平静地向妻子赵国卉道出这次北上的来龙去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振家业、报师恩、扬咏春,那种娓娓道来的从容和缓与笃定不移的神态,都透露出这个男人铮铮的英雄之气。可后来面对徒弟被害死的事实,陈识后悔于自己没能保护好他,使得影片一开始为观众塑造的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的近乎无情的人物形象发生了改变,最后他发现寄托着理想的武行与武林在时代现实的冲击下已不可挽回,但依然将自己一身“真东西”传给天津武行,离开之后,留下了令人望而生畏的遗憾和希望。
徒弟耿良辰,是因为觊觎师娘赵国卉的美貌,才萌生了学拳的念头。但练武之后,每日挥刀五百下,敬师父师娘为神,“师娘就是师娘,再也不是什么漂亮女人了”,这体现了他对武德、武道的参悟和敬畏;之后遭人暗算,明知向前是生,回头是死,但他还是转身回到天津,决不能在危难之时弃家而逃。可以高贵地失去生命,但绝不能背弃规矩苟活于世,也让人们看到了真正武人的操守。
3. 徐浩峰武行电影的自身尝试与展望
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输出的类型电影——武侠电影,它承载着更多的目光与期待。在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下,包括徐浩峰武行电影在内的中国武侠电影,如何突出重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虽然这关系到事物客观的发展规律,但从徐浩峰武行电影自身主动的商业尝试,到其将继承传统与思考历史地更好融合,再到艺术性、商业性、观赏性地和谐统一,都可以视作是徐浩峰武行电影及中国武侠电影的主观能动地寻求。
3.1 于商业尝试之中“博一条出路”
与徐浩峰导演的前两部影片《倭寇的踪迹》和《箭士柳白猿》相比,《师父》在电影的商业方向做出了调整与努力,徐浩峰是清楚商业性对于电影的重要作用的,因为他说过:“他被告知,自己从事的是商业,作品即商品” 。所以,在商业市场等因素和电影自身商业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了更具商业气息的《师父》应运而生。
起用知名的演员参演,提高关注度。对于非专业领域的普通观众而言,演员是最直接的将作品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那群人,他们对于演员的记忆和兴趣点也就更加深刻。陈识的扮演者廖凡,《师父》是他自《白日焰火》在柏林电影节获得影帝之后,公映的第一部影片;师娘赵国卉的扮演者宋佳,形象端庄、气质优雅,同时演技出众;“老戏骨”金士杰、蒋雯丽也都贡献了精彩的表演,这都成为了票房号召的重要筹码,也增加了观众和市场的更多期待。
《师父》原著小说中武打设计的部分是拳斗,而电影改编拳斗改为械斗,是出于可看性考虑。“八斩刀”有着很强的造型性,由它引出的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武艺的巷战对决,给观众带来了十分震撼的视觉刺激,这种奇观化的表达,给观众的猎奇心理以一定的满足。在改编上还将邹馆长由男人改成了女人,在一个可以说全部都是由男人构成的世界中,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却是一个女人,不同于观众观影经验而形成的观影期待,这种巨大的反差,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反而让观众有了新的兴趣点。
在情节方面,线性叙事更为连贯、紧凑。师父陈识,北上天津,想为詠春扬名,以报师恩,天津武行“头牌”以“毁一个天才,成就一个门派”为前提同意。在这一过程中,徒弟被害死,陈识领悟到时移势易,武人、武行、武林已然不复当年。他放弃“开宗立派”,选择为徒报仇,离开天津。这样环环相扣地讲完一个故事,并在结尾依然留有悬念,让观众意犹未尽。相较于《倭寇的踪迹》和《箭士柳白猿》当中的哲学化、留白化的艺术表达,《师父》的故事讲得更清楚直白,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情感表达更为直接明确,容易引起观众共鸣。在《师父》中,处处都体现出“规矩”二字,武行的规矩,人情世故的规矩,时代变革的规矩等等。但有了有情、有温度的人物关系,也让故事更加的深刻且柔和,刚柔并济,精神升华。师父与师娘,徒弟与茶汤女,以及师徒之间,这三对人物关系所传递出的情感、道德、责任,都让人们在为武林落魄,礼崩乐坏感到无奈与悲哀的同时,看到了人性的光芒,理想的道义和情感的温度,给观众留下了回味与思考的空间。
3.2 价值观的重塑
价值观的重新树立,对于武侠电影的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类型电影,其灵魂都是价值观。而每个故事的高潮,即是价值观的冲突,而能否碰撞出新的价值观念,就是这个故事中最想要传递的核心要素。《师父》中,时代的更迭,导致传统的价值观也随之崩塌,武行从而寻求建立现代性的契约观念,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一种职业,给整个武林立了规矩,做了表率。同理,现代武侠电影的发展,也希望能够给整个现实社会的运作以精神支撑,贴近生活,指导生活。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任何艺术都根植于这片沃土之中,对于天地人的敬畏,对于礼法的规范与约束,个人修养、意趣、品味的更高追求,不仅关乎武侠(武行)电影,更是中国电影及其他艺术领域都应自省的重要内容。
3.3 艺术性、商业性、观赏性的和谐统一
电影是艺术、也是商品,它需要被人所欣赏接受,是每一个电影创作者都知道的事实。艺术性不代表曲高和寡、难以理解;商业性不代表粗制滥造、审美肤浅;观赏性也不仅仅单纯作用于视觉。任何一部优秀的影片必将是这三者的和谐统一。
艺术性:包括对于传统武侠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于当下社会依然有可供精神寄托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武人高远的精神追求,深远的底蕴修养,长远的文化求索等,都为武侠(武行)电影艺术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营养。商业性:必要的打斗场面,猎奇与窥视心理的满足,明星的加入等,以及最重要的文化价值的传播与输出,建立在商业性价值的基础上,以求得更好地发展。观赏性:一方面,它需要建立在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基础之上,有着良好的艺术品质和巨大的商业价值,那其观赏性必然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在于导演个人艺术风格的独特与发挥。导演“作者化”的风格演绎,既是他的特色,又是他的招牌,就像徐浩峰的以纪实风格著称的武行电影。例如《师父》中对武打部分的展示,没有快速剪辑,没有花俏的特效,这恰好符合民国武行的现实样貌,反映的是武术技击的真实状况。只有第三者视角下的冷静、直观的长镜头,而这恰好就是它最具观赏性的部分。
武行电影在电影片种划分的大范畴里还是属于武侠电影,所以武侠电影在未来长足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将三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艺术性是根,电影是“第八艺术”,艺术性定是立命之本;商业性是茎,它支撑其运作和发展,让它“枝繁叶茂”;而观赏性就是这棵大树的叶,这样等到以后“开花结果”,武侠(武行)电影才能“独木成林”。
4. 结语
徐氏武行电影面对传统桎梏,勇于突破,积极创新;面对文化精髓,竭力保留,经典传承。虽然我们遗憾于《师父》的结局是陈识走了,也带走了武林最后的生气;但现在我们庆幸,徐浩峰带着他的武行电影来了,也带来了新的蓬勃与希冀。
参考文献:
[1]徐皓峰.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5页
作者简介:崔芳菲,北京市东城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