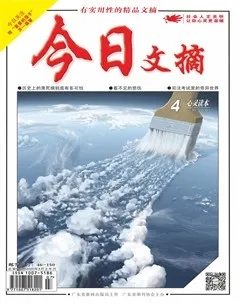换一张新脸,真能开始新生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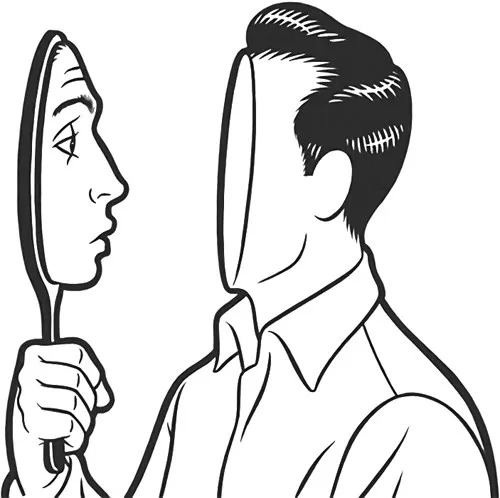
2016年4月22日,一个女人死了。
她原本是个很普通的女人,当过裁缝,离过婚,有两个孩子,养着一条拉布拉多犬。
5个月后的9月6日,女人的死讯才公布出来。这一天,全球有大约16万人去世。但她的死讯,成为了全球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
女人名叫伊莎贝拉·迪诺瓦尔,法国人。她养的那条爱狗塔尼亚,曾经撕碎了她的脸。
面部严重受损后,伊莎贝拉在法国一家医院接受手术,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的脸。作为全世界第一例接受“换脸术”的患者,伊莎贝拉跟这张脸相处了10年。
脸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标识。据心理学家介绍,人类是极端的视觉生物,灵长类动物大脑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便是过半的大脑皮层都用于处理视觉信息。在了解一个人之前,人们通过外貌猜测他们的性格、生活。人们根据一个人的脸,对其产生第一印象。在一个“看脸”的社会里,脸部的缺陷,总是给人们带来很大困扰。
伊莎贝拉经历的,大概是很多对自己容貌不满者的梦想,换掉原来的那张脸,换上一张更新的。但对真正的换脸术来说,并不是那么简单。
谁先找到那张脸?
2005年5月27日,伊莎贝拉陷入昏迷中。她服用了过量药物,不久前的离婚、和女儿的争吵也许都是“最后一根稻草”。失业一年多的伊莎贝拉深陷抑郁多年,她试图用药物让自己忘记这些烦恼。
爱犬塔尼亚把它叫醒了。
她睁开眼,满目都是血色。很快,她就发现,自己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洞。血,是自己的。为了唤醒不省人事的主人,塔尼亚几乎啃掉了她的半张脸。
考虑到面部受损的严重程度,法国外科医生让·米歇尔·迪贝尔纳和贝尔纳·德沃谢勒决定放弃传统的整形外科手术方法,为伊莎贝拉进行“同种异体颜面移植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换脸术”。
迪贝尔纳是异体移植领域的专家。1976年他完成了欧洲第一例胰腺移植手术,1998年,他又主持进行了世界首例手部异体移植。次年,美国也完成了本国第一例手移植。这个手术之后,就有人预言:一年内就会进行第一例颜面移植。
整形外科专家郭树忠表示,也正是2000年前后,“换脸术”成为国际整形外科界研究的热点。他是显微外科医生出身,当时这个领域已发展到“瓶颈”,“所有技术都成熟了,唯一能突破的就是在异体颜面移植,这也成了下一步大家都要攻坚的方向”。在当时的研究界看来,“这个领域技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换脸术。如果能攻下这个难关,那意味着技术到达了顶峰”。
就在法国医生为世界首例换脸术做准备的同时,还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担任整形外科主任的郭树忠也在准备“换脸术”。2005年,郭树忠及其团队宣布成功把半张白兔脸移植到了灰兔脸上。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国外医学团队也在同步进行动物试验,“只不过他们用的是老鼠”。
科学研究争分夺秒,每个国家的专家都希望成为那个“第一例”。郭树忠说,当时他也有一例患者,关键是,谁先找到可以换脸的供体。
寻找到合适的供体差不多是全凭运气的一件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马勇光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脸是人体上最特殊的器官,具有相当的身份辨识性,而切取面部组织会彻底破坏死者容貌,这比切除内部脏器更让家属难以接受。捐脸者难求,即便有人捐脸,也需要跟供体进行性别、年龄、种族、脸型等多维度的匹配,“在稀少的供体上还要进行严格的配型,从而使寻找合适的供体难上加难”。
“始终隔着一个面罩”
郭树忠的病人叫李国兴,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新建村的村民。2003年,他在放羊途中遭遇黑熊攻击,导致脸部严重毁容。郭树忠记得第一次见他时非常震惊,“没有鼻子,没有上嘴唇,牙齿露在外面,半边脸都没有了”。
从事整形美容几十年的郭树忠见到了太多因各种原因被毁容的人。他觉得普通人都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但那是因为“很多人不能感同身受”。在多年从业经历中,他发现被毁容者永远只能活在被隔离的社会,他们与外界“始终隔着一个面罩”。
2005年9月,一个电话打到了伊莎贝拉所在的医院:适合她的供体找到了。
那张脸属于46岁的独身女子玛莉莲·圣·奥伯特,她是自杀的,只成功了一半:大脑死亡,心脏却仍在跳动。其亲属同意捐出她的脸和其他器官。
11月27日,来自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的50多位专家进行了超过15个小时的手术。他们把一张新的脸移植到了伊莎贝拉脸上。
这成了全球第一例换脸手术。4个月后,郭树忠也找到了供体,为李国兴实施了换脸术,这是全球第二例。
伊莎贝拉在两天后看到自己的“新脸”。情况比她想象得要好,那个洞不见了,她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张肿胀、发蓝的脸,实际上只是嘴唇有些歪并且肌肉不听使唤而已。镜子中的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至少看起来要正常多了。
在郭树忠印象中,李国兴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好”。很多人以为,换脸后的患者看到移植后的脸内心会有异样情绪,毕竟“这是一张死人的脸”。其实并非如此。据他了解,截至目前,全球大约进行了40例换脸术,“病人满意率还是很高的”。
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虽然伊莎贝拉和李国兴很快接受了这张脸,但他们的免疫系统,仍然表示拒绝,像提防病菌入侵一样,提防着这张新面孔。
“握住了一枚圣杯”
伊莎贝拉花了10年跟那张脸相处,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既然我做了决定,这就注定是一场战斗。”伊莎贝拉说,“哪怕我将会面临巨大的未知转折,那些失去的部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不过,她最终还是去世了。医院没有透露她的死因。有法国媒体报道,她是死于近期手术后的并发症。法国《费加罗报》则有消息,伊莎贝拉在2015年就曾出现了排斥反应,并因此丧失了唇部的部分功能。而高强度的抗排斥治疗也是她患上两种癌症的始作俑者。
李国兴的战斗结束得更早。
2007年12月,手术后的李国兴就回到自己生活的那个闭塞山村。2008年6月,他去世了,“死因不明”。
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手术团队曾对6名面部移植者进行了长达5年的随访。2019年,在他们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结果显示,每位患者都需要治疗2-7次急性排斥反应。免疫抑制药物也会引起诸多代谢副作用,大大增加了患者罹患癌症的风险性。
李国兴是目前为止中国唯一一个接受了换脸术的患者。尽管在这之后,国内仍有一些医院用自体组织为脸部受损患者进行了面部重塑,但在郭树忠看来,这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换脸术”,而是皮肤扩张技术的运用。
抗排斥仍是最大的挑战。克利夫兰诊所的团队正在研究更精准测量身体对面部移植的耐受性和不耐受性,以降低免疫抑制剂潜在的副作用。这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在一些医学博士看来,解决排斥问题相当于“握住了一枚圣杯”。
对于接受脸部移植的人来说,这场战斗的终极战场在内心。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整形外科张曦博士在《换脸换的是什么?——关于中国首例换脸术的回顾与反思》中认为,李国兴之所以放弃治疗是因为与家庭及周围环境的融入度不理想,导致心理落差,对“新脸”产生排斥感。
图像学学者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一书中引用了导演汉斯·齐施勒的说法:“脸是我们身上代表了社会性的那一部分,身体则属于自然”。这意味着,换脸术不止是换了一张脸,还有关于这张脸的所有社会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换脸术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和争议性的手术之一。
负责记录凯蒂换脸的《国家地理》摄影师玛姬·斯蒂伯见证了一张新面孔重生所需要经历的痛苦、挣扎和战斗。她说,这张脸“与外貌无关,关乎精神。你的脸就是你生活的地图”。
(周深深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