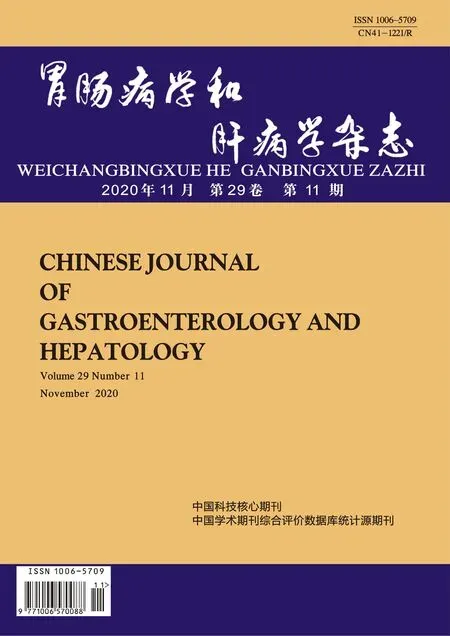1,25(OH)2D3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肠道菌群及免疫调节的研究进展
黄红洽,李校天
1.河北工程大学临床医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0; 2.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类多系统疾病,可增加2型糖尿病、肠道疾病、慢性肾脏疾病、心血管及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风险[1]。其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NASH相关性肝硬化和肝细胞癌。人群中病毒性肝病的发病率显著降低,但NAFLD发病率却持续升高[2],位于我国肝脏疾病之首[3],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疾病之一。单纯依赖个体运动及生活方式调节具有明显局限性,目前亟需明确的临床治疗药物,因此探索NAFLD发病机制尤为重要。
1 肠道菌群及其功能
1.1 肠道菌群概述自胎儿早期,原肠胚的内胚层发育形成肝脏,肠道血液经胆管、门静脉系统流入肝脏进行解毒,胃肠道和肝脏系统之间便存在着菌群联系[4]。肠道菌群包含1 000余种常驻的细菌[5],约占人体内微生物总数的70%,占肠道微生物99%以上,主要包括原生动物、古细菌、真核生物、病毒、寄生虫等。正常情况下,个体的肠道菌群是相对稳定的[6],与宿主、环境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发挥着抗感染、营养代谢、抗肿瘤及免疫调节作用[7-10],当发生菌群紊乱时,诱导肠道菌群和宿主发生相互作用,产生免疫应答,促进脂肪肝形成。最新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对维生素D3具有羟基化作用,在维生素合成中作用显著,且维生素D3对肠道菌群也有调节作用,两者相互影响[11]。
1.2 肠道菌群与NAFLD动物实验[12]发现,菌群失衡在NAFLD中普遍存在,肠道菌群既是促炎、致病因素,又是治疗手段,如肺炎克雷伯杆菌、某些球菌均可增加脂肪肝的严重程度[13-15],Odoribacter和Alistipes杆菌百分比与NASH呈反向关联[16]。一项涵盖1 148例NAFLD患者的临床研究[17]表明,Faecalibacterium减少与NAFLD形成密切相关,且在随机临床试验[18-19]中用益生菌治疗后,NAFLD患者的脂肪变性程度及氨基转移酶活性显著降低。此外,Miele等[20]在35例病理活检证实的NAFLD患者中发现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检出率高达60%,是正常人的2倍,伴肠黏膜通透性明显增加。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也可对疾病发展造成影响,如增强肠黏膜屏障和脂代谢,减轻肝损伤等[21]。因此,菌群干预可能作为治疗NAFLD发生和进展的新靶点[22]。与抗生素、粪便移植法相比,益生菌具有不良反应较小的优势,无疑成为调节菌群失调的最佳选择。
2 维生素D3代谢与功能
在哺乳动物体内,维生素D3不存在生物活性,需要利用细胞色素酶P450s(CYPs)进行羟基化转化为25-OHVD3及la,25-(OH)2VD3的活性形式,才能在机体内发挥功能。维生素D3多以25-羟维生素D3形式存在于血液中,并在肾脏中经CYP2B1(1a-羟化酶)代谢,最终转化成为具有生物活性的1,25(OH)2D3。研究发现,1,25(OH)2D3不仅可以调节钙磷代谢、抗氧化,还具有调节肠道菌群[11],免疫调节[23],保护肠黏膜屏障[24],抗细菌感染及调节蛋白表达[25]等重要作用,进而调节肠道菌群,干预NAFLD进展。肠道上皮细胞屏障是1,25(OH)2D3发挥菌群及免疫调节作用,预防不可控炎症反应的重要部分[26],肠道上皮屏障包括免疫屏障、机械屏障、生物屏障、化学屏障,以前两者作用显著。同时,还发现1,25(OH)2D3可使肠-肝循环中胆汁酸转运体下调,内源乙醇生成减少,胆碱可用性降低等,从而抑制脂质沉积。目前我们团队着重1,25(OH)2D3对NAFLD患者固有免疫方面进行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及代谢组学研究。
2.1 维生素D3与免疫调节肠道免疫系统由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构成,可以抵抗多种病原体,前者又称为固有免疫,在免疫屏障中发挥最主要作用,Paneth cells(PC)是固有免疫的最主要效应细胞。多项研究表明,1,25(OH)2D3是固有免疫的重要调节剂,可直接或通过刺激回肠PC及免疫细胞表面大量表达的维生素D受体(VDR)间接作用于PC,使其分泌大量抗菌肽(AMPs),发挥自噬功能,参与肠道免疫调节[23,27],如在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中,1,25(OH)2D3与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表面VDR结合后可强烈诱导细胞中cathelicidin AMP(CAMP)基因的表达[28]。AMPs也称宿主防御肽(HDP),是先天免疫的第一线,具有免疫调节活性,通过NF-κB、VDR、MAPK等多种信号通路起作用,对细菌、真菌、病毒及寄生虫均具有活性,常储存在大的细胞质颗粒中,后释放到小肠隐窝腔,累积杀死微生物、限制共生菌群的炎症反应,为宿主防御作用提供支持[29-30]。另外,VDR在PC和多数免疫细胞表面均大量表达,也提示活性维生素D3对宿主小肠免疫细胞增殖、分化及固有免疫及肠道菌群调节作用显著。
1,25(OH)2D3可刺激PC表达α防御素(隐窝素)、溶菌酶、凝集素RegⅢ-γ、分泌型磷脂酶A2(sPLA2)、cathelicidin LL-37及杯状细胞分泌的糖蛋白等抗菌多肽。PC位于小肠隐窝底部,紧邻肠上皮干细胞,参与介导免疫反应,如PC在其基底外侧膜上表达CD95或FAS配体,可诱导周围组织的FAS+免疫细胞凋亡;AMPs不仅具有抗内毒素的作用,还可抑制促炎细胞因子TNF-α、IFN-γ、IL-6、IL-22等的水平,调节趋化因子的表达,促进血管生成及伤口修复[31];还可激活并募集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及T细胞等免疫细胞,诱导免疫细胞分化[29,32];中和促炎细胞因子从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释放、肥大细胞脱落等[30]。
多项研究表明,充足的活性维生素D3不仅可以刺激AMPs表达、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抵抗肠道黏膜通透性改变、防止大量细菌及其代谢产物LPS、DAO、D-乳酸等入血[33];还是增强固有免疫的必要条件,可刺激免疫细胞表面应答的模式识别受体NOD2、AMPs及关键细胞因子基因转录表达[34],减少细胞因子释放、抑制肝脏TLR4等炎症通路[35],以及阻碍复制和转录过程、减少翻译因子及前体细胞合成、抑制肽聚糖和蛋白激酶NF-κB活性等途径干预免疫反应,延缓NAFLD[30]。反之,维生素D3缺乏可导致肠黏膜固有层免疫细胞及抗菌肽数量更加减少、活性极大降低、黏膜通透性增加,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菌群失衡、肥胖及NAFLD形成。
获得性免疫常发生在固有免疫之后,经抗原提成细胞作用后才能启动的免疫功能,主要表现为固有层浆细胞分泌抗菌肽—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后者可以招募、激活树突细胞、巨噬细胞等抗原呈递细胞,调节获得性免疫系统。
2.2 维生素D3与肠上皮细胞屏障1,25(OH)2D3除了可作用于免疫屏障,还同时对机械屏障和化学屏障有影响,肠道上皮细胞及细胞间连接构成肠道机械屏障,1,25(OH)2D3不仅可以上调肠道上皮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2表达,还能增强单层细胞间黏附连接、紧密连接的完整性,防止菌群移位[36]。
研究还表明,维生素D还可刺激肠上皮细胞大量分泌黏多糖(mucin,MUC2)及表皮黏附蛋白,分泌物质黏附于肠黏膜表面,形成化学屏障,进而维持黏膜通透性完整和肠道微生态平衡[37]。维生素D缺乏时,黏多糖和表皮黏附蛋白表达下降,肠道通透性明显增加,甚至黏膜萎缩,伴防御素的激活酶(基质金属蛋白酶7)下降,导致肠道防御系统失衡,进而引发肠道微生物系统失衡,作用于NAFLD形成。
3 维生素D3在NAFLD治疗中的价值
研究表明,维生素D3具有延缓NAFLD的作用[38],且肠道菌群在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Kim等[39]筛选了1988-1994年4 015例确诊为NAFLD的患者进行了长达19年的随访,发现维生素D水平与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呈显著负相关(P<0.01),活性维生素D3是阻止肝脏脂质堆积、NAFLD发展的保护因素[40]。16S RNA测序及宏基因组分析数据均表明,维生素D3可大范围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如维生素D3缺乏(VDD)和CYP27B1-/-小鼠[41]的肝螺旋杆菌属细菌数目显著增加。而且,VDR基因敲除小鼠(VDR-/-)[41]与其有相似的表型,表现为肝螺杆菌数目增加、阿克曼菌数目降低及肠α-防御素5下降,伴肠道黏膜脱落和脂肪肝形成。向高脂肪喂养的小鼠提供充足的维生素D3仅出现轻微脂肪肝,而VDD小鼠不仅表现出肝脏脂肪变性,甚至形成肝脏炎症、纤维化[42],另外,研究发现维生素D可上调VDR表达,进而调节肠道菌群结构。此外,研究表明VDR-/-小鼠对脂多糖的敏感性显著升高,ZO-1、E-cadherin、Occludin、Claudin-1等连接蛋白表达下降明显[38,40]。同时,维生素D3和肠道菌群具有协同作用,在免疫调节方面也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NAFLD可能会受益于两者之间的协同作用[11]。
综上所述,1,25(OH)2D3对肠道菌群及免疫调节极其重要,可能通过干预肠道菌群及肠道屏障途径延缓NAFLD的发生或发展,进而发挥NAFLD治疗作用。另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3]、类风湿关节炎[44-45]、过敏性疾病[46]、神经系统疾病[47-48]、心血管疾病[49]等均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肠道菌群在疾病中的地位,为疾病诊治服务。
4 展望
目前NAFLD发病率在全球仍呈持续上升趋势,该疾病治疗属热门研究领域。大量临床试验表明,1,25(OH)2D3可以减轻脂肪肝,然而它具有多重生物学功能,且NAFLD形成是多种细胞因子和通路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充分探究或明确1,25(OH)2D3具体作用机制尤为重要。肠道菌群和肠道屏障在NAFLD发展中的作用显著,两者可相互作用,是1,25(OH)2D3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肠道菌群和肠道屏障之间的作用极其复杂,以后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1,25(OH)2D3与肠道菌群、1,25(OH)2D3与各肠道屏障、各肠道屏障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可能影响机制,发现最主要作用机制及途径,并针对性地进行相应动物及临床试验验证,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可靠的治疗理论和方法。临床上免疫相关性疾病类型繁多,一直是医学史上较难攻克的课题,且黏膜免疫系统构成了机体的第一道防线,本文主要从肠道固有免疫屏障和免疫调节方面阐述,希望能为发现NAFLD治疗的临床药物提供新思路。此外,随着实验方法和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已成功将宽泛的肠道菌群研究由多种、单种深入到亚种水平菌落;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到肠道黏膜,甚至肠道屏障的超微观组织结构及变化,我们期待未来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为临床NAFLD治疗提供有效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