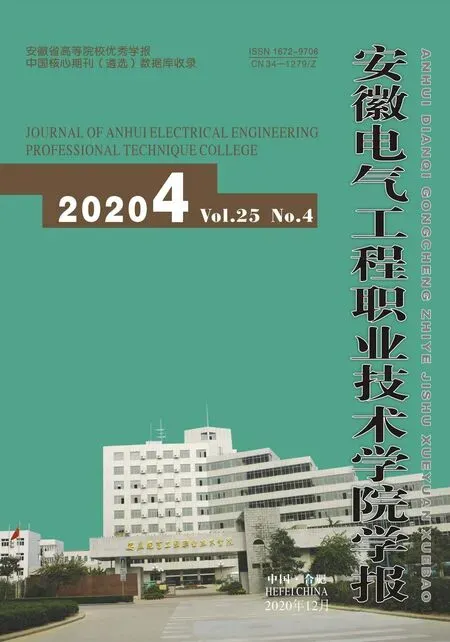韩愈集现存宋集注本研究综述
王习之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在唐代,韩愈是“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开启点之人物”[1],其作品在后世广为传播,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之说。宋代是韩愈研究的高峰时期,自北宋以来,流传至今的宋代集本共十三家,亡佚一百零二家,今之能见不过十之一二。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2]
韩愈集现存宋代集本共十三本,分别是潮本《昌黎先生集》、祝充《音注韩文公集》、文谠《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方崧卿《韩集举正》、南宋浙本《昌黎先生文集》、南宋江西本《昌黎先生文集》、南宋闽本《昌黎先生集》、南宋蜀刻十二行本《昌黎先生文集》、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张洽池州本《昌黎先生集》、廖莹中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其中七家为注本,分别是: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廖莹中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祝充《音注韩文公集》、文谠《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其余六家皆为校本。现据此分别讨论。
一、方崧卿《韩集举正》
《韩集举正》为南宋方崧卿于淳熙年间所作,此集引用其他校本共七十多家,引校唐宋典籍九十多种,其著述之详可见一斑。亦可见韩学于唐宋时期发展之兴旺。此本对韩学的接受与流传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韩集举正》之研究,版本方面,刘真伦的《〈韩集举正〉现存抄本及其释读》[3]将现存抄本分为三个系统:影宋本,四库全书本及四库全书传抄本。又提出方氏由于不具备完整的校勘凡例而删减字符造成的后人阅读上的困难。史历的《〈韩集举正〉版本源流考》则探究了《韩集举正》[4]淳熙刻本以后的八种清抄本流传情况。史明文《〈韩集举正〉在版本学上的价值》[5]则明确地写出《韩集举正》为考察唐宋时期韩愈诗文集版本提供材料和撰写版本题录两种贡献。
在校勘方面,则有史历的《〈韩集举正〉在校勘学上的贡献》一文指出方崧卿在校勘方面的多处成功之处。此外他还有《〈韩集举正〉校勘符号简论》[6]对《韩集举正》使用的四种校勘符号进行细致说明。
除了校勘和版本方面,还有刘真伦先生的《方崧卿韩集校理本考述》[7]及《宋淳熙南安军原刻〈韩集举正〉考述》[8]二文,一是对《韩集举正》以及集本残卷的解剖,重新描绘出方崧卿韩集校理本的作品编次、校勘体例、文字特征,并考察其刊刻流传情况。二是考察南宋原刻本《韩集举正》的流传端绪,同时考察其刊刻时地、文献价值及其在现代释读中存在的问题。
可见有关方氏《韩集举正》的研究多集中在流传过程、校勘特点方面,且褒扬甚多。但是在其校勘符号上的误区及校勘时的失误却少有人提及。对《韩集举正》的查漏补缺将是研究的重点工作之一。
二、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及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四库全书所载“原本韩文考异”即朱熹的韩集校理本。宋代虽号称五百家注韩,但对韩集文本有实质定性作用的只有方崧卿和朱熹两家。朱熹的韩集校理本为宋元以后韩集传本的祖本,因宋代朱子理学一时风靡,而朱本也被人们奉为经典。朱熹在方崧卿的基础上成此书,但其对方本的某些修订也能够弥补方崧卿学风较为拘谨的某些缺陷,故成为后世之通行本也并非偶然。[9]“方书用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不载全文,但大书所正之字,而以辩证注于下,此亦仍之。后张洽校刊,又附以补注数条。此本为李光地所重刻,以有散附句下之别本,故今题曰‘原本’以相别。”(1)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95页。后又有“别本韩文考异”载“宋朱子原本,王伯大重编。以朱子《韩文考异》散入句下,而别采诸家音释,附篇末。后书肆重刊,又散音释入句下。”(2)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95页。朱本由于没有原文对照而在阅读的过程中略有困难,而王伯大本将朱本注释散入原文中,并新增部分补注,读起来较为方便。
关于朱子《考异》之研究,在版本方面,曾抗美的《〈昌黎先生集考异〉版本考略》[10]及《〈昌黎先生集考异〉成书与版本线索述原》[11]二文详细著述了其版本源流与成书过程,刊照甄别了十卷本与四十卷本、十卷本之间版刻系统的异同优劣,考订出张洽校定的宋椠为海内孤本。
在朱子学和韩学方面,赵聃的《试论〈昌黎先生集考异〉创作的理学目的》[12]认为朱熹借校勘韩文来批评韩愈的儒家经学思想并阐释自己的理学思想。查金萍《学术视域下〈韩文考异对清代之影响〉》[13]以清代学术史为视角,考察《韩文考异》的影响,有助于推测清代对朱子学及韩学的接受情况。陆德海《〈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法学研究》[14]从具体字句篇章之法的分析、总结入手,批驳了《韩集举正》的“好奇”,对于现实中流行的怪奇文风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起到了正视听、导后学的作用,为当时及后代的文章写作灌输了平易的文法学思想,并进而建立起“文从字顺”的新文法标准。
在文献学方面,刘真伦在《朱熹韩集校理文献来源考实》[15]中具体考察了《考异》校语中直接征引的唐宋文献,深入发掘了朱熹的韩集校理工作。
其他还有杨国安的《朱熹〈考异〉与韩集的近世化》[16]、戴从喜的《朱子与〈韩文考异〉》[17]、张文华的《〈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学术价值》[18]以及一篇硕士论文《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研究》[19],都从文本出发,对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探究朱熹《考异》对韩集的推动发展关系。
纵观朱本的《考异》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朱熹原本《考异》的探索,至于后世流通量较大的王伯大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却少有人提及,王伯大本与朱本的具体差异之处更无人问津。因此要对朱本韩集深入研究,王伯大本的探索是必不可少的。
三、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问世稍晚于朱熹《考异》,于南宋庆元六年所作,由魏仲举汇编并刊印。该书以不同文体分类编纂,诗题下有题解、校语及注文散入正文中。虽号称五百家注,但魏仲举作为一个书商,无疑将其过度夸大了。《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有三百六十八家,认为“大抵虚构其目,务以炫博,非实有其书。”(3)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卷一五〇,第1288页。魏本虽批评较多,仍不失为善本。其广泛搜集唐、宋两代众多的韩集整理本,使今人了解此类韩集整理本的特点与概貌,以及韩集流布、韩学研究状况的重要的文献史料,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近人傅增湘则认为:“读韩集者,若求集注,当以魏仲举本为优。”[20]
文献学方面关于《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的研究,有刘真伦先生的《韩集五百家注引书考》[21]一文,对魏本在卷首实际征引的84家及引用文献的89家进行了一一考述。通过这一研究,可以清楚的看出南宋时期韩集笺注的发展面貌。刘尧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音注勘正》[22]亦是如此,对魏本注音的失误进行校勘,在指正失误的同时,从音理上加以说明。另有王东峰《〈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的文献学价值及其在韩集流传中的影响》[23]一文,论述了《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的辑佚价值、校勘价值、考证价值和版本价值,以及流传过程中对后世的影响。
在韩学方面,杨国安在《〈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在宋代韩学中的地位与价值》[24]对该书中所引樊汝霖、孙汝听、韩醇、刘崧、祝充、蔡元定本进行了考证,指出严有翼《韩文切证》在该书中的实际地位是远在刘崧、蔡元定之上的。
当然,也有将此本韩集与其他韩愈集注比较的研究,如《〈详注昌黎文集〉与〈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的关系》[25]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与〈韩集举正〉、〈韩文考异〉的关系》[26]二文,其一论证了魏本的集注和补注都间接地采用了文谠注和王俦的补注,并且在文本校勘上也多吸收其成果。其二摈弃此书没有采用《韩集举正》及《韩文考异》的旧说,论证了《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不但大量地采用了方崧卿和朱熹的韩集校勘成果,并且在文本确定上是以朱本《韩文考异》为主,体现了编纂者高超的眼光和严谨的态度。
其他关于魏本的研究,还有王东峰的硕士论文《〈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研究》[27]和《〈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的特点与价值》。[28]对《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的文献价值及学术价值从多角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魏本给予极大的肯定。
魏本作为集百家之大成者,内容上自然足够丰富,但是丰富繁多的内容与驳杂的诸家朱本自然会导致其中不少失误。目前也仅有刘尧指出魏本注音上的失误,这其中原因是由于魏本所引书目现今多已失传所致。或可通过魏本对已佚书书目补充查其线索,如魏本《曹成王碑》引姚宽注或可判断姚宽可能除诗集注本外另有文集注本(4)关于姚宽文集的推测,其具体论述详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第215页。。此亦可能为魏本在将来的研究趋势。
四、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
廖莹中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刻于宋度宗咸淳六年,直至明代东雅堂徐时泰(亦作徐泰时)将其翻刻,才得以重见天日。徐氏在翻刻时有意抹去廖氏姓名以自己替之,《四库总目》载:“明万历中,长洲徐时泰重刊,恶赢中为贾似道之党,削去其名,并削去世綵堂名,而改题东雅堂。刊字相沿,称徐氏东雅堂本,盖以此云。”(5)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95页。相比之下,魏本“未免失之太烦”,王本“稍有笺疏,不为赅备”,“惟此本录《考异》之文,节取魏本各注,易于循览耳。”(6)参见:[清]方成珪,《韩集笺正》影印版,第2页。可见此本的文献价值依附于朱子《考异》之上,在其卷首凡例中亦称:“今以朱子校本《考异》为主,而删取诸家要语付诸其下。庶读是书者,开卷晓然。”(7)参见:[宋]廖莹中,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
关于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的研究,有李庆涛的《东雅堂徐氏刻〈昌黎先生集〉辨》[29]和《东雅堂本韩集再议》[30]。认为东雅堂主人并非徐时泰或徐泰时,而是另有其人;且其刊刻年代亦非万历中而是嘉靖中。杨国安在《韩愈集注本概述》[31]中分析廖本所做工作,即删去注家姓氏、补充注释、删并改换题注及删并正文注。由于世綵堂本的特殊经历,研究者多将目光放在其流传过程上而忽视了其校雠学意义,因而有待进一步发掘。
五、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
近代学者傅增湘曾说:“若求一家之言,则舍祝氏莫求矣。”[32]《音注韩文公集》成书于方崧卿《举正》前,与上述注本有颇多不同,是最接近南宋监本系统的一个注本。[33]他主要对韩愈诗文中的字词做了音切和训释,对偏僻语字深入浅出地作出解释,是后世韩文注音的先驱。
学界对祝充本研究甚少,仅有刘真伦先生的《韩愈集祝充〈音注〉本考述》[34]以及景雪敏的硕士论文《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研究》[35]和《〈音注韩文公集〉著者祝充生平考》[36]。刘真伦先生对祝本的刻工、避讳、编排及文献来源进行研究,探究了作者祝充的生平简介并考察了今传本。景雪敏则将重点放在作者的生平上,对祝充生平深入探究。
六、文谠《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
文谠注王俦补注的《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是现存较早的宋代韩集注本,该注本成书以来一直流传不广,不仅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未见采用,其他韩集注本也罕见征引。目前该书卷十二至卷十八已经亡佚,韩文注释部分已残缺不全。
关于文谠本的研究,杨国安先生有《蜀刻〈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考论》[37]一篇,对文谠注的特点详细探讨,即注文冗繁,注文往往数倍于正文,可见注者的兴趣关注点极为广泛。另有杜学林三作:《〈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流传渊源考》[38]、硕士论文《文谠、王俦韩诗注释研究》[39]及《文谠、王俦韩诗价值新探》[40],全面地对文谠、王俦韩诗注释的学术价值进行总结和探讨,并深入探究了文谠本的流传情况:清代前期,徐乾学、汪士钟始见收藏,道光之后进入杨氏海源阁,至第四代海源阁主杨承训将92种善本古籍抵押至天津盐业银行,这批古籍后归国有,此书即在其中。
通过对现存七种韩愈集宋代集注本的研究的分析调查,可以发现研究热点集中在方本《举正》的版本流传与校勘细节的考论、朱本《考异》版本流传与对朱子学贡献的研究、魏本《五百家注》对韩集流传的贡献及意义等方面。而王伯大本、世綵堂本、祝充本、文谠本的相关研究则较少,虽有不小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疏漏,依旧等待研究者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