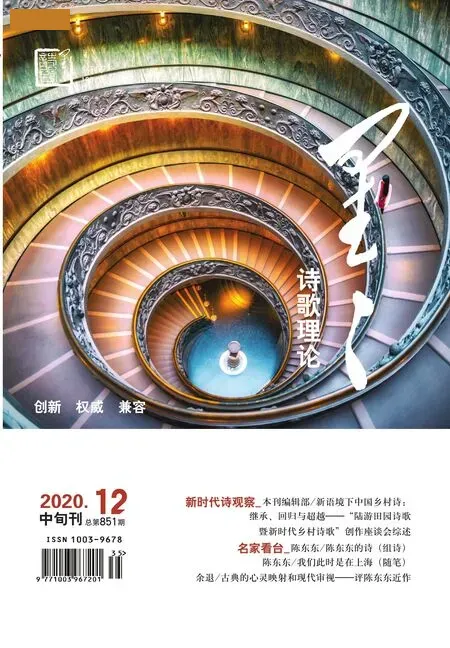诗与时代历史的研究
——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阅读札记
成 路
《裂开的星球》是一部研究性的长诗——人性、政治和道德的时代历史研究。贝内代托·克罗齐在《诗,真理作品;文学,文明作品》里说:“在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上,要把诗和文学作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在精神上所需要的东西加以培育”。以此,在阅读《裂开的星球》时,就不难理解诗人“试图来回答当下世界所面临境遇的种种疑问”是以参与在将要进入历史的时代里,以诗学培育哲学精神——在这一文明的概念下,诗人“对思想的论证”,犹如军官在战斗正酣时发出吼叫,正如帕里尼所说的,这吼叫“使长得十分结实的耳朵也被震破”(贝内代托·克罗齐)。
之所以这么说,是这部“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的诗,从引入一个彝民族秘史《查姆》的意象组——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与创世神话相关的古老隐喻——黄金的老虎——“这个星球的四个方位有四只老虎在不停的走动,而正是因为它们不断迈动的脚步,才让这个星球永远没有停止转动。”开始,就设置了一个宏大的背景,呈现人性的本真,从而对原罪的追认——“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心灵的罪与罚。
接着,诗人以呼唤的方略:“哦!古老的冤家。是谁闯入了你的家园,用冒犯来比喻/似乎能减轻一点罪孽,但的确是人类惊醒了你数万年的睡眠。”引导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例,以生存自然法则、文化相撞、科技灾难(核战争)、史学战例、哲学智慧(阿多诺、卡德纳尔、本雅明、茨威格)、权利和自由的阐释,以及人类确认的各民族母亲河——“哦!幼发拉底河、恒河、密西西比河和黄河,/还有那些我没有一一报出名字的河流”暗指了人类血亲的统一性。这时候,他以具实的象征——“打倒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这个世纪的进攻。/陶里亚蒂、帕索尼里和葛兰西在墓地挥舞红旗。”开始了表达对世界灾难的忧患和对世界罪行的叩问,借请出彝民族智者毕阿什拉则在召回人类古朴的温暖的灵魂,而适时地唱起共产主义的颂歌——“我精神上真正的兄弟,世界的塞萨尔·巴列霍,/你不是为一个人写诗,而是为一个种族在歌唱。”并在其后的几节诗里,陶里亚蒂、帕索尼里、葛兰西、塞萨尔·巴列霍四位共产主义先驱和人类学家胡安·鲁尔福以精神象征的出场,以此,可以说,吉狄马加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诗人,他用汉民族语言(不时闪现彝民族典籍的光彩)表达对这个有缺点时代的一个民族诗人的思想观点——“裂开的星球”——“不要建在好的旧时代,要建立在坏的新时代”(瓦尔特·本雅明《反思》)。
在这里——“裂开的星球”的代词,诗人采用陈叙的方式,经过33次“在这里……”的意象转场,归拢了人类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种族等诸多问题的巨大冲撞,有的是撕裂性的,从而揭示出进步与阻隔——心灵与制度的阻隔。正是在这样的时间当口——2020,岁在庚子。这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用新冠肺炎这样另类的方式狠狠地抽打了我们这些“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且还有继续抽打下去的趋势。而我们,全球几十亿人,竟然也只能摊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这对牛逼哄哄的“现代人”来说不啻为黑色幽默。
那么,我们真的就无能为力了吗?是的,医学界、生化界至今尚无良方。人类在进化,疾病也在进化,感觉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死胡同。即便如此,显然人类也不打算放弃。
人类面对疫情大流行,就显得格外苍白、平庸、无聊了。诗人何为?命题太大,让人难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总要有人默默前行,总要有诗人发出属于自己的“天问”。在这个时候诗人吉狄马加写下了《裂开的星球》。
诗人的“天问”是忧患,还有“这是救赎自己的时候了,不能再有差错,因为失误将意味着最后的毁灭。”的惊醒和号召——“如果要发出一份战争宣战书,哦!正在战斗的人们/我们将签写上这个共同的名字——全人类!”这时候,吉狄马加以繁密的当代灾难史实意象,铺排的长句,浓墨重彩,强烈而深刻地表现主题和诗人的思想——要求人类善待自然,善待生命,善待自己——他以39个“这是……的时候”提出了诗学方案。也正是这些具体的实例意象,对作品思想的整体性、意义感、尊严感负有责任。
“当满足于一时成功的作家们大多沉溺于雕虫小技时;当天才躲避劳动,而鄙视庄严的古代文学典范作品成为一时风尚时,当诗歌不再是一种虔敬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件轻薄的事情时,——我们却怀着深深的敬谢之忱关注着一位把一生的最好年华骄傲地献给特殊的劳动、无私的灵感和建立丰功伟绩的诗人。”普希金高度赞扬俄国作家格涅吉奇翻译荷马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把它用在我读《裂开的星球》时的感受也是贴切的。
诗人身在其中,他不躲入臆造的天堂,他不想逃避,也无意逃避。他用稍显粗糙但不失炙热的语言,把我们再次拉入我们正在经历的灾难之中,他用雄壮的嗓音告诉人们,他在任何时候都未失去对生活、人类及其未来的信心。他在病毒面前保持着一种高度的乐观主义,一种对人类的最终胜利、它的文明和成就的确信。我认为,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疫苗”——在时间的进化历史中,诗人分拣出了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断代的事件和代表人物——哲学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诸多方面,开阔的视野容纳历史(神话)与现实、生命与灾难、微观与宏观,将这些庞杂乃至相悖的事物组合成了一个大的诗歌空间。或者从根本上说,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生命和自然宇宙的深度认知,对人类命运的自觉担负:
哦,女神普嫫列依!请把你缝制头盖的针借给我
还有你手中那团白色的羊毛线,因为我要缝合
我们已经裂开的星球。
进而,当阅读到“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这两句追问的诗句时,我记起了在《自然》中,爱默生认为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三个原则: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是精神的象征。追忆这三个原则,是我看到了诗人在作品里对裂开的星球上存在而随时可能消失的历史(自然)事实的忧伤和人类的罪(或者说是疑似罪)的揭露,以15个“让……”诗句点燃愿望和思想的光辉,为诗歌增添了丰富的血肉组织,显出诗人的愿景色彩瑰丽。
吉狄马加这位马克思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关于善恶观念、生死之理、自由民权、创造和掠夺(破坏)等等与“这个世界将被改变”联系在一起。改变是要战斗的:“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铠甲/流淌着数字的光。唯一的意志。”老虎、铠甲、光、意志,在这首开阔宏大的命运交响曲里,打通时间的壁垒,将历史神话与现实世界熔铸一炉。炉火正旺,它是诗人的情感和哲学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