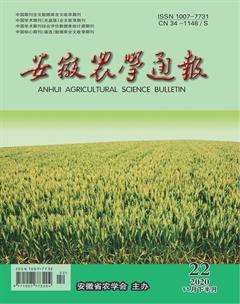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乡村治理疲惫问题反思
任家庆 肖俏



摘 要: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对乡村治理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乡村在治理实践中存在治理疲惫的困境。该文从城乡规划学、政治学和人类学视角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城乡差异是治理疲惫现实的源头、基层治理压力加剧治理疲惫、治理疲惫处在中断的自治文化环境中等观点,以及从规划层面健全公共应急管理体系、从实践层面创新基层治理单元化解治理疲惫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疲惫;学科融合;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D42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0)22-0018-04
Abstract: To solve the governance dilemma of exhaustion which exposed in the test of sudden new crown epidemic in 2020, this paper offers some conclusions that urban-rural differences are the source of the reality of governance fatigue, the pressur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tensifies governance fatigue, and governance fatigue is interrupted in an autonomous cultur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integration with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suggests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lanning level and innovate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units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Exhaustion of governance;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Rural governance
2020年春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国各地市积极响应党中央的领导,及时有效地控制了此次疫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层乡村作为疫情防控的“大后方”,为此次疫情防控和治理提供了重要帮助,但是辩证反思此次乡村疫情治理,仍可发现诸多值得改进之处。本研究从乡村治理的实践情况出发,调查部分东北乡村样本,发现乡村在面对突发疫情时,普遍存在应急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主体乏力且治理僵化问题,出现诸多极端治理行为,暴露了乡村治理疲惫问题。治理疲惫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由于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性、未知性和高危性,对治理能力要求高,乡村在面临高压治理时难免捉襟见肘,致使治理问题凸显。因此,有学者提出,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乡村治理进行“强行保养”的一次难得机会[1],对此次疫情期间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和反思,将有利于发现被放大的乡村治理问题,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1 学科融合视角下的二维分析框架
由于田野调研直接深入基层社会,调研虽有方向,但乡村治理深植基层社会整体环境,包含问题繁杂,内部结构联系紧密且跨度大,学科界限模糊,解释角度众多,因此对于其中事物的看待需要融合多学科知识综合思考,获得具有针对问题整体而非片面孤立的结论,使田野研究在借助多学科分析视角中提升学理价值。本研究以实践为依托,从管理学视角提出治理实践所存在的治理疲惫问题,融合多学科视角综合分析问题及原因。这种融合视角既可以从专业角度提出问题,又可以打破学科壁垒,从相对完整的视域研究乡村治理水平提升问题。
基层治理实践是顶层规划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田野调研有必要既关注到基层的治理实践,又将治理的实践放置在国家治理的整体中看待,统筹兼顾基层实践和国家规划2个层面,打通国家与田野社会[2]。因此,在研究乡村治理疲惫问题时,不仅要关注治理实践情况,还需要关注到体系建设等宏观规划层面。本研究在多学科融合分析成果基础上,利用二维分析框架,从实践和规划2个维度解决治理疲惫问题。
2 应急管理视角提出问题:极端治理暴露治理疲惫问题
应急管理问题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在21世纪初经历各种突发事件后,提出了包括应急组织体系、管理运作机制、制度及资源保障3方面的应急管理系统。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于“非典”之后开始建立,2019年初又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但在此次应急治理实践中,并没有看到新建立的应急管理体系发挥特殊的作用[3],反而出现了诸如“坚壁清野”、“封村封路”等应急管理体系外的极端响应措施。极端治理是一种以集体为治理单位,大规模集中采取偏激的、非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反常态治理行为,“坚壁清野”、“封村封路”、“土法消毒”等响应措施属于极端治理行为。在已经建立起新应急管理体系的今天,乡村为何采取应急管理体系外的非规范性极端治理行为?这种极端治理方式虽然起到切实的效果并为多数群众所接受,但是否足够科学、合理、可行?
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极端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展示了极端化的集约治理力量,但绝非科学治理。调研发现,由于资源不足、管理不当等,一些乡村基层单位难以满足现实的治理需要,对治理现实表现出对治理现状的无奈和服从,即出现治理疲惫问题。治理疲惫是治理主体在完成某些超出治理能力之外的问题时展示出的倦怠和无力的不健康的状态,治理疲惫有多种表现,如懒政怠政、形式主义、集体失能等。这种在治理过程中受现实情况控制、治理灵活性弱、疲于应付、耗能过高的极端治理行为,是受多方压力影响而暴露的另一种治理疲惫现象。在高压的运动式治理逻辑中,乡村单位为完成治理任务,被迫采取极端治理行为,伴生新的治理矛盾。有受访基层工作人员(包括村委会人员和基层政府人员)表示,极端治理实属下策,是在现实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办法,其言语中流露了对治理现状的无奈,体现了治理疲惫困境。这种疲惫的治理行为因缺少科学规范引起了一些“副作用”。有村民表示,极端治理限制了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出行、采购和交流等。由于极端的隔离和信息、物资流通不通畅,甚至引起了一些村民的恐慌,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治理矛盾。以上案例实证了乡村极端治理实质上是治理疲惫的表现,从实际成效角度看仍有缺陷。
3 学科融合视角分析乡村治理疲惫成因
3.1 城乡规划学视角:城乡差异是治理疲惫现实的源头 治理疲惫问题不能只依靠管理学解决,究其原因在于:一是乡村社会环境复杂,自然环境差异显著,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存在众多差异和分歧,难以在广阔的乡村社会中构建统一的管理模式或体系;二是乡村的资源相对匮乏,管理基础和条件不完善,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经济资源、基础设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缺,这种资源的短缺奠定了治理疲惫的基础。由此可见,治理疲惫问题的原因不仅在于管理技术缺乏,还受现实困境制约,因此只有解决现实的阻碍才能更好地发挥管理的效能。
从城乡规划学视角看,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长期受我国以城市发展为目标的导向影响,“乡土中国”在与强势的“城市中国”竞争中逐渐丧失话语权。近年来,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要素未自发、平等地进入流通过程,要素流通继续以“剪刀差”的形式扭曲[4]。因此,乡村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资源从乡村源源不断地以不平等的渠道和“价格”向城市流动,逐渐导致了城乡二元失衡甚至对立。所以,城乡不平等导致城乡差异是问题的根源,解决城乡二元矛盾,推动城乡均等化发展,将有利于化解治理疲惫的问题。
3.2 政治学视角:基层治理压力加剧治理疲惫 由于治理方法存在缺陷,治理难度和压力出现逆涨,乡村应对能力不能满足现实要求,乡村治理单位自发地采取治理疲惫行为。对东北部分地区10个乡村治理单位的调研发现,每个乡村治理单位均有不同程度的人手紧缺、上级任务过重等问题。对以上10个治理单位的30份样本分析显示,治理压力增大程度与极端治理程度相关性显著,各种现实困难造成的基层治理压力会加剧治理疲惫问题。具体如图1所示。
在我国条块体制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承担着来自纵向和横向的众多压力。基层既承担着来自“条块”结构的多目标的治理需求,又向上负责基层信息传输的任务,发挥了沟通群众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诸多重要作用,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此,国家决定将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而基层面临的是一个大社会,基层单位作为一个小政府,在面对大社会治理过程中时常不堪重负。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虽然治理人口少于城市社区,但要面临治理人口素质低、治理范围大、治理案件特殊、治理专业性差、治理主体僵化等问题,治理难度不减。因此,处在“城市中国”被动地位的乡村,其基层单位不仅面临经费少、保障少、人手少、能力差等常规困境,同时还要面对治理问题多、治理困难大、工作压力大等现实困境。在这种体制与社会背景下,基层为完成任务,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暴力的手段。所以,基层治理压力加剧了治理疲惫问题,释放治理压力迫在眉睫。
3.3 社会人类学视角:治理疲惫处在中断的自治文化环境中 在治理疲惫的乡村中,治理任务“被包揽”现象突出,即治理单位为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主动或被动包揽过多治理任务。而在乡村社会,承揽任务不等于完成任务。乡村社会生活具有一套自成一体的逻辑,村民有接受“法治”的意愿,也有接受“人治”的意愿。“法治”和“人治”区别不仅在于治理形式,还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5]。在治理实践中,相当多的治理矛盾起源于治理人员强调法律而忽视权威,最后导致治理难以开展,形成“官民对峙”的僵局。深入访谈和观察发现,治理疲惫的村庄多存在治理主体单一、缺少其他民间治理组织、习惯管理而疏于治理等伴随现象,反映了自治、“人治”文化传统中断的情况。
中国自古就有“国权不下县,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 [6]的治理传统。在这种“分治”的历史传统下,乡村自治往往依赖村中权威人物。古代乡村社会多靠乡绅参与公共服务,发挥教化、互助等自我服务功能;管理方面则由乡里制推选出的里长在基层社会发挥管理村务的功能。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在治理中重视“能人治理”的“人治”特点。在较为棘手或涉及矛盾主体较多的治理实践中,经常需要村中权威参与。但在当今乡村社会,权威外流的现象突出,乡村治理主体逐渐缩减和固化,而在村两委的选举实际中,“能人”权威又未必成为官方治理人员。乡土中国的“自治还乡”问题尤为凸显。因此,要化解治理疲惫、任务过重问题,有必要继承自治文化传统,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引回自治”。
4 二维层面化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治理疲惫问题
4.1 规划层面:统筹健全公共应急管理体系 一些学者考察此次疫情防控过程后,提出建立健全公共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议。但实际上,我国已建立了公共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出台了《突发事件应急对法》,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构建更为科学的新时代公共应急管理体系[7]。结合城乡规划学视角,笔者认为通过统筹规划城乡资源,引入专业管理人才,调整治理体系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共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有利于化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乡村治理疲惫的问题。
在先前关于乡村公共应急管理体系的调研中发现,乡村存在决策系统协调不足、信息预警不健全、三级防控网络名存实亡等问题[8]。在本次以东北部分农村为例的调研中发现,信息预警预案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决策系统协调和三级防控网络依旧存在问题。在完善决策系统方面,城乡社会具有异质性,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一些城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逐渐发生逆转,正在自觉形成素质较高的自治群体[9],而乡村社会成员文化素质偏低,需要主动将管理资源向乡村社会倾斜,统筹协同城乡系统。因此,引入专家合作机制,建立专家智库平台,可以在危机出现时从专业的角度为乡镇单位提供治理指导,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三级防控网络建设方面,城乡体制存在历史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乡村“政社合一”的治理制度与城市社区“单位制”不同,由此形成了区别于城市社区,以行政区划为结构依据的“县区—乡镇—行政村”三级运作体系;到了80年代这一运作体系被自治建设打破,村—乡(镇)治理出现割裂,而在当今防控治理环境中,乡村又缺少第三方治理主体(如物业、业委会等),最终共同导致现实中的应急管理体系松散,出现“网破人散”的局面,因此重新调整在村一级的防控治理体系变得尤为重要。调研发现,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存在防控组织混乱、权职不清问题,直接导致缺少良好的应急治理准备,在应急事件发生时人多手乱,出现内耗等现象,因此亟待乡村治理单位提前做好人员组织建设工作,划清职务范围,明确治理责任,整治结构体系及关系。结合人类学视角,在调整三级网络防控中的村—乡(镇)关系时,要考虑到村民自治的自主性,符合村民治理习惯。从政治学视角看,要防止乡镇政务以行政压力形式下放村委所导致的村委会内卷化和基層压力过大。这样,关于具体调整治理体系结构的问题则由规划层面降至实践层面,由管理学和城乡规划学引入到人类学和政治学领域。
4.2 实践层面:创新基层治理单元 中国乡村受古代家户经济影响,形成以家庭(族)为单位的村级自治传统。这种村级自治依赖内部力量进行自我治理,当下的村民自治同样是由激发村民内部主体性力量而创立的自治秩序[10]。所以,我国村民自治始终是我国农民自主创建的一种具有历史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但这种模式在“城市中国”的外力制约下出现组织资源退化、自治活力下降、治理形式单一、自治持续力不强等难题,要求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的村民自治体系[11]。应急治理作为特殊的一类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暴露的治理疲惫问题要求应急治理同村民自治一同调整和创新治理单元,激发村民自治活力。
在现在的体系中,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地理范围存在差異。一般来说,村民内生动力存在于自然村中,而村民自治制度存在于行政村中,这种结构上的不对等弱化了村民与村务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发挥村民积极性的基础上创新基层治理单元成为可能。在现有的研究中,存在缩小或下沉治理单元论、扩大治理单元论和上移治理单元论等多种观点。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受地方社会文化传统及现实治理状况等多元因素影响,采取治理单位下沉,建立多层次、多样式的治理单元的方法更为合适。以疫情防控为例,可参考徐勇[12]对村民自治运作模式的划分,将受访村子分为规范型、行政化的村和失控村3类。规范村治理效果较好,“村—民”关系和谐,治理协调有序;行政化的村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不得已承接行政单位事务的委派,出现“小村委大农村”等现象,体现了基层治理结构单一和治理行为背离自治初衷;失控村村中势力繁杂(宗族、企业、个人威信、宗教势力等),存在强于村两委的另一方治理力量,外界管理力量难以渗透,存在村委会被“架空”或被控制的现象。由于新冠病毒具有致命危险,无论何种模式的村子都主动配合村委领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辩证地看,村委会不是村民自治的唯一载体,包揽一切基层治理任务是疲惫地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应急治理过程中,利用村民自治传统文化思想,统领村民“人情”网络,整合村民利益关系,组建完全自治的村民组织,才是更和谐地为人民服务。村委会作为与上级政府联通的机构,则可继续发挥联通的功能,重村民之“政”,巧村民之“治”,通过嵌入治理单元,分配治理任务,转移治理矛盾,化解治理压力,实现领导村民组织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图2)。对于失控村,鉴于已经存在他治的现实力量,村委会与他治的竞争易使原有的自治结构失衡,导致治理效能降低。因此在村民愿意接受合法他治的情况下,他治势力作为村民自治的有机形式,可以与基层单位建立友好互动和有效衔接的叠加型组合。通过引入并领导村中势力,创立多样化次级治理单元,推动村内势力与村委会共治共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图3)。
5 结语
2020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乡村治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乡村在疫情治理中暴露了极端治理和疲于治理的问题。在学科融合视角的二维分析框架下,极端治理反映了治理疲惫的现实困境。从城乡规划学领域的城乡差异角度、政治学领域的基层治理压力角度、人类学领域的治理传统角度分析治理疲惫问题,得出规划和实践层面的对策思考。从规划层面上看,有必要统筹城乡,引入专业管理技术支持,调整体系结构,健全公共应急管理体系,缩小城乡治理宏观差异;从实践层面上看,可以创新基层治理单元、下沉治理单元,根据不同的治理运作模式对现实治理结构进行优化。
本研究调研了东北部分乡村,获取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一些有关东北乡村治理实践的案例并进行反思。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区域之一,农村农业发展较好,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今后仍需到各地乡村进行案例调研,以检验研究框架和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意义,适合更广泛的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段德罡,陈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应对思考[J].规划师,2020(5):75-79.
[2]明海英.基于田野实践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8-18.
[3]包冬冬.“疫情就像冬天里飞出的黑天鹅”——访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刘铁民[J].劳动保护,2020(4):10-12.
[4]曾小溪,汪三贵.城乡要素交换:从不平等到平等[J].中州学刊,2005(12):39-44.
[5]费孝通.乡土中国[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50.
[6]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
[7]刘铁民.科学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管理体系[N].中国应急管理报,2019-07-30.
[8]范金利.论县乡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
[9]熊易寒.新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分化:沿海城市地区的社会治理[J].文化纵横,2012(5):40-46.
[10]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206-207.
[11]徐勇,赵德健.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8.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118-126. (责编:徐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