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游戏之梦》:电子游戏研究的文化批评实践
周思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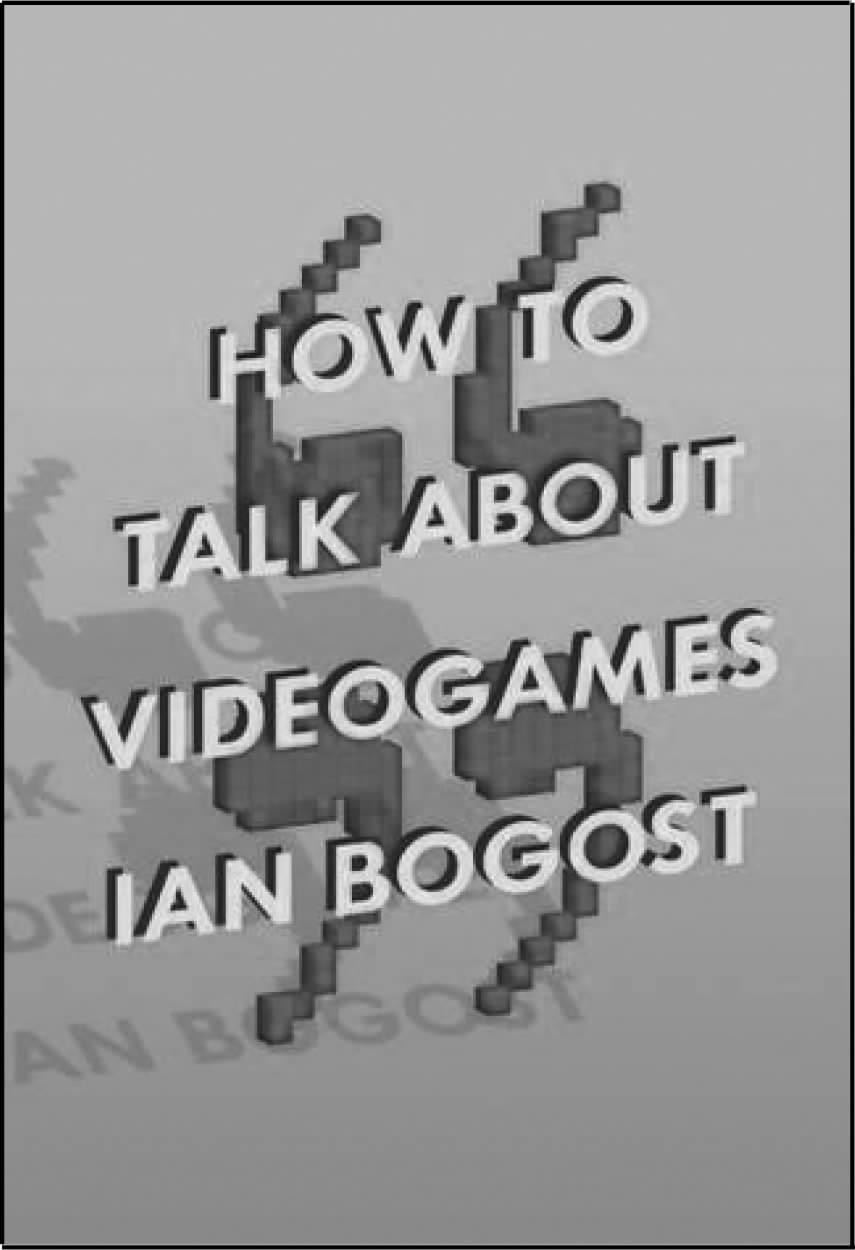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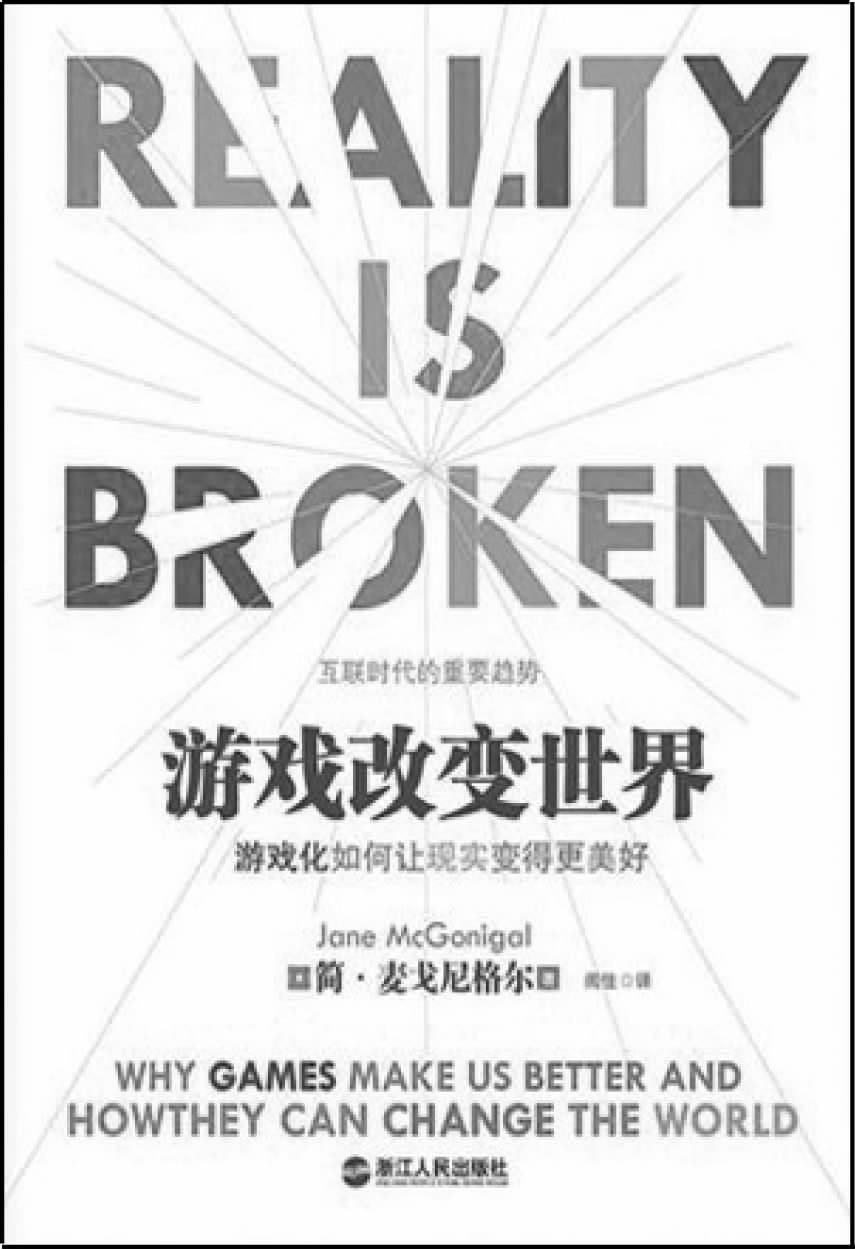
电子游戏与文化批评
游戏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Ian Bogost在其著作《如何讨论电子游戏?》(How to Talk about Videogames?)的“导言”中说:“每当我写电子游戏批评的文章时,总会有游戏爱好者发出质疑:‘你是在搞笑吗?好像只有智障才会思考这些东西。”[1]Ian无奈地感叹,电子游戏就像是烤面包机,只能用来烤面包,只能研究它的运作机制、烤制口感和技术改良,任何涉及烤面包机“意义”的研究都是无稽之谈,没人想要“烤面包机批评家”。
2000年以来,西方的游戏研究围绕着游戏学(ludology)和叙事学(Narratology)两种视角的争辩逐渐发展壮大,迎来了游戏研究的繁荣期,研究的视角逐渐多元,跨学科研究之势越发明显,敢于做“烤面包机批评”的游戏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在文化方面,游戏逐渐成为英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下的一个研究对象,其主张文化多元、雅俗共赏,对大众文化和经典文学一视同仁。
电子游戏作为一个“出身卑贱”,常被边缘化、污名化的文化媒介,非常迫切地想在文化研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早对游戏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游戏自身“去污名化”的过程。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的《游戏改变世界: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Reality is Broken:Why Games Make Us Better and How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的《游戏改变学习:游戏素养、批判性思维与未来教育》(What Video Games Have to Teach Us About Learning and Literacy)、格雷格·托波(Greg Toppo)的《游戏改变教育:数字游戏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变聪明》(The Game Believes in You: How Digital Play Can Make Our Kids Smarter),只是看这些题目,就能感受到游戏试图重塑作为文化媒介的自身地位的努力。如今,游戏在学者、玩家乃至大众的眼中逐渐摆脱旧有的“毒品”身份,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不二去处、激发人潜力的教育工具甚至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抵抗阵地。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游戏化”“学习游戏化”“产业管理游戏化”的提出,游戏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最好的辅助。但是游戏真的是抵御文化霸权的阵地吗?玩家真的是具有颠覆性的群体吗?游戏真的能——按简·麦戈尼格尔的话说——重塑人类积极的未来[2]吗?
周志强教授在《否定性的批判实践——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分立》一文中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前者主张文化多元,良莠并存,以良性的解放性文化取代对话僵化的文化;后者与批判理论紧密相关,坚持强调总体性视野下当代文化结构性缺陷和矛盾,依乎否定的哲学逻辑,深刻地反思多元主义论调,从而确立历史性的批判实践思想。简言之,前者注重对文化本身的分析和解析,而后者主张对文化的结构性颠覆和革命性重构。[3]
由此看来,如今游戏领域文化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的部分,而对“文化批评”涉及甚少。游戏作为当下受众最广也最具話题性的文化产业之一,必然反映和暴露整个社会的问题与矛盾。对文化批评自身而言,游戏是必须包含在内的研究对象,这对游戏本身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对理解当下时代的文化生活,发掘现代社会的文化症候,则是不可或缺的。
《电子游戏之梦》(The PlayStation Dreamworld)[4]正是这样一个电子游戏的文化批评实践。电子游戏究竟是什么?我们怎样分析它?电子游戏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好补充?它是否具有颠覆性?作者阿尔菲·鲍恩(Alfie Bown)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拉康式回答。
重塑欲望:作为“梦”的电子游戏
当我们面对一个电子游戏,准备着手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爱好者称它为“第九艺术”,叙事学学者将它看成一个文本,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认为它是行动(action)[5],科林·克雷明(Colin Cremin)指出它是情动(affect)[6]。如何看待游戏决定了研究者分析的方法,在《电子游戏之梦》里,阿尔菲则将它看作一场“梦”。
当我们打开电脑、游戏机或者带上VR头盔,沉浸在游戏世界中,陷入半梦半醒的恍惚状态时,不正是和做梦一样吗?游戏不像文学,它是一种积极体验,似乎每个玩家都能决定它的走向和结果。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体验到种种情感,并依据情感采取行动,但同时,游戏中的积极体验又是虚幻的,玩家实际上既不能决定过程,也不能决定结果,甚至玩家自己也被某种东西所控制。这不正是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吗?
因此,面对梦一般的电子游戏,阿尔菲采取了“释梦”的精神分析方法。但“电子游戏之梦”并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晚上入睡时的幻想,也不是患者面对分析师时二次修饰的复述,而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每当我们于现代空间漫步,于城市中遭遇无尽能指与所指围困时的体验。如今包围人们的不再是繁盛的都市景观,而是梦幻的赛博空间,正如唐娜·哈拉维在其著名的“赛博格宣言”中所说:“我们是赛博人,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我们的政治正是它赋予的。”[7]
阿尔菲的游戏批评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之上展开。在电子游戏的精神分析中,分析对象并不是游戏文本,更不是游戏中的角色,而是沉浸在梦境之中的玩家,他既是一个有算法性质的赛博人,又是有感情和个性的人类。然而,游戏与其说是玩家的梦,不如说是他者的梦,Ian Bogost认为游戏是我们操纵的设备,而阿尔菲指出,游戏更是操纵我们的设备。游戏并非满足了玩家的欲望,而是让玩家将他者的欲望体验为自己的欲望。简言之,游戏重塑了我们的欲望。
阿尔菲认为,我们最好将电子游戏之梦看作一种表面是内在冲动的意识形态建构。当人们讨论《侠盗飞车》《看门狗》这类犯罪游戏到底是会挑起人们的犯罪欲望,还是会让人们把犯罪欲望发泄到游戏而非现实中时,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犯罪欲望真的是人的“本能”吗?在犯罪类题材的游戏中,玩家往往扮演和制度相冲突的反面角色,但是玩家获得的并非是纯粹的犯罪快感,而是犯罪之后的正向反馈——物质层面的游戏经验和金钱,情感层面的罪犯之间的兄弟情义或者是反抗体制的正义感和叛逆感等——所带来的快感,通过正向反馈,游戏重塑了玩家的欲望。于是,玩家并非是在游戏中被挑起或者满足了现实的犯罪欲望,而是越来越离不开游戏所创造的这种“积极”的犯罪欲望,换句话说,游戏不会让玩家在现实中犯罪,但是会让他们不断购买犯罪类游戏。
即使是看似最“无辜”的游戏中同样包含着对玩家欲望的意识形态重塑。由著名“禅派”游戏制作人陈星汉创作,屡获殊荣的游戏《花》,鼓励人们在游戏中进行禅意哲思和冥想,在游戏里你扮演“风”,伴随着美丽的音乐穿越自然风景,在旅途中收集花瓣。然而,这款“与世无争”的游戏预设了一种倾向,它宣扬自然界的美丽,追求一种未曾被“玷污”的风景,拒绝任何技术进步。它重塑了玩家的欲望——一种对原始、纯粹、未经污染的自然的渴求。
阿尔菲告诉我们,游戏可以将“影响(affects)”变为“情感(emotions)”,让玩家在体验经由游戏影响而重塑的情感和欲望时,仿佛在体验自己本身的情感和欲望。电子游戏之梦不是让我们成为想成为的人、做想做的事,而是改变我们欲望的对象和方式。简言之,作为“梦”的电子游戏的功能就是重塑玩家的欲望。
享受(enjoyment)的命令与享受(jouissance)的时刻
拉康的法文术语jouissance在英文语境中译为enjoyment,中文语境中往往将enjoyment译为“享受”,而jouissance则有享受、快感、原乐、执爽、绝爽、激爽等多种翻译。由于英文enjoyment的通用含义和法文jouissance的含义有一定差异,所以有时在英文语境中jouissance也会不做翻译,直接拿来使用,但是用enjoyment同时表达通用含义和拉康式含义的情况更多,因为这二者无法截然分开。本文基于《电子游戏之梦》一书的做法,将enjoyment的通用含义和拉康式含义都翻译为享受,以表达这二者相互交融、无法分离的状态。
艾布拉姆斯将作者、读者、世界、作品看作文学的四要素,文学批评基本是围绕着这四个要素展开的。与之相应,阿尔菲认为电子游戏也是三位一体的:主体(玩家)、客体(游戏)和享受。从未有任何一种媒介像电子游戏这样注重享受,游戏设计可以说是建基于玩家的享受之上的,没有任何一款游戏会在设计时完全不考虑享受,享受不是单单决定了某款游戏好还是不好,而是所有游戏制作的根本出发点。
齐泽克追溯了享受的意识形态功能。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中,享受禁令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前的禁令要求我们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身的享受,而后现代资本主义“享受经济”要求我们必须享受。当享受的自由变成享受的义务时,享受也就不再可能。[8]换句话说,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享受的命令”,这种命令让人们在疲惫不堪的夜晚打开手机完成今天的游戏日常,让人们在午休时间迫不及待地来一把《开心消消乐》“放松”一下,让人们工作期间癫痫般地不断解锁手机,尽管没有任何新动态也要刷新两下朋友圈。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享受的权利,却再也不能放松享受,时刻都处于某种焦虑之中。
阿尔菲将享受看作游戏批评的关键。如上节所说,电子游戏精神分析的对象不是游戏文本,而是玩家,更确切地说,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流转的玩家的“享受”。为何《愤怒的小鸟》让人欲罢不能?为何《星露谷物语》是资本主义的共谋?为何《请出示文件》(Paper,Please)提供了一种不正当的快感?阿尔菲带我们从玩家的享受中获取答案。
阿尔菲首先介绍了《愤怒的小鸟》这样的游戏到底是如何捕捉我们的享受的。如今我们享受着成百上千种毫无意义的娱乐——手机游戏、社交软件、短视频软件——它们占满了人们的时间。这种毫无用处的享受看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大敌,但实际上它是将人们变成合格劳动力的强大工具。这类游戏对资本主义原则的暗中赞同不是通过提供一种成功感,而是通过自身的毫无意义和浪费时间来实现的。当我们在《开心消消乐》中“荒废”了五分钟再次回到手里的Excel表格时,忽然觉得自己平庸无聊的工作如此有意义。大量网页和手机游戏调动起了一种奇怪的愧疚感,它让人们在短暂的快乐后投入无尽的偿还和焦虑之中,让人们在白天玩了太多手机之后半夜奋发图强。
阿尔菲借本雅明之语将这种游戏称之为“分心的文化”,“分心文化不会阻止我们做真正重要的事”。阿尔菲说道:“它只会让我们相信,确实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这种分心可能看起来没有任何效果,但它会让我们更加坚信这个神话。”[4]40
《星露谷物语》自2016年发售以来一直在模拟农场游戏领域独占鳌头,这部由个人独立开发的复古像素类游戏截至2020年1月销量已过千万。游戏的开头,玩家扮演的角色处在一个现代办公楼的小小隔间中,冷漠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随后玩家收到了爷爷寄来的一封信,邀请玩家前往星露谷,继承爷爷的农场,回到真实而自然的农耕生活中去。游戏就此开始,在游戏中,玩家可以种庄稼、养牲畜、修整农场、装饰房子、钓鱼、地洞探险、参加村子的节日、与NPC互动,甚至可以结婚,同時随着剧情推进,还要和试图接管乡村经济的Joja联合公司做斗争。
阿尔菲指出,《星露谷物语》表面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孤立主义的撤退,它提供了一种怀旧式的享受,让人们回归到有机的集体生活。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生活本身从来没有存在过,对旧日的想象完全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中。《星露谷物语》塑造了纯粹自然的享受,避免了直面真实的对抗和矛盾,通过表面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抑制批判资本主义的真正可能性。
《星露谷物语》反映了如今潜在颠覆性的艰难政治处境——对体系不满表达总是被资本主义逻辑转化为完美的商品。但同时,《星露谷物语》也为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条线索:“反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脱离资本主义,不是说要跑到资本主义‘外边(outside)去,而是要反对你‘所在(inside)的结构。”[4]58换句话说,反资本主义不能变成一种幻觉式撤退,将整个资本主义生活排除在外,而是要深入其中,从内部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简言之,就是要给予资本主义的享受文化足够的关注,从自身的享受出发,才能如齐泽克所说的“认同症候”继而“穿越幻象”。
著名的反乌托邦游戏《请出示文件》往往被看作电子游戏中最具有颠覆性的那一类。游戏中,玩家扮演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边境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十分严密,与邻国的关系也非常紧张。玩家需要在游戏中选择是否要接受恐怖分子的贿赂,是否要帮助避难的移民,同时如果玩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主角的家人很快就会生病死亡。玩家必须在维护法律和保护家人之间,在违背法律和让难民送死之间做出选择。你可以加入无政府组织来对抗高压政府,但是家人会随时暴露在危险之中;你也可以接受政府官员的贿赂,但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弱势群体受苦。
《请出示文件》让玩家时刻面临道德和利益的抉择,似乎提供了一种对压迫性政治体制的反思,但是阿尔菲通过分析玩家的享受解构了这款游戏的颠覆性。阿尔菲指出,在这款游戏中,玩家的享受恰恰来自高压政府赋予的权力,也就是说,玩家作为边境检察官,有权对申请人的道德、处境进行判断,决定申请人能否入境以脱离目前的困境。这就是游戏的基本动力,也是玩家享受的根本来源。但是这一享受的基础是玩家政府官员的身份,玩家必须通过行使自己所反对的高压政府的权力,才能进行令自己“问心无愧”的选择。简言之,这种享受是打着违反法律的旗号对法律自身的享受。
通过对手机网页休闲游戏(《愤怒的小鸟》)、农场模拟游戏(《星露谷物语》)和反乌托邦游戏(《请出示文件》)的分析,阿尔菲为我们展示了资本社会享受的命令,它更像是一种义务,而非自由。《愤怒的小鸟》命令你在工作间隙赶快“放松”一下;《星露谷物语》命令你在资本社会高压下寻找一个纯粹自然的怀旧场所;《请出示文件》命令你成为权力代理人,完成自己的道德梦想。电子游戏成为一种享受的命令,要求我们不断投入新一局游戏中,“享受”游戏的快乐。
但同时,正如齐泽克所说:上帝死了,一切都不被允许了。当享受(enjoyment)变成一种命令的时候,享受(jouissance)却成了最不可能的时刻。
拉康式的享受指的是主体经历符号阉割后的残留物,即当婴儿进入符号的象征界的时候,就被迫与自己的原初享受分离。比如,孩子在长大后被迫与母亲割离,不再能完全占有母亲,需要依循作为“父亲之名”的象征秩序,由此,对母亲的拉康式享受就被禁止了。于是,拉康的享受是一种不可能的享受,它与快乐和性无关,而是主体进入象征界后的某种残留物。简单来说,拉康式享受(jouissance)是一个不可能的时刻,当享受(enjoyment)成了命令,当一切都成为可能时,这种不可能的享受(jouissance)的时刻也就销声匿迹了。
享受的命令是对快乐原则的追逐,而享受的时刻是“死亡驱力”的时刻,它包含着黑格尔式的否定,它不是一种快乐,而是超越快乐原则的痛苦,是一种在既有框架之下无法被阐释和理性化的享受。而阿尔菲通过对电子游戏的分析,从享受的命令里发掘出了享受的时刻,他告诉我们玩家为何会陶醉于这些游戏而不能自拔,这种享受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机制,又暗含着意识形态对何种享受的时刻的掩盖。
阿尔菲通过对电子游戏享受的分析告诉我们,如今的享受是非常危险的,它培养了这样一种话语——享受是最正当不过的,谁都不能干涉我的享受。但事实上,享受的命令塑造了我们的享受本身,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不能被阐释和理性化的过度享受,这正是享受的时刻,它向我们展示了意识形态想要隐藏的东西。
如何成为颠覆性玩家
阿尔菲在“导论”中指出本书中的根本论点有三:首先,电子游戏世界只有通过拉康的理论才能完全理解;其次,任何颠覆性尝试都必须在梦空间之内而非之外进行;最后,我们可以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通过揭示电子游戏中的意识形态和分裂的享乐发掘潜在颠覆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拉康精神分析,从电子游戏内部发掘其颠覆潜力。
在阿尔菲看来,不存在所谓的颠覆性电子游戏和非颠覆性电子游戏之分,因为“颠覆性的享受完全有可能将一个循规蹈矩的文本和一个循规蹈矩的玩家联系起来,同样,一个自认为是颠覆性的玩家,在参与一个他们认为非常‘激进的文本时,也可能体验到一种循规蹈矩的享受”[4]115。也就是说,游戏本身只有颠覆的潜力,却没有颠覆的本质,表面看起来越具有颠覆性的游戏,越容易成为资本所贩售的“抵抗”商品,它让人们产生一种抵抗的幻觉,似乎只要在游戏里种种田,或者打死几个贪污官员,就能完成自己的颠覆使命。在玩家、游戏和享受的三位一体中,只有玩家才是最有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存在,玩家可以揭示出游戏背后的意识形态,体验游戏分裂的享乐,释放游戏的颠覆性潜力。于是,如何成为颠覆性玩家就成了阿尔菲要解决的问题关键。
阿尔菲给出的答案正是拉康式精神分析,在本书的最后,阿尔菲借用瓜塔里——或者说德勒兹的“黑暗面”——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质疑:精神分析还能否在当今的主体性上运作?阿尔菲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对精神分析的拒绝太过仓促,在赛博人诞生、本体论变化的时代,精神分析的地位确将受到挑战,但是在这个如梦似幻的年代,我们也前所未有地需要精神分析。
阿尔菲指出我们首先要去掉精神分析中的两个东西:非政治化欲望和不可改变的主体性结构。“在一个技术和娱乐密不可分且无处不在的社会里,对技术的精神分析让我们看到的欲望、享受和愉快的新政治。这种理解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在这个世界里,不管你喜不喜欢,主体性都会被技术变化所改变。”[4]131阿尔菲在文中没有明确提及批判理论,但是他数次引用本雅明,并指出本书最关键的“梦”的概念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而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是我们于现代空间漫步时遭遇无尽能指与所指围困时的体验。显然,在阿尔菲对电子游戏的批评中,精神分析和批判理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精神分析对欲望和享受洞察和批判理论对文化与政治的透视相结合,构成了阿尔菲电子游戏批评的基础。
如何成为颠覆性玩家?答案正是将电子游戏看作一个“梦”,它是重新塑造人们欲望和享乐的梦境,也是繁荣奢华,让人们迷失其中的拱廊街幻境。通过精神分析与批判理论的结合,阿尔菲完成了电子游戏的文化批评实践,掀开了文化症候的一角,为文化的结构性颠覆和变革扩展了新的空间。
注释
[1]Bogost,I.How to Do Talk about Videogames[M].Minneapolis:Minnesota,2011:xi-xii.
[2][美]简·麦戈尼格尔.游戏改变世界: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329.
[3]周志强.否定性的批判实践——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分立[J].南京社会科学,2019(1):125-133.
[4]Bown,A.The PlayStation Dreamworld.Cambridge:Polity Press,2018.
[5]Galloway,A.Gaming:Essays on Algorithmic Cul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
[6]Cremin,C.Exploring Videogames with Deleuze and Guattari:Towards an Affective Theory of Form.New York:Routledge,2016.
[7]Haraway,D.“A Cyborg Manifesto”, inSimians,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1:149-181,151.
[8][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热·齐泽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雨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