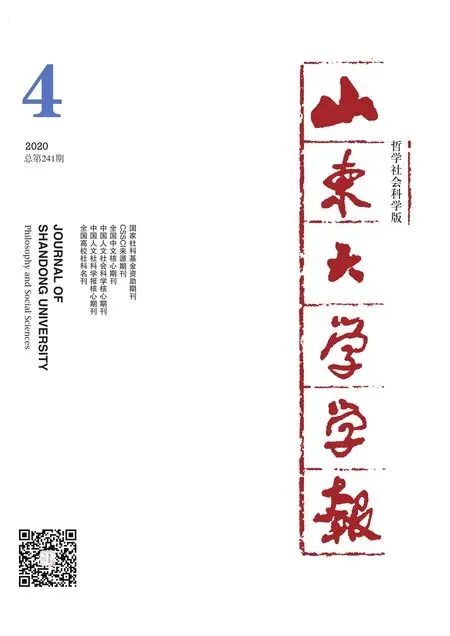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理性历久弥新
——重温恩格斯关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论述
王新生
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不仅与马克思一道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博览群书、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始终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学术前沿,对于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很多问题都有精辟论述。特别是,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一起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而且他本人还对于阿拉伯宗教文化的发展、伊斯兰文化的兴起等都提出了独到的科学见解。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这些科学论述,犹如沐浴熠熠生辉的真理之光,其理论真理、思想方法和问题意识历久弥新,始终是指导我们进行宗教文化研究的指针和法宝。
一、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
宗教可以说是与人类一样古老的人类本质现象的一种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具有的形式已经是歪曲了的和走样了的”(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而且这种“歪曲和走样了的”反映又因时间、地点、民族和文化等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和样态;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几乎从宗教现象存在那一刻开始,历史上对于宗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解或理论,其中有中国传统上具有代表性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说,有西方传统中代表性的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论,也有现当代各种宗教理论思潮,不一而足。同样,宗教本身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着力阐发的一个主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超越所有其他宗教理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把宗教现象放到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当中,放到克服人的“异化”和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去定位,从而揭示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而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确切含义,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那就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象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33页。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看来,宗教这种麻醉性的现象是与人的有限性相关的、受历史发展阶段和人的认识局限制约而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异化和颠倒。在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关键认识是,在人类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漫长征程中,人们不能沉迷于宗教这种“鸦片”所带来的麻醉,而是要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把在宗教幻象中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还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与科学的进步,宗教也会逐渐走向衰亡,而这个衰亡过程对于每个以人生为时间度量单位的人们而言则是显得无限漫长的。因为,“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自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56页。。
可见,迄今为止只有马克思主义把宗教放到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解放道路的大格局下加以分析和研究,最全面、最深刻和最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恩格斯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论述正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用于具体宗教文化研究的一个值得效法的典范。
二、恩格斯划分了蒙昧时期阿拉伯宗教文化发展的阶段
伊斯兰之前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中心,信仰万物有灵。蒙昧时期的阿拉伯宗教文化是由原始的闪米特沙漠信仰发展而来的。在阿拉伯的各个地方,尤其是在贝都因人当中,万物有灵论相当盛行,树木、岩石、洞穴、水泉和水井等自然物都受到极大尊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力崇拜。”(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在阿拉伯人的自然崇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于枣椰树、神石和水泉的崇拜。阿拉伯人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树木莫过于当属第一特产植物的枣椰树了,单单麦地那的枣椰树就有百种之多。枣椰树所结出的椰枣是除了骆驼肉之外阿拉伯人主要的固体食物,因此也成为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崇拜的对象。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对石头的崇拜也十分普遍,例如,塔伊夫地方的拉特神就是以一块方形的石头为代表的,彼特拉的左舍拉神则是以一块未经雕琢的长形黑石为代表的。(8)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0版(上),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87页。而阿拉伯宗教历史上受到崇拜的石头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嵌入阿拉伯半岛最为神圣的圣所克尔白的一角之中的一块黑色陨石,通常称为“玄石”。此外,“沙漠里的水井,有清洁的、能治病的、活气的凉水,故在很古的时代已变成一种崇拜的对象”(9)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0版(上),第86页。。水泉崇拜中最为著名的是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对于麦加克尔白不远处的圣泉渗渗泉的崇拜,这个井泉中的泉水对于环绕克尔白圣所的朝圣者们而言是圣水。
除了上述自然崇拜之外,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还流行过星宿崇拜和图腾崇拜。游牧的阿拉伯人为了避开白天的酷热,通常在月光下放牧他们的牲畜,由此形成普遍存在的以月亮为中心的星宿崇拜。就星宿崇拜而言,最为发达的是阿拉伯南方的拜星教(10)金宜久:《伊斯兰教概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页。。而且根据公元8世纪的依沙克和希沙姆的《穆圣本纪》的记载,伊斯兰教之前的麦加克尔白中曾经供奉有一只木鸽子和两只金瞪羚。在对鸽子、瞪羚、老鹰、秃鹫和骆驼的敬重之中可能已经包含着图腾崇拜。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上述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还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力崇拜”,“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06页。
在伊斯兰诞生前夜,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已经从上述自然崇拜发展到偶像崇拜,尤其是对于欧萨、默那和拉特三女神的崇拜最为著名。大多数阿拉伯人,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都在崇拜当地的神或女神。这样的一些神祇严格说来是部落神,还有一些则是主宰某些地理区域的“土地爷”。根据《穆圣本纪》的记载,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对于阿拉伯人中间偶像崇拜的起源有这样的说法:“我看到阿慕尔·本·鲁哈依在火狱中……他是第一个改变伊斯玛仪的宗教,树立偶像和制度化缺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免役驼习俗的人。”(12)A.Guillaume,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bn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p.35.
尽管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偶像崇拜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是学者们一般把伊斯兰诞生前夜阿拉伯人所敬拜的神祇归为如下范畴:一是在整个阿拉伯受到敬拜的至高神安拉;二是作为安拉女儿的“三女神”——拉特、欧萨和默那(53:19,20)(13)括号中冒号前后的数字分别指马坚先生译《古兰经》的章与节,不同的章节以分号隔开,下同。,其中的欧萨特别受到麦加的古来氏族人的敬拜;三是努哈同时代人的五个神祇(旺德、素瓦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四是其他大约35个有名有姓的神祇,其中的胡伯勒因为其人形偶像矗立在克尔白之中而最为著名。另外,阿拉伯人还在家中供奉家神,例如:“在麦加的每个家庭的房屋里,都有他们崇拜的一尊偶像。”(14)Hisham Ibn-Al-Kalbi,tr.by Nabith Amin Faris,The Book of Id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28.那时的阿拉伯人相信,所有这些神祇都有其创造能力,在世间事务方面比遥不可及的安拉更加活跃。(15)Jacques Waardenburgp,Islam:Historical,Social,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Walter de Gruyter, 2002, p.25.
就类似阿拉伯宗教文化这个阶段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偶像崇拜是略高一些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特点;处于最低阶段的部落,连偶像崇拜的痕迹也没有……偶像一般都采取人形。”(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67页。后来阿拉伯考古发现充分支持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阿拉伯人偶像崇拜的相关论断,例如,在公元早期的那些世纪的铭文中就发现了阿拉伯人普遍存在偶像崇拜的证据。此外,公元5世纪安提阿的以撒(Isaac of Antioch)也谈及阿拉伯人向偶像欧萨献祭,还有6世纪的证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莱赫米德(Lakhmid)皇室曾以拉特和欧萨起誓,并且以囚徒向她献祭。(17)PJ. Bearman, TH. Bianquis,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and W. P. Heinrighs,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Volume 10, Koninklijke Brill, 2000, p.968.正是因为阿拉伯人的头脑中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偶像,所以当伊斯兰教的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向他们传布一神教,告诫它们不能以物配主的时候,他们是无法理解的——“难道他要将许多神灵变成一个神灵吗?这确是一件怪事”(38:5)。
三、恩格斯发现了阿拉伯宗教文化向着一神教过渡的趋势
伊斯兰诞生前夜,阿拉伯宗教文化不仅完成了从自然崇拜到偶像崇拜的发展,而且以偶像崇拜为特征的多神教已经开始出现衰落迹象,在麦加及其周围出现了一个朝向一神教的运动。古莱氏人和麦加部落联盟的经济扩张带来了其对于一种更为广泛的、阿拉伯人都可以接受的宗教的需要,特别是在安拉的角色方面出现了一种扩展和增长,天界的权力逐步集中到了安拉身上,亦即“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上”(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33页。。与其同时,在整个阿拉伯半岛还存在一种共同的宗教语汇的传播。
研究表明,“纵使有一些地区性传统的发展,但是阿拉伯人形成了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传统的意识,这种意识——连同共同的仪式行为形式、共同的赖哲卜月(Rajab)朝觐、共同的对于安拉及其‘女儿们’的敬拜——又与下述深刻意识休戚相关:纵使不同的部落和氏族之间常见倾轧和斗争,古莱氏人治下的麦加这样的城市具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深刻意识到存在一些共同的经贸模式和政治效忠模式,以及他们共同构成一个民族”(19)Jacques Waardenburg, Islam: Histor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Walter de Gruyter, 2002, p.30.。
从《古兰经》的一些经文也可以看出,这时的阿拉伯人对于真主(安拉)并非一无所知,亦非毫不信仰,但是他们只是把安拉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创造神祇,认为这种高高在上的神祇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干系。(20)John L. Esposito, edited, The Islamic World: Past and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Volume 2, p.47.只有在少数事关生死的情况下,比如海上航行等情况下,这个神祇对他们才有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在蒙昧时期人们眼中的安拉并非唯一的神祇,因为他们还把许多女儿(37:149)归给安拉,其中包括上文提及的女神拉特、欧萨和默那(53:19-2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向这些“配主”寻求援助(6:136;10:18)。这就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所谴责的“以物配主”。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阿拉伯神灵世界出现的转折和变化一定是直接或者间接与游牧民族的定居化有关,与绿洲和城邑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新的宗教需要有关,尤其是与麦加商业社会的发展与新兴生活模式的出现有关。因为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生活在其中的背景,而这又反过来对于道德与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对此,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断:“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事实上,正是因为存在着麦加这样的商业城市生活模式和沙漠游牧生活模式的差异,阿拉伯宗教文化并非各处都是一样的。尽管出现了朝向一神信仰的趋势,但是在形式上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而且内部也并非没有冲突。例如,在游牧的贝都因人与像麦加人这样的定居民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传统;出现了带有膜拜的众神和众女神的扩散,此消彼长,沉沉浮浮;神明和精灵可以彼此靠拢或彼此分离;最终,在对至高神安拉的崇拜为一方面,与对“他的女儿们”、其他神明和精灵崇拜为另一方面的两种崇拜之间出现了张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因此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革。”(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3页。

四、恩格斯阐释了伊斯兰文化由之产生的社会动因
伊斯兰教是随着《古兰经》于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中西部的麦加城与麦地那城的启示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是阿拉伯社会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正如恩格斯1886年初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阐明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仅仅在这些多数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我们才发现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8页。
公元6-7世纪,中东历史舞台被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这两个“巨人”之间的争斗所主宰。就像当年华约和北约两大国际组织都努力争取相对弱小的中立国家支持一样,在6世纪和7世纪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也各自寻求扩大在阿拉伯的势力范围,以图压缩另一方的生存空间,而且双方都通过酬劳边境上的半游牧部落来阻止游牧部落对于人员定居国家的侵扰。正是通过波斯边境的希拉王国和罗马边境的爱萨西奈王国的桥头堡作用,以及传教士和阿拉伯商人的传播,外来宗教和文化渗透到阿拉伯腹地。在外来的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观念所带来的不同于原有部落集体人格的个人意识的同时,阿拉伯人经商所带来的不同于传统游牧生活的全新生活方式,则进一步催生了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观念,这与传统的部落集体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形成张力。这种张力通过下述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是商业社会的兴起。6世纪末叶,麦加商人取得了对于来往于阿拉伯半岛西部沿海边缘与地中海之间贸易的垄断性控制。《古兰经》中提及冬季和夏季商队:“因为保护古来氏,因为在冬季和夏季的旅行中保护他们,故教他们崇敬这天房的主,他曾为饥荒而赈济他们,曾为恐怖而保佑他们。”(106:1-4)传统上,冬季和夏季的商队分别向南和向北行进。南下的商路通往也门,进而通过曼德海峡延长到非洲对岸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此外货物还可能通过海路来往于阿拉伯与印度之间。

《古兰经》的语言和观念也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新的伊斯兰文化最初是在阿拉伯新兴的商业社会氛围中发轫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麦加的商业繁荣及其商队的经文之外,通过对《古兰经》中的“商业—神学术语”的研究表明,它们不仅仅是解说性的隐喻,更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古兰经》中可以归入此类的断言包括:人的行为被记录在“功过簿”上(69:19、25;84:7、10);最后审判是一种清算(84:8);每个人都得到他的账目(69:26);公道的天秤被支起(就像交换银钱或货物一样),人的行为被称量(21:47;101:6-9);每个灵魂因所作所为而抵押(52:21;74:38);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受到肯定,他得到酬劳,或工钱(57:18-19;84:25;95:6);支持先知穆罕默德的事业就是借贷给真主(2:245;5:12;57:11、17;64:17;73:20)等等。(27)W. Montgomery Watt, Bell’s Introduction to the Qur’an, 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
其次是穆鲁瓦制度的失效。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部落社会以血亲复仇和集体主义为中心的穆鲁瓦制度无疑是一种残酷的社会机制,但是它也滋养了一种深刻的、强烈的平均主义,鼓励了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漠然,从而慷慨成为一种美德,注重今生今世成为常态。穆鲁瓦制度在阿拉伯人那里长达几个世纪一直有效,但是及至6世纪,这种制度已经无力回应时代的变迁,结果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夕阿拉伯社会出现了广泛的不满和精神躁动。这种躁动源于外部个体主义观念的引入和经济生活带来的金钱崇拜对部落社会集体人格和集体主义传统价值的挑战。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贫富分化的出现,个人身份开始从部落的集体身份中分离出来,这为个体接受与原有集体人格信仰的传统多神教不同的新宗教提供了可能。
个体主义来自阿拉伯半岛周围更为发达的文明社会,主要是拜占庭和波斯两个强大的帝国。处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包围下的阿拉伯半岛,通过这两个帝国边境的阿拉伯人附庸国加萨尼王国和希拉王国渗入外部文化,同时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经商的商人带回文明奇迹的故事,带入外部文化的影响,阿拉伯半岛内地的人们开始有了模糊和初步的个体意识。新观念的渗入带来了从根本上削弱旧有公有道德的个体主义。例如,基督教的后世观念使每个人的永恒命运成为一种神圣的价值,这就造成如何与部落理想——个人服从部落、个人的不朽寓于部落的生存——相协调的问题。
第三是金钱拜物教的出现。麦加的古来氏人从游牧部落时期起着宗教作用的“穆鲁瓦”集体主义,变为定居和商业时期的金钱拜物教,认为金钱“拯救”了他们,感到他们依靠金钱而成了命运的主人,有些甚至认为财富使他们不朽。这种建立在财富之上的“自足”膜拜意味着部落集体主义的解体。进入经济社会之后,个体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竞争成为新的规范。个体开始积累个人财富,不再关心贫弱的古来氏人。每个氏族,或该部落较小的家族群体为分享麦加的财富而彼此争斗,面临着部落在内耗中出现道德和政治上的自我解体的危险。
概而言之,古来氏人定居和经商之后,取得了与旷野游牧相比而言的“得救”和安全生活,但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是他们的财富,主要基于个人努力之上的财富积累则催生了一些为富不仁的贪婪现象。财富观念和个体意识与原有的部落集体主义形成冲突,伊斯兰文化作为新的上层建筑就是旨在以安拉信仰为基础的新的集体主义取代原有的以血缘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并超克财富对集体主义的侵蚀。正如马克思在回复恩格斯有关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书信中所言:“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使我很感兴趣……在穆罕默德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五、恩格斯阐明了阿拉伯宗教文化新旧更替的实质
作为一种新兴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对于旧有的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的取代是在对于之前的多神教文化进行一神教改造的基础上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加工……”(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9页。
首先,伊斯兰教对蒙昧时期的宗教功修进行了改造。“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2页。伊斯兰教基于变化了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既有宗教的改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伊斯兰教把蒙昧时期已经出现的、尚有“以物配主”倾向的唯一主神论,发展为崇拜安拉、认主独一的一神信仰;把游牧部落原有的“酋长—诗人—卜人”权力结构收归唯独掌握真主所降示的真理的穆罕默德之手;把杂乱无章的崇拜仪式改造为“五番拜”;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相关节期创制为斋月;把穆鲁瓦原始共产主义改造为周济穷人的课功;把原有带有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麦加朝觐改造为以纪念和感恩安拉为中心的朝觐。而这种改造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伊斯兰的“五功”制度,即“伊斯兰筑基于五件事项之上: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履行拜功;完纳天课;朝觐和封斋”(31)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康有玺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其次,伊斯兰教针对蒙昧时期的多神信仰而确立了“六信”的信仰体系。“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宗教的这种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传统的政治设施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从属于此的宗教自然也就会崩溃。”(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97页。
伊斯兰教不仅吐故纳新,确立了伊斯兰教的五大功修,而且确立了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归信真主的人们!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4:136)伊斯兰教信真主是独一的主,所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的多神教信仰;信天使是真主的仆人和崇拜者,所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把天使误以为是真主女儿的观念;信经典是来自真主的启示,所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人们对于受到精灵(镇尼)蛊惑的诗人和卜人的言辞的轻信;信穆罕默德和列圣是主的使者,所针对的是“有经人”对穆圣身份的质疑及其把尔撒(耶稣)神化的错误;信末日实际上一是信万事万物都由真主前定——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人们所信的时间决定一切的宿命论,二是信来世天园和火狱的赏罚——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人们只顾今生今世、不行善积德的陋习。当然,这六信在破旧立新方面的作用是相互支撑和互为补充的。(33)王新生:《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第三,伊斯兰教是对于古老一神教的返璞归真。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既有一神教的关系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势不两立,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通常被统称为亚伯拉罕宗教,因为它们都认亚伯拉罕(易卜拉欣)为始祖。伊斯兰教所认可的先知不仅包括阿拉伯先知,而且包括诸如阿丹(亚当)、努海(挪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尔撒(耶稣)等等“圣经先知”;伊斯兰承认属于《圣经》的“讨拉特”“则逋尔”“引支勒”为“天经”,其中有“光明和向导”,但是因为其中也存在人为的篡改,所以只有“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85:22)的《古兰经》是无谬的。所以,伊斯兰教把《古兰经》的教导看作是对先前的、有别于多神教的古老一神教(像犹太教和基督教)教导的一种再肯定、一种去伪存真的更新,是恢复易卜拉欣的正教。《古兰经》中不乏这样的明文:“你说:‘我们确信真主,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伊斯玛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尔撒和众先知所受赐于他们的主的经典,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归顺他’。”(3:84)
一旦认识到上述这一点,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一脉相承的渊源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所有的先知和使者都是“穆斯林”,即都是些归顺神的旨意的人们,而且他们传布顺从全能的神,就是传布“伊斯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斯兰教并非是诞生于公元7世纪的一种新的宗教,而是“复兴”神通过在穆罕默德之前的众多使者们业已向每个民族启示过的那同一个宗教。穆罕默德不是来改变先前的先知们所带来的信仰“一神”的基本教训,而是相继确证和刷新这一信仰“一神”的基本教训。“先知啊!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为报喜者,为警告者,为奉真主之命而召人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33:45-46)
对于伊斯兰教的这一立场及其与先前古老一神教犹太教的关系,恩格斯基于他那个时代的最新考古和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认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复古和返璞”:“从阿拉伯的古代碑文中显然可以看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任何宗教运动一样,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璞。在这些碑文中,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的一神传说还占优势(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一样),而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只是它的一小部分。”(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0页。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不仅在学术上言之有据,而且也符合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关系的实际。
六、结语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通过重温伟大导师恩格斯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论述,再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理性历久弥新。恩格斯亲身示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博览群书、勤以思考、努力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始终站在时代学术顶峰的大师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当代学人铭记和效法。特别是,恩格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方面的真知灼见给予我们巨大的理论勇气,鞭策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