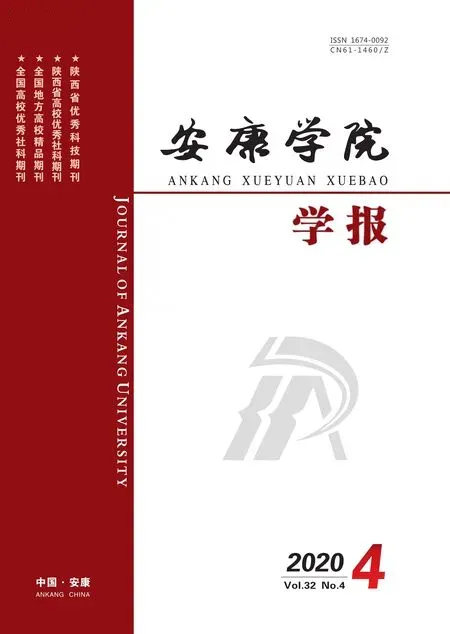论张爱玲《怨女》的空间叙事
李德慧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怨女》讲述了麻油西施柴银娣为改变命运嫁入姚家,一跃成为姚二奶奶的故事。在作品中,张爱玲通过银娣个体的反抗和挣扎,展现出那个时代女性群体的边缘地位和生存焦虑。对于这部作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锁记》与《怨女》的比较分析、《怨女》的自译、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角度解读《怨女》等方面,本文以“空间叙事”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旨在揭示“空间”这一因素在《怨女》中的作用以及空间与人物、时间的互动,进而试图从物理活动空间深入到人物的精神空间。
一、《怨女》空间叙事的类型
“地理并非惰性的容器,不是一个文化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盒子:它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弥漫于文学领域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它。”[1]空间这一因素和文学的联系已经日益密切,如“上海学”“北京学”“江南学”、巴蜀文化等悄然兴起。纵观现代文学,地域“空间”依旧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成都之于李劼人,湘西之于沈从文,它们像是一个个历史的核心现场,凝聚着当时的意识和形态。同样在张爱玲的《怨女》中,“空间”这一要素依旧活跃在文本之中,并主要呈现为两种艺术形态:物理空间和女性空间。
(一)物理空间
《怨女》中的物理空间分为麻油店、姚家、老式洋房。首先麻油店是银娣婚前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张爱玲通过这一地点点明了银娣的社会阶层:和哥嫂生活在一起,靠卖麻油为生。小说中对麻油店的整体布局没有进行细致的描述,只是在人物活动时顺带写过,从中可以推测麻油店是二层的建筑结构,一楼是卖麻油的商铺,二楼属于家庭住所。一楼作为商铺,属于公共空间,银娣在柜台后卖麻油,总会惹来男子看,这就说明银娣的外貌条件是很优越的,她有很大机会选择自己的爱人,阻碍之一就是哥嫂为了省下嫁妆钱一年年搁置她的婚事。另一局部空间是楼梯,“在狭窄的楼梯上,姑嫂狭路相逢,只当看不见”[2]163。银娣和嫂子并不和谐的关系通过楼梯这一空间巧妙传达出来。同样是在麻油店中,银娣外公外婆来借钱的场面更让银娣坚定告别贫穷的想法,麻油店这一物理空间,不仅仅是空洞的建筑物,更真实地反映了银娣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于婚姻的看法,从而为银娣后来嫁入姚家埋下伏笔。
其次是姚家。给老太太请安是姚家的惯例,这一不成文的惯例实际上代表了封建性的习俗,经过时间的过滤已经成为姚家晚辈所默认的一套规则,在姚家盛行的这套惯例之下遮掩的则是大家族中鲜明的等级观念,对封建家长老太太的惟命是从,使得银娣这样出身低微的儿媳妇被下人瞧不起。银娣的谋求进入和姚家这一空间依据自己的秩序对她的排斥形成了《怨女》的内在动力。姚家的这种等级性使银娣不甘于苦守毫无生气的丈夫,和三爷开启一段藕断丝连的畸形关系。传统礼教浸透下的家族空间,特别是像姚家这样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大家族,等级观念愈加深厚。张爱玲旨在通过姚家的“这一个”实体空间,以此揭示出中国旧式大家族的封闭,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麻木。
最后是银娣分家之后居住的老式洋房。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包括不同功能的区域,如厨房、书房、卫生间等,而对这些区域进行划分的是像门、窗这样的分隔物,它们不仅能够分割空间,还能连接空间。门作为分隔物被张爱玲运用于《怨女》的空间叙事中。白漆拉门连接了饭厅和客厅两个空间,当姚三爷第二次来找银娣,两人在未开灯的客厅中度过了一段时光,此时客厅将两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而及时将过去的眷恋打破的是银娣,由此两人的活动转移到饭厅。饭厅这一空间,使两人迅速回到当下的现实世界,也为姚三爷后来失控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催化剂——酒。银娣和三爷在饭厅喝了玫瑰烧,从开始“她喝了两杯”,到“三爷再来一杯”,“老妈子替他斟了酒”,“她剩下的半杯一口喝了下去”,“打杂的打了酒来”等饮酒程度的不断加深,两人的精神状态慢慢放松,酒成为饭厅这一空间的组成部分。而后人物活动又转移到客厅,如果说饭厅作为日常饮食的地点,还有打杂的和老妈子出入,那么客厅的私密性更强。在封闭私密的客厅中,在酒精的催化下,三爷和银娣两个人的行为越来越亲密,在激烈的挣扎中,生动地展现了两人的心理空间:三爷的表露心迹和步步紧逼,实为借钱;银娣的步步防守,更是断掉了对感情的最后一丝希望。“门可以分割空间,造成门内门外的空间转换和心理转换。”[3]当客厅的门打开之后,一切回归平静,也意味着两人关系的彻底破裂。客厅——饭厅——客厅,是由门这一分隔物连接的,在客厅中是情欲纠缠的过往世界,饭厅则象征冰冷的现实世界。门把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段,饭厅和客厅两个空间连接起来,进而形成了小说的叙事动力。
(二)女性空间
张爱玲在《怨女》中塑造了银娣这一主人公,而在银娣生活的不同空间中还存在众多女性,她们的生存状态共同构成了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空间。银娣出嫁前生活在麻油店,哥嫂因为拿不出嫁妆钱给她介绍了瞎眼残疾的姚二爷。当她嫁入姚家后,上要服从老太太,下被佣人看轻,自身情欲无法正常释放,因为卑微的出身,甚至连三奶奶珠花被偷也要怀疑到她身上。和三爷的畸形关系更是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下慢慢结束,得到的只是三爷的戏弄、欺骗、和以借钱为目的的表白。银娣被等级观念一步步吞噬,而生活在姚家的其他女人如大奶奶、三奶奶,甚至老姨太太们,无一例外都要坚定得维护这套封建秩序。连奶奶们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老夏妈这样身份低微的下人了。张爱玲在这里,揭示了女性的第一层生存空间——被食,以此凸显女性个体空间在封建氏族空间的强势主宰和控制下不断地被挤压的处境。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犀利的笔调在家族空间里塑造“狂人”这一形象,通过展现狂人个体与主流空间的差异性,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相。张爱玲和鲁迅在两部作品中共同揭示出人类存在的生存焦虑,然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并未对作为旁观者的女性形象展开深层次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做了进一步的延伸。
女性的第二层生存空间——自食。银娣最终走向悲剧的命运,既受到传统观念的戕害,同时也有自身画地为牢的不觉醒。她是出名的麻油西施,本来有足够的机会和自由挑选自己的爱人,如药店的小刘。可是她又不甘心过平淡贫穷的生活,在两情相悦和靠婚嫁改变命运之间,她最终选择后者。一旦选择嫁入姚家,也就意味着她感情生活的苦闷与压抑,而对情欲的渴望又让她陷入和小叔子的畸形关系之中。银娣的出身使她无比热衷金钱,不顾一切地捞取钱财,最后成为一个“清醒的疯女人”。
“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难者不肯忘记将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4]如果说银娣在做大姑娘和儿媳妇时代饱受被食与自食的苦痛,那么当她熬到自己成为婆婆时,便疯狂发泄心中的恶念,成为凶狠的报复者和食人者,于是形成女性的第三层生存空间——食人。由于内心情欲长时间得不到释放,让她产生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甚至公然在牌桌上讲儿子媳妇的秘密,把自己的丫头冬梅许给儿子,最后折磨得儿媳病死。银娣一步步毁掉自己的生活,又要牺牲儿子的幸福以寻求安慰,传统意义上神圣的母亲形象早已解构,最终只能孤独的走向悲剧的命运。被食——自食——食人,形成了一个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食人者不会永远处于顶端,被食者总有机会上位,在这样的循环之下,女性的生存空间愈发狭窄,她们不仅要承受社会主流空间对女性空间的压迫,还要忍受女性空间内部的相互碾压、争斗。
二、《怨女》空间叙事的形式
弗兰克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提出了“空间形式”这一概念,从博尔赫斯笔下《曲径分岔的花园》中迷宫式的形式,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圆拱形”空间形式,再到鲁迅《呐喊》 《彷徨》中或开放或封闭的空间形式,空间形式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具体到小说《怨女》中,空间形式主要表现为:并置式和圆圈式。
(一)并置式
《怨女》中主要表现为以银娣对麻油店、姚家和药店的不同感受实现三个空间并置。张爱玲没有将这三个空间单纯得设定为实体性建筑,而是分别赋予它们更深厚的社会内涵。在麻油店中,日子虽然平淡,银娣和哥嫂时有摩擦,但总体来说是放松的状态。麻油店这一空间同样决定了银娣所处的社会阶层,正是生活在这样底层的环境中,银娣看到了贫穷和等级,她不想长久过这种日子。和麻油店处于同一社会层次的还有小刘所在的药店,药店在麻油店的对面,距离上的靠近很容易使两个空间发生联系。银娣和小刘之间曾有过隐秘的交往,小刘给银娣偷带过一大包白菊花,银娣“一直喜欢药店”,对小刘也有好感,然而小刘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让她陷入理性的思考。于是她为改变窘境嫁入了姚家。在她看来,姚家是大家族,是权贵的象征,银娣一跃从麻油西施变为姚二奶奶,由此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跳跃。张爱玲通过描写银娣对麻油店、姚家和药店三个不同空间的认知,把不同等级的地点并置在一起,直接凸显了银娣的心理变化过程:弃贫从富,弃情守利,进而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和阶层。
(二)圆圈式
圆圈式叙事形式强调的是小说中开头和结尾的前后呼应。在小说的开头,木匠一声声喊着“大姑娘!大姑娘!”引出银娣出场,并描述了银娣女孩子时期拿灯烧木匠的手的场景。而终点场景是银娣晚年时期把油灯凑近小丫头的手,同样伴随着“大姑娘!大姑娘!”的喊声,两个相似的场景使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现在和过去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形的轨迹,把银娣一生的悲欢喜怒都夹杂其中。以银娣对木匠的反抗揭示银娣性格的开端,以银娣对小丫头的举动为这种揭示的终点,这之间银娣所有的人生经历、心理变化都被细密地编织进这一圆形结构之中。这是物理空间不同而场景类似形成的封闭,这样的圆形结构既使小说结构完整,又使小说外观显得齐整、有序。正如作者在文中写道:“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有经过什么事。”[2]238银娣的一生都在压抑和扭曲中度过:低微的出身、被压抑的情欲、和小叔子的畸形关系、人性的异化,而最后似乎一切又回到原点,从未发生过什么,是非成败转头皆空,更加剧了小说的悲剧性意味。
三、《怨女》空间叙事的意义
“空间是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折射到现实的具体镜像。”[5]张爱玲以“空间”为切入点进入《怨女》的小说叙事中,既开拓了小说的主题意蕴,同时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形式,由此使《怨女》的空间叙事呈现出张爱玲独特的印记。
童年经历和人生体验是张爱玲文学空间感形成的基础,破败后的家族、被父亲囚禁过的房间、生活的公寓等现实中的种种空间带给她不同的体悟,当这些体悟汇聚到小说叙事中,形成一个个带有人物情感印记与当时社会维度的物理空间,这些空间超越了本身的建筑形式,打上深层次的精神烙印。一方面,《怨女》通过描述不同类型的空间,还原琐碎日常的真实,展现十里洋场的世俗人生;另一方面,在不同空间切换的过程中,揭示女性在传统伦理和自身性格的双重束缚下,无法摆脱的悲剧宿命。张爱玲旨在进一步探讨像银娣这样的女性,无法安分于所处的底层空间,尽管凭借一己之力进入上层空间,又时时被其排斥,从而开拓出《怨女》的另一种主题意蕴——“人在空间外”的生存焦虑,不仅仅展现女性群体处于空间之外的尴尬处境,进一步延伸至小说一切人的生存状态。
《怨女》中空间叙事的建构有力体现了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尽管张爱玲笔下的空间形式没有太过为人称奇的创新与突破,但以“空间”这一因素进入《怨女》的文本创作,打破了传统小说按时间顺序进行叙事的一维模式,实现了空间与时间、人物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充实并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空间叙事的研究。叙事与时间的紧密关系,几乎已经得到国内外叙事学研究者的认同,而对空间的关注却没有形成相应的平衡。如尤迪勇所说:“任何一个事件都既是时间维度的存在,又是空间维度的存在。”[6]通过对张爱玲小说《怨女》的空间叙事分析,我们了解到叙事学研究既有时间的参与,也有空间的建构,两者共同形成巴赫金所说的“艺术时空体”。由物理空间至精神空间的提升,为《怨女》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现代文学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
四、结语
张爱玲从“空间”维度展开《怨女》的文本叙事,旨在通过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探索女性的精神园地,进而思考:在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下,女性如何才能挣脱传统观念的枷锁,克服自身性格的缺陷,实现“灵与肉”的结合,进而自由享受“淡淡的音乐和淡淡的喜悦”。这是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深切观照,也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