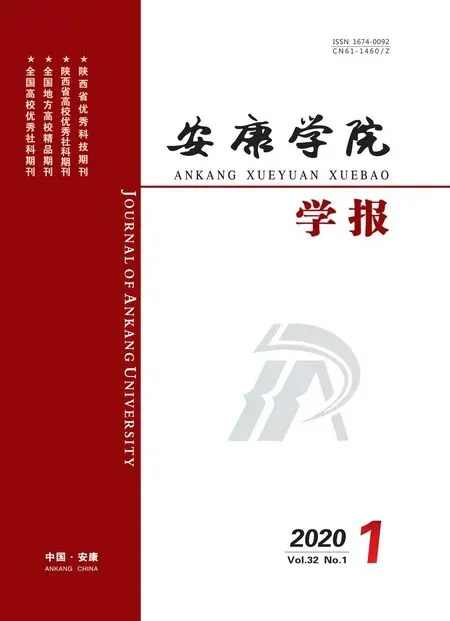激进与徘徊:论熊佛西的《长城之神》
倪金艳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二十世纪初,话剧艺术传入国内,为了扩大接受范围和建设“国剧”的需要,剧作家们有意识地对中国传统题材进行创作改编,而尽人皆知的孟姜女传说自然也被纳入改编范畴。相对于剧种丰富的姜女戏,话剧《孟姜女》要少得多。比较知名的有熊佛西的《长城之神》和谭毅、一行的《孟姜女》,虽然这两个剧本演出的机会不多,但前者代表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勇敢追求自由幸福的时代潮流,后者是典型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哲学戏剧。此二剧塑造的形象和表现的主题不同于以往所有题材,带给观众巨大的思想冲击,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对熊佛西的话剧《长城之神》进行分析。
四幕剧《长城之神》,是熊佛西1925年在纽约创作完成的,1926年3月22日到4月12日在国内《晨报副刊》连载,这是其继《甲子第一天》《当票》之后在美国创作的第三个话剧。目前,这部话剧仅收录在《佛西戏剧》中,其他地方未见踪影。这可能与本剧的浓厚趣味、噱头有关,也和当时或当代的批评不无联系。闻一多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佛西之病在轻浮”,“佛西乎,岌岌乎怠哉!至于剧本中修辞用典之谬误尚其次者,然亦轻浮之结果也”[1]。丁罗男评价道:“作者把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悲剧故事编排得相当累赘、离弃,并夹杂许多无聊的插科打诨,冲淡了题材本身的反封建意义。”[2]诸多的负面评论影响了《长城之神》的传播和接受。虽然此剧确实存在过分注重“趣味”和噱头的缺陷,但无法掩藏它在结构、思想方面的光辉和形象塑造上的突破性,故而笔者挖掘其价值,试为此剧“平反”。
一、塑造了五四新女性,突破了因因相袭的“固化”形象
孟姜女故事在民间传说、戏曲、歌谣中塑造的形象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延续了史述与诗词叙事所树立的守礼、痴情、贞烈形象,但从话剧开始,传统形象得到突破,甚至是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熊佛西的《长城之神》中的孟姜女是受五四新思想熏陶的女性,类似于庐隐、冯沅君、丁玲等作家笔下追求自我主体的“莎菲女士们”。孟姜女“不但穿着摩登衣履,并且富有新时代的头脑,所以她才有破坏长城之神的勇敢,才有艰苦卓绝的精神,才有始终热烈的爱情”[3]。
一方面,以“新女性”姿态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当姜父盘问万喜良时,孟姜女“只是不住的瞅着万喜良”,大有眉目传情之意;丫鬟频儿打趣道:“因为小姐很喜欢这个叫花子”,孟姜女也不做过多的反驳。为了说服父母留下万喜良,孟姜女先是机智地夸赞他虽是落难书生,但“我看此人非凡,将来必有发达”,“当然是个书香门第,将来也许有大发达,只要他肯用功上进”[4]。“万喜良现在是境遇不佳,可是他长得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将来难免发达。”熊佛西依照传统戏曲“落难秀才中状元”的套路,从功利性角度劝说守旧的父母,把救助万喜良作为投资,以享他日荣耀。可想而知,劝说无济于事,丝毫不能打动保守的父母。于是,她索性将计就计搬出少时许下的夙愿“将来应嫁给第一次见她的手膀的男子”,如果父母不同意宁愿死,果然立竿见影。机智的孟姜女终于保住了万喜良,为后续剧情发展埋下伏笔。
孟姜女的魄力在得知爱人惨死后完全被激发出来,殴打神庙,怒对军差的指责:
军差:难道你不怕王法吗?
孟姜女:我的生命尚且完了!我的一切都乌有了,还怕什么王法?
军差:难道你亦不怕神打么?
孟姜女:神打!哼哼!(冷笑)神已经杀了奴夫万喜良,那就是杀了我!杀了我的一切!万恶之根源,长城之神![5]
孟姜女飞蛾扑火般地追求婚姻爱情,而爱人却死于长城,她毅然选择报复,发誓与罪魁祸首——长城,视死同归。
另一方面,认识到作为独立的人的价值,追求男女平等。父亲问她:“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如何去得了长城?”孟姜女坚定地回答:
男人亦是人,女人亦是人,你们既可以单人独马,远别家乡到数千里外去,难道我们做女子的就不能够吗?[6]
此话明显带有五四运动时期的意味,受新文化洗礼的熊佛西懂得女性不是男人的附庸,更不是男人满足性需求和孕育生命的工具,而是有思想的独立个体。孟姜女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与丫鬟以姐妹相待,关爱年老啰嗦的高寿,对不相识的叫花子也给予怜悯同情,这都是新女性孟姜女的优点。
虽然孟姜女具有五四新女性的果断勇敢,但也不可避免地兼具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彷徨的软弱性格。孟姜女得知丈夫被祭长城后,先是本能地在长城庙前犹豫、披头散发,跪着望天呼唤“天呵!天呵!”甚至一度昏厥,如此三番四复。在精神上自我调整后方鼓起勇气、举起锄头,击打庙神,边捶边歇斯底里地诅咒:
长城之神!我把你这万恶的长城之神!我把你这残暴的万里长城!你!你!你不但不能保护人们,如今反伤害了无数的生命!你!你!你!吃……吃了奴的夫,伤了无数的命!
……
如今——如今——我要与你拼命!我要与你拼命!我要与你灭亡!我要与你拼命!我要与你灭亡!我要你沉到海底——无底的海底——永远沉到无底的海底!我把你这长——城——之——神![5]
孟姜女把小小的长城神庙打得东倒西歪,体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然而剧情突转,军差责问:“难道你亦不怕你的丈夫死后受折磨么?难道你亦不怕你的父母遭神打呢?”听到这些质问,孟姜女潜在的封建保守思想开始“发挥作用”,泪如雨下,跪地求饶:
神!神!全能的神呵!你宁可将我砍成肉饼,只求您保佑奴的双亲!……你宁可把奴打到十八层地狱受永远的苦刑,只求您!苦苦地求您——永远不要再折磨奴的夫万喜良!长——城——之——神——呵——[5]
前后态度的急剧转变反映了其性格的矛盾,既追求自我、追求自由爱情,与压迫势力抗争,又受传统封建观念约束,摇摆不定,最后以妥协告终。
熊佛西赋予孟姜女激进与徘徊的性格,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共性。但这不能掩饰编剧对追求自由、平等的孟姜女角色的偏爱,更重要的是,以觉醒的孟姜女这一新女性形象启发民众,发挥戏剧开启民智的功能。孟姜女体现了对爱情的自觉追求,对平等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借助演员的表演而引导着观众对民主进步思想的认知。然而,民主自由之路,任重道远,五四时期,当易卜生《玩偶之家》译介到我国以及《新青年》开设易卜生专号以后,国内女性的自我意识渐渐觉醒,纷纷效仿娜拉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可是,社会经济制度并没有提供接纳机会,女性的出走注定无实际效果,因此鲁迅在《娜拉出走以后》断言,出走的“娜拉们”要么回来,要么堕落。
二、堪称完美的叙事结构
戏剧要在固定空间、时间内表演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那么,有效地选择、提炼、组织、裁剪情节对戏曲举足轻重,甚至是一部戏能否成功的关键。《长城之神》在结构方面有优长之处,梁实秋先生坦言自己在读过《长城之神》后认为这是“在艺术上毫无缺憾”,“紧凑的结构,处处吻合,丝丝入扣”,“人物上场下场自然”[7]。这与熊佛西秉承的剧作观相关,即“剧本不好,一切都是徒劳”。此剧在情节安排、悬念设置、营造高潮和功能性人物方面,独具匠心。
第一,谨慎的安排,内容层层递进,情节铺展水到渠成。剧本按照时间顺序,围绕孟姜女的人生经历编织情节,讲求情节血脉相连、紧凑衔接、环环相扣,切忌突兀。《长城之神》力争做到前呼后应,使剧情层层推进,浑然一体。第一幕点明故事发生空间,两个军差看到万喜良逃到孟家花园,立即进园搜查,本幕结尾衙门再增派衙役捉拿,首尾呼应。编剧安排高寿去买绳子系葡萄架,看似不经意的一笔也含有大文章。高寿的缺席正好给万喜良谎称自己是“陶兰”逃难至此的机会,他假装自己仅是落难叫花子,以勾起孟家母女的怜悯之情。恰在此时,高寿拿着绳子将万绑缚起,揭露他作为皇帝钦点逃犯的真实身份,全场大惊!如果万喜良仅仅是“清白无辜”的乞丐,孟家留宿他最多是冒着被邻居耻笑、败坏小姐名声的风险,而现在万喜良是有罪之人,收留他就是窝藏逃犯,全家的命也难保,矛盾迅速升级,逼迫孟姜女亮出底牌。有了这段内容,再安排孟、万二人结成连理,顺理成章。
孟姜女戏剧本是一出难以驾驭的剧,它的情节并不复杂,可资渲染的细节也不多。加上观众对故事内容耳熟能详,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引来质疑。为了让剧目情节跌宕起伏,熊佛西增加了逃役的兄弟二人谄媚讨好与老妇人诘难的桥段,并让孟姜女在官兵的逼问中精神崩溃,结束整部剧。这些情节的加入让此话剧内容丰富起来,也实现了对孟姜女故事的一次拓展。
第二,留白,存有悬念。《长城之神》以地点转换为线索,孟宅的后花园、孟姜女卧室、荒山破庙、长城脚下的坟地。地点变化推动剧情发展,每换一个地方,情节也随之推进,且此剧每一幕都可单独演出,剧本灵活性强。更巧妙的是设有多重悬念,第一幕结束后,万喜良在花园石硖中躲避再来搜查的官差,至于是否找到和找到后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全部省略;第二幕直接过渡到孟姜女卧室,频儿鼾声大作,孟姜女神思恍惚、寝食难安。在四幕剧中前三幕的结尾都留下悬念,而在新一幕的开始,另起炉灶,中间解决的方式由观众思考,充分调动了每一位接受者的想象力。第二幕姜母不同意女儿去长城,母女二人相拥而泣,剧情戛然而止,第三幕开篇已经跳跃到寻夫途中的荒山破庙,演绎兄弟二人的滑稽行为。第三幕结尾是山中老虎追赶,兄背孟姜女拼命逃跑,第四幕已经到了长城脚下的坟地,二人如何脱离虎口,姜女如何摆脱兄的欺负,均不得而知。奇妙的是,这些缺失的内容并不影响剧情的完整,反使收尾利落、不拖沓,也能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是非常经济的处理方式。
第三,善于营造高潮。“高潮,即全剧最紧张的一点,最完整地表现了剧作家心目中的现实发展规律”,也是最能调动演员和观众的部分,高潮“牵涉到人物和他们的环境之间平衡状态的一定变化的动作”[8]。这部剧入戏快、情节紧凑、环环相扣,起承转合恰到好处,而且高潮迭出。笔者简单梳理高潮如下:
(1)孟姜女苦苦哀求父母时,家丁揭露他逃犯的身份→矛盾迅速激化。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习总书记所指出的“四有好老师”的首要标准。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是辅导员最为重要的工作职责。而要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辅导员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练就好“看家本领”,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原理,同时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会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决学生工作中的问题,这样才能做好学生理想信念的坚定传播者。
(2)孟姜女以理说服父亲的反对,但面对泪如泉涌的慈母,于心不忍,母女撕心裂肺→情感的高潮。
(3)老虎追击孟姜女和“兄”,姜女遇难→危机高潮。
(4)老妪怒责挖了她丈夫坟墓的孟姜女,众人劝解→趣味性高潮。
(5)孟姜女击打长城庙被官差训斥,内心极度惶恐→精神冲突高潮。
每一幕都有剧作者精心设计的高潮,使剧本张力十足;而绵密的高潮亦成为剧中的“兴奋点”,以吊足观众胃口,也使审美情绪由轻松调笑渐趋紧张,推动阅读或观看体验抵达顶点。
这有什么稀奇!造长城死的人多着啦!我的丈夫是造长城死的!我的儿子亦是造长城死的!这有什么稀奇!你以为凡是造长城死的就是你的丈夫吗?那么,这坟地里的人都是造长城死的,难道他们都是你的丈夫吗?[5]
老妇的指责讽刺看起来轻描淡写,实则交代了修筑长城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以至死伤无数,家破人亡;更可悲的是人们已经麻木了,不仅不悲戚,反而哈哈大笑。孟姜女矛盾性格的表现就是缘于军差的话语刺激,把思想解放的不彻底性展现出来,方有了孟姜女跪地、哭泣、忏悔、惊悸、绝望而死的系列行为。逃避苦役的两个兄弟和孟姜女前后矛盾的行为共同影射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的软弱,一方面信誓旦旦要与过去决裂,标榜是自由、自我、独立的新青年;另一方面又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左右,犹豫不决。熊佛西没有一味高扬反叛精神,而是真实地摹写了彼时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增加了主人公形象的真实性。总之,情节层层推进、留白使悬念叠生,辅以五个高潮,使《长城之神》的结构堪称“完美”。
三、立足于舞台演出效果的趣味
对《长城之神》批评的焦点就是“趣味主义”,认为无聊的插科打诨让作品冗长混乱,笔者并不赞同此观点。虽然《长城之神》确实重视调笑氛围,也存在文本叙事脱离情节的科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剧目的严肃性,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反而这些“瑕疵”使此剧适合舞台演出,无怪乎梁实秋断言“排演起来必定头头是道”。
熊佛西力争让《长城之神》情节有趣、人物有趣、话语有趣,而不是卖弄低俗趣味。情节有趣方面,两个军差因可笑的理由发生口角争执,进而挥剑相向,打得不可开交,而姜父却站在后面尽情欣赏刀法,并放言“可否再请他们来耍一次给太太小姐看看”;破庙里两个兄弟劈了神牌位烤火(神牌代表封建思想,劈掉象征着摧毁传统思想,而后头疼又忙不迭地的跪拜,这暗示了与过去决裂的不易),纷纷向孟姜女献媚的滑稽场面;孟姜女误挖了老妪丈夫的坟墓,老妪还以为老伴有了外遇与她争执等等。小幽默频现使悲情剧不至于太过伤感。人物趣味性方面,《长城之神》中笨拙愚钝的军差、憨厚的频儿、爱吹嘘的高寿、滑稽的两个兄弟,都是“有趣”之人,他们的言行举止都表现了滑稽的趣味。高寿啰里啰嗦,常常煞有其事地向太太告状,也在醉酒时说些无伤大雅的狂话。丫鬟频儿笨拙愚蠢、贪吃,当小姐彻夜难眠时她鼾声大作,时不时冒几句梦话;她惦记姑爷好是因为姑爷不吃的都给她吃,不玩的都让她玩。语言谐趣方面,庙里兄弟两人争献殷勤,兄:“贤弟,你不是要睡吗?你先睡吧!”弟:“我不要睡,我说大哥,你不是头痛病吗?”兄:“头痛?不!不!早就不痛了!”……兄:“我是哥哥,我叫你去!”弟:“我是弟弟,我偏不去!”兄:“对!王小姐是极公平!叫他们兄弟俩同去!”[9]两个各怀鬼胎、色眯眯的无赖活现在读者眼前。
熊佛西在剧中设置多处调笑情节表现了他的戏剧观。熊佛西是一个为演出、为观众写戏的人,他坚持戏是为普通观众写的,“戏剧是以观众为对象的艺术,无观众即无戏剧。无论你的剧本艺术是何等的高超或低微,假如离开观众的趣味与欣赏力,其价值必等于零”[10]。民国时期人们的识字率较低,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欣赏水平与当下无法相比,人们喜欢悦人耳目、谐趣、滑稽、奇巧的作品,所以特意在剧中加入趣味性内容,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长城之神》趣味化、“平民化”的美学特质,符合民国时期平民大众的接受心理。也正是因为熊佛西把握读者、观众的接受心理,努力让“戏剧大众化”,避免话剧沦为少数知识分子的艺术。
《长城之神》除了人物形象塑造、剧本结构和立足舞台演出的趣味等文学性和艺术性价值外,该剧的文学史意义更为显著。《长城之神》创作与设置的时代背景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时期家国零乱,局势动荡,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批短篇白话小说像“问题小说”、写实派小说等纷纷涌现,揭露社会弊病,引起有识之士的疗救。此时期,戏曲也承担着启蒙的责任,即“移风易俗,责在诸君,是所望于今日之新剧家”[11]。熊佛西意识到话剧在民众启发方面的作用,联合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13人于1921年5月在上海创办了民众戏剧社,并宣告“将看戏当成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戏剧在现代生活中“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12]。如何借助话剧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来救助忧患的国家是熊佛西关注的焦点,他在《长城之神》中直接揭露:“国内尚且是乱七八糟,强盗呵,土匪呵,真是层出不绝,就是建筑了这万里长城,亦只能防外患,也不能止内乱”[13]。呼唤民众予奋起反抗,所以其塑造的孟姜女形象具有抗争性,以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这是民国时期戏剧的共性,譬如颇具爱国意识的艺人潘月樵在合适的场景,便在舞台中央“阐发言论”,以富有煽动性的内容与饱满的情感来激发观众的觉醒,一度被冠名“言论老生”,来引发人们对时局的注意[14]。
任何文本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诞生的,蕴涵着孕育它的那个语境的特点。家国零乱的背景下难容下一对幸福的夫妻。戏剧作家、戏剧教育家熊佛西立足于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创作了试图反抗现状的孟姜女。《长城之神》在传统剧目情节和人物形象设置上进行了突破,给予孟姜女“新时代的灵魂”“革命的精神”和无法摆脱的“软弱”,打破了因因相袭的“俗套”;在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前后呼应、浑然一体,留白、设悬念,营造高潮,并安排了趣味性情节,以调节悲剧性的氛围。熊佛西把握住民国时期人们的接受心理,既以具有平民色彩和趣味性的情节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又以孟姜女的反抗性启发民众。无疑,这是用旧材料写出的新剧本、好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