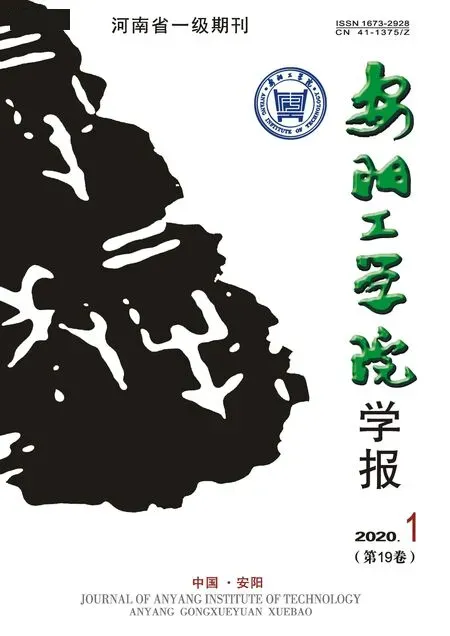论谭献《复堂词话》的尊体观
罗敏先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南宁530006)
谭献是清代常州词派周济之后比较突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常州词派发展的中坚力量。常州词派的重要词论主张重“寄托比兴”,到了谭献这里既表现出一种继承先贤前辈的传统,又体现出自身论词主张的精微特色。谭献在继承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而又富有启发价值的词学观点和词学主张,卓立于清代词学理论大家之列。谭献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之后“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1]58,可见他的词论以及词学思想大概是在人到中年之后形成的。作为工于词学的名家,谭献的词作主要存录在《复堂词》中。谭献汇编的《箧中词》收录清代近千首词,是清代重要的词选本。《复堂词话》是其学生徐珂从谭献的文集、日记、《箧中词》及所评周济《词辨》中将有关词的言论辑录而成的。唐圭璋先生在《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四册中收录该词话,《清代名家词选刊》选录黄曙辉点校的《复堂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亦附载该词话。
一、承绪“风雅”
谭献继承了常州词派的词学主张,极为重视张惠言、周济的重内在深层意蕴的思想。在《复堂词话·周济词》中评周济道:“持论益精。其言曰:‘慎重而后出之,驰骋而变化之,胸襟酝酿,乃有所寄。’又曰:‘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申触类,意感偶生,假类必达,斯入矣。’”[1]91对周济的选词及在其中体现的“寄托”“触类感意”的词学思想极为推崇,而后又说:“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1]91不仅对常州词派作了简单的源探,而且表明他跻身常州词派并推崇其“万感横集”富有“寄托”的词学思想。
近人蒋兆兰在《词说·自序》中说:“逮乎晚晴,词家极盛,大抵原本风雅,谨守止庵……在南则有复堂谭氏,在北则有半塘王氏,其提倡推衍之功,不可没也。”[2]谭献《王氏词综》中曰:“予欲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张惠言,号茗柯)、周介存(周济,字保绪,又字介存)之学。”[1]75表明其是有意继承张、周之主张。不难看出,无论是张之“意内而言外谓之词”,还是周之“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都重在强调词的深刻意蕴和有深度的思想性,从而蕴含着浓厚的儒家诗教色彩,这将词体与中国传统的诗教原则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谭献将儒家的诗教思想直接表述为更具实质性的“风雅”品格。在《复堂词录叙》中写道:“愚谓词不必无颂,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变者欤。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1]57这里的“雅”即为传统诗教之“风雅”。谭献直接借用传统诗歌的创作原则,以风雅内核精神来阐发词学理论。他没有停留在辩驳词为“末技小道”的词学观念上,而是将词体作更深层次的辨析和阐发,把词从表达形式、情感内容等方面推上与诗同样重要的地位。
“雅”本来是儒家传统诗教的概念,是我国古代一直坚持的正统诗学原则,谭献将其运用于词论之中。在《复堂词话》中,“雅”字就多达几十处。“雅”源自于《诗经》,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后世“风雅”并举。风雅精神所具有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表现为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复堂词录叙》言:“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志洁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从中可以发现谭献重视人的内在情感的抒发。他说“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1]58喜怒哀乐可以说涵盖了人的一切情感内容,可见其非常注重内在的情感力量。
“雅”有“正雅”“变雅”之分,谭氏则更为注重“变雅”。“变风”“变雅”乃是政衰道失时期的突出现象,谭氏所谓的“变雅”绝不仅仅是站在封建正统政治的角度去进行刻板地补教风化,而是借以发声,使艺术的表达有了现实的土壤。关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是常州词派的显著特色,谭氏继承了常州词派的优良传统,以诗之视角来看待词,特别重视当中的“变雅”之意,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谈到词的内在力量时说:“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矣。”[3]谭氏合乎时序关乎社会的观点不仅给词体以正名,而且表现了他内乱外患时代的“治乱”意旨。
此外,谭献“以诗评词”的思想凸显他与诗学的深厚联系。他给词穿上诗歌的衣裳,站在诗歌的立场运用诗的思维来评词。如在评唐珏词时道:“汐社诸篇,当以江淹《杂诗》法读之。更上则郭璞《游仙》。”[1]65(《复堂词话·评唐珏词》)这是重在从诗歌体式上去评论。在评柳永词时说:“耆卿正锋,以当杜诗。”[1]62(《复堂词话·评柳永词》)这里以“正锋”评柳永词,其意义可谓独到。在评孙麟趾选《嘉庆来绝妙近词》曰:“孙月坡(孙麟趾,号月坡)选《绝妙近词》三卷,多幽淡怨断之音,可以当中唐人诗矣。”[1]85(《复堂词话·绝妙近词》)是说孙选《绝妙近词》多为“幽淡怨断”,即内心的曲折幽怨之言,这显然是谭献将之比为中唐韩孟诗派一格。
二、衍播“柔厚”
“柔厚”在谭献的词论是里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概念。“柔厚”本不用于词论,而多用于古代传统诗教领域。《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里的“温柔敦厚”指的是诗歌对于人的心灵起到的感化作用,某种程度上对人产生正义和善的影响。
谭献的“柔厚”之论显然是从传统诗教中阐发而来的,反映了他注重诗词在思想内容、表达形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共通性。《复堂词话·绝妙好词笺》曰:“南宋人词,情语不如景语,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于柔厚之旨。”[1]72讲南宋词多使用技巧,凭借才能在艺术技巧上下功夫,重于外在格律、修辞、辞藻等形式方面的“融法使才”。在他看来,“融法使才”固无不可,这是词的一个方面的特色,但更重要的是突破形式技巧追求内在立意基础上的意蕴,以含蓄路径通达到词的意旨,即“柔厚之旨”。谭献评孙麟趾辑词言:“去取矜慎,殆可继踵草窗,冲澹幽微,如读中唐七言诗。”[1]102“幽微”为精微深奥之意,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状态。评叶英华词云:“梦禅居士(叶英华,号梦禅居士),《有小游仙词·法驾导引》一百首,托兴幽微,辞条丰蔚。”[1]98等皆表此意。谭献自己在《明镜词序》曾举例说:“江君某赋士不遇,憔悴婉笃而无由自见于世,于是玲珑其声,有所不敢放;屈曲其旨,有所不敢章……夫声至于不敢放,至于不敢章,是亦《离骚》《小雅》之意,而出之劳人思妇之口乎?吾顾世之为词者,同臻斯境也。”[4]所谓“屈曲其旨”正是他主张的“柔厚”。
谭献的“柔厚”之说中包含巨大的情感内容,既有个人的境遇遭遇,又有家国情怀,更有盛衰世变之叹深蕴其中。个人主体和世道并重形成了他幽婉的深刻内蕴。在评小山词《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时说道:“千古不能有二。所谓柔厚在此。”[1]62晏几道以含蓄之笔写现实与理想之迥异,抒写刻骨铭心的真情与爱,这种浓重而含蓄的个人情感,的确如谭献所说的“柔厚在此”。
谭献生活在清王朝腐朽动乱的时代,这一时期朝政混乱,外敌也频繁侵略,正是处于封建社会将要坍塌的末世时代。他的词学思想和理论主张形成于三十岁至四十岁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正好处于内乱外患严重的同治年间。谭献出生不久便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因此在他的心中郁积着对现实巨变的忧虑和关怀。正是在这种从未有过的历史语境下,他承担起了呼唤正义与善念的忧国职责,以回归传统儒家诗学的道德情感来表示一种救世的博大精神,将新语境之下爆发出的炙热情绪寓寄于“折忠柔厚”的传统精神内核之中。他在《复堂类集·明诗》中说道:“以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5]此言可窥见其心中之意。他在词选集《箧中词》中尤其推崇许宗衡,说其“伤心人别有怀抱,胸襟酝酿,非寻常文士……为近词一大宗。”[6]他推崇许宗衡为“大宗”,虽有过誉之嫌,未必十分准确,但其中的意义可见一斑。在评邓廷桢《双研斋词》曰:“……然而三事大夫,忧生念乱,竟似新亭之泪,可以觇世变也。”[1]81(《复堂词话·邓嶰筠词》)他还将有清一代的词人选为前后十家词,其中有张惠言、蒋鹿谭、钱芳标、纳兰容若、龚定庵、项鸿祚等人,亦显黍离之伤。
谭献继承常州词派的精髓,其词学思想必然与该派先贤有所替递,“柔厚之旨”的主张显然是周济之“寄托”论发展而来的。他在《词辨·跋》中说道:“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仲可比类而观,思过半矣。”[1]60可见他所强调的“柔厚”和周氏“寄托”“比兴”有着类似的价值功能。在选清人词上也是“选言尤雅,以比兴为本。”[1]79(《复堂词话·阅历代诗余》)。“寄托”“比兴”都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以“微言”或其他事物来指向另一面或深层的含义,如香草美人之类。“柔厚”也可视为艺术表现手法,是表现出含蓄蕴藉的方法,延伸出厚重、婉致、沉着等韵味,融入词中形成一种稳妥的特质,升华成整体浑融的风貌。可知周济之“寄托”在于过程,谭献之“柔厚”扩而大之在于风格气象之意。当然,周济的词学理论中也有“浑厚”之说,也涉及词之内容与风格方面的论述,同样重深层意蕴和气象,重在本体艺术的解析。而谭献“柔厚”明显透露出诗学诗教余风之味,多了一份可以观测的历史色彩,其间更细致的含义区别还需另外论述。他们之间具有极大的相通之处。这也正是谭献作为常州词派重要继承者继先贤之风、成推尊词体领袖地位的重要表现。
三、结语
谭献在论词中推尊词体,继承常州词派张、周等人主张的精髓,体现深刻的词学尊体思想。“风雅”和“柔厚”是他的两个重要的词学概念,这既是他从中国传统诗学的内涵角度阐发词体特性进而形成的深刻独特的词学主张和理论思想,又是他探求词体艺术价值的两个重要指标。清人叶恭绰在《广箧中词》(卷二)中云:“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益廓。”[7]此言一语中的。
——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