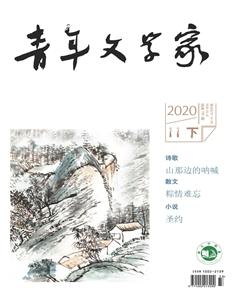浅析电影《百花深处》中的对比手法
摘 要:《百花深处》是短篇电影集《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的最后一部,导演陈凯歌匠心独运,以搬家为线索,以拆迁对传统建筑和传统文化的破坏为主题来表现时代变迁。影片中导演在镜头、人物、音响、叙事空间等方面都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形象生动的为观众展现了年华老去的意蕴。
关键词:《百花深处》;陈凯歌;对比;艺术手法
作者简介:孔令菊(1995-),女,云南昆明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艺与传媒。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3
短片电影集《十分钟年华老去》是制作公司交给导演的命题作文,15位世界大师级的导演都用自己独特的风格表达了对时间的独到理解。陈凯歌导演的《百花深处》选取了一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话题——拆迁,以戏谑又讽刺的口吻讲述了几个搬家工人给疯子“冯先生”搬家的故事。影片只有短短10分钟,导演也用了最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最精炼的镜头语言为观众呈现这个故事,但其中所包含的对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逐渐消亡的无限伤感和无可奈何的情感却永久留在观众心中。这种叙事效果的达成得益于导演在叙事过程中大量的对比手法的运用,通过对比将抽象的年华老去具象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具体体现在影片的镜头运用、人物设置、叙事空间、音响效果等方面。
一、镜头运用的对比
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重要原因就是电影是通过镜头讲故事的,镜头就是电影最基础的表意单位。在《百花深处》中,导演虽然只用了较为常见的镜头语言,但每一个镜头的运用都恰到好处,与电影要表达的内容和主题相辅相成。其中在电影中占据较大篇幅的是几组正反打镜头。
正反打镜头在电影中主要用于人物对话,展现人物关系,在《百花深处》中也不例外,但导演运用得颇为巧妙。第一组正反打镜头出现在影片开场,冯先生突然从车后冒出来,询问耿乐饰演的搬家工头可以搬家吗。在这一组对话中,导演拍搬家工人用的是近景的过肩镜头,镜头模拟的是冯先生的视点,透过镜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车窗里叼着烟、低着头写东西的搬家工人。而拍冯先生时导演则用的是单人的近景镜头,冯先生的情绪直接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这种正反打的拍摄方式有意识的区分了两个人在对话中的轻重关系,冯先生在对话中被凸显了出来,观众也会更加关注冯先生的情感变化,这也表明了在整个故事中冯先生是导演重点表现的对象。在这里还有一个叙事的小细节:在整个对话中搬家工人始终低着头,随意的和冯先生交谈,直到冯先生说:“都叫我冯先生”,搬家工人才抬起头认真地打量了冯先生。这里人物态度前后的转变,也暗含了社会风俗的变迁。因为“冯先生”这样的称呼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不多见。“都叫我冯先生”这种叫文雅的书面表达也与喧闹的搬家现场格格不入。
第二组正反打镜头出现在去百花深处的车里,冯先生好奇地望着窗外,搬家工人们奇怪地望着冯先生。在这一个叙事段落的对话拍摄中,导演用了内反打的方式来展现人物关系。当然一方面这样的拍摄方式是由于叙事空间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单人镜头的正反打表现了人物之间疏远的关系,甚至在电影中搬家工人对于冯先生把上半身探出窗外的行为是有些厌恶的情绪。此外,内反打镜头传达的是两个人物在叙事中处于同等位置,观众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两个人物的情绪冲突。在这里导演也借助了耿乐所饰演的搬家工人之口点出了城市快速变迁的迷思——“如今就这老北京,才在北京迷路呢!”。与这组镜头形成呼应的是搬完家后五人坐在车里的第二次对话,冯先生要赔钱,搬家工人没要的叙事段落。导演在这部分对话则没有用正反打镜头,而是用了固定机位的双人中景镜头,因为经历了灯碎事件之后,几个搬家工人对冯先生有了同情心,5个人在情感上已有了联系,用双人中景镜头更能表达这种情感上微妙的转变。在同样的叙事空间内的两组对话,却用不同的镜头语言,可以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人物前后的行为转变,也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凸显。
第三组有意味的正反打镜头出现在影片的后半段。当搬家工人在冯先生的指引下到达百花深处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是一片拆迁后的荒地。在第一段的对话中,冯先生蹒跚地爬上坡之后,摄影机上摇,高机位、大角度全景俯拍冯先生,冯先生很高兴的向搬家工人介绍这是他家两进的院子,让他们赶紧搬。随后反打,低机位大角度中景仰拍两个搬家工人,工人们认为冯先生这是在耍他们,随后要开车离开。在这一轮的对话中导演通过不同角度的拍摄表现出了人物的地位,冯先生这时是处在乞求对方搬家的地位,在全景俯拍镜头下显得弱小无助。搬家工人处在主动位置,用中景大角度仰拍,突出这些人的傲慢强壮。第二段对话发生在几个搬家工人知道冯先生是疯子,去要工钱的时候。与前一段对话相同的场景安排,但此时导演却将拍摄角度调换,选择高机位全景俯拍搬家工人,低机位大角度仰拍冯先生。导演通过角度的变化,将故事中人物关系的变化用视觉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此时搬家工人处在弱势地位,冯先生处在强势地位,于是才有后面搬家工人假装搬家的剧情出现。在整个搬家过程中,导演也基本用仰拍的角度来拍摄冯先生,俯仰之间也蕴含了导演对冯先生为代表的坚守传统文化的人的敬仰和赞美之情。
二、叙事空间的对比
电影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艺术,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转换是电影叙事的基本条件。好的“电影应该善于把时间性叙事转换成富有视听冲击力的空间性叙事, 即善于在线性叙事的链条中寻找营造空间意象的一切机会,通过强有力的叙事空间的表现,来把故事讲得富于情绪感染。”[1]《百花深处》由于时长限制,电影只有两个叙事空间:繁华的现代高楼和拆迁的百花深处,但导演通过两个叙事空间的对比和虚实结合等手法延展了两个叙事空间的含义。
首先,两个叙事空间在视觉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都市的叙事空间由两个场景组成,第一次出现在电影开场,跟随着搬家工人的移动,摄影机慢慢向后景移动,到门口时摄影机缓缓上摇,映入我们眼前的是一棟要使劲仰头才能看到顶的高楼。此时摄影机呈现的是一个近乎九十度的仰拍,这个视角让观众非常难受,视线有一种压迫感。这就是导演想要通过镜头传达给观众的感受,现代的高楼大厦常常会使我们感到压抑,喘不过气。现代都市的叙事空间第二次出现在路途中,导演从冯先生的视点,用几组运动的大全景让观众看到了现代化的北京都市——高楼林立,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的中西结合的饭店,在环境音效的衬托下,整个城市呈现的是热闹的景象。[2]在这里导演也给了一座高楼一个高机位、左摇的仰拍镜头,这个左摇加仰拍的镜头给了观众强烈的眩晕的感觉,如同冯先生看到陌生的街景时找不着北的眩晕感,这也暗喻在现代都市里人们常常会迷失自己的方向。这一切的繁华都与之后出现的百花深处的破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百花深处破败的呈现,导演选择的是搬家工人的视点,随着放置在驾驶舱内的摄影机,我们看到了一排排正在拆迁的传统建筑。之后是几个大全景,我们看到前景是夷为平地的百花深处,后景是一墙之隔的高楼大厦。让我们对比最为强烈的是影片的最后一幕,几个搬家工人回头看到了夕阳中壮美的大槐树。这个叙事空间导演用了一个固定机位平视的大远景来拍摄,伴随着悠扬的笛声,凄凉、壮观又美好的氛围被营造出来。在这里,导演选择的视点非常巧妙,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我们的经验更接近于搬家工人,我们没有住过胡同,甚至怀疑百花深处是否存在,所以从搬家工人的视点出发去看百花深处美丽的景象,所带来的震撼会更加深入观众的内心。透过两个叙事空间不同的呈现方式,导演想要抒发的情感也更好地传达给观众。
除了繁华的现代都市叙事空间和破败的荒凉的百花深处的叙事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之外,曾经的百花深处和现在的百花深处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导演选择百花深处作为叙事空间也是独有寓意的,因为百花深处在进入电影叙事之前,它就已经具有了文化含义。顾城《题百花深处》中的百花深处、陈升《北京一夜》里的百花深处,这些百花深处先在的美好文化含义已经给了观众一个印象,导演再来重现百花深处,就能让影片的内容和其他文本产生互文的效果,有助于观众更好的理解电影的主题。此外,这种对比的产生也得益于导演精心的引入了动画叙事。通过动画的演绎用视觉的方式呈现了曾经的百花深处:大槐树下,百花纷飞,青砖碧瓦,几许人家。现在的百花深处只剩残檐断壁和突兀的歪倒在路边的树根。之后在一个镜内蒙太奇的运用下,转眼间沧海桑田,只剩一颗大槐树孤零零的矗立在夕阳之中,至此年华老去的主题生动鲜明地呈现在了观众的眼前。如果说那个坑让观众开始怀疑冯先生是不是真的疯子的话,那么百花深处的动画演绎则将谜底揭开,百花深处也许真的存在,可惜已经消失了。在这虚实交错间,悲哀与无奈伴随着凄凉的笛声萦绕在观众心头,冯先生欢快的搬新家的声音更添几分讽刺。
根据观众对空间的知觉方式,电影的叙事空间可分为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视觉空间就是指荧幕上观众直接可见的视觉形象,听觉空间即由故事内声音所直接提示而感知到的空间,它是对观众和故事中的人物视觉所不可见的空间的提示和确定。[3]在影片的高潮部分——搬家工人向工钱屈服,假装搬家的叙事段落中,导演就巧妙地运用视觉空间和声音空间的相互补充关系,延展了影片的叙事空间,在虚实对比之间,完成了主题和情感的表达。从视觉空间上,观众看到的是大槐树下一片荒芜,没有房屋更没有家具,搬家工人们正在进行完美的无实物表演。而从听觉空间上,通过画外音的使用,观众却感受到了鱼缸里的水在晃荡,柜子发出吱呀的声音,灯座落地发出来打碎的声音。这种视觉和听觉的不同步,一方面调节了影片的氛围,为影片增加了笑料,增添了影片的趣味性。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的错位,让观众反思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习俗,但如今都只存在于听说里。我们都无法再亲眼所见了。
三、人物设置的对比
《百花深處》中的人物关系非常简单,仔细算下来全篇也只出现了四组人:搬新家的家庭、4个搬家工人、冯先生、骑自行车闯入的人,在这四组人里导演架构了一对对比关系人物。
电影中显性的人物设置中的对比手法的运用集中体现在了冯先生和几个搬家工人之间,他们一个代表了传统文明,一个代表了现代文明。先看冯先生,作为老北京人,冯先生全身充满了的老北京的韵味儿。就其穿着来说,红色和黄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色,红即为吉祥,黄有黄色文明之意。此外冯先生语言文雅、动作也颇有梨园京剧之色,回家之前的动作充满仪式感,虽然疯了,却还清楚地记得家里物件的摆放位置。这种融化在冯先生血液中的传统文明的象征与现代社会的氛围格格不入,只会被当作疯子的疯言疯语。搬家工人们代表了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生活的中国当代青年人。他们从言语动作上与冯先生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行为、言语粗鲁,但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积极地融入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他们身上也有着现代人的缺点,见钱使舵,只要给钱什么都干,完全被现代物欲社会所影响。同时他们身上也还保留着一些传统文化的因子——汽车上随风飘荡的中国结,在打碎了冯先生不存在的灯座之后对冯先生的歉疚,这些都代表着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在他们身上的融合。这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就集中体现在了搬家的过程中,大衣柜和紫檀的衣橱的对比、金鱼缸和花瓶的位置对比、屋檐下的铃铛。通过对白,观众感受到了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文化习俗的吞噬。积极拥抱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早已不记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俗,只留下简单的中国结。结尾导演还是用了比较中立的态度来看待两个文明,年轻人重新拾起了象征着传统文化的铃铛,开始回望过去的传统。夕阳下,冯先生欢快的搬新家的背影,除了一抹对于传统文化的消逝重来的凄凉之外,也蕴含着其独特的未来希冀。
四、结语
《百花深处》是一部极具隐喻和人文关怀的电影。通过大量对比手法的运用,年华老去、历史变迁的主题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导演用他一贯的忧患意识,和一脉相承的文化忧思展现他对于人和社会历史的永恒关注。影片最后以乐景写哀情,更将历史变迁,文明消逝的悲凉和无奈深深的镌刻在观众心里。昏黄的主色调更为影片增加了几分历史沉重感。文物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平衡至今依旧是社会热门话题,影片通过视听语言的呈现再次警醒观众,在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要回头看看,寻找自己文化的根。
参考文献:
[1]黄德泉.论电影的叙事空间[J].电影艺术,2005(3): 18-24.
[2]阙一都.百花深处藏笑泪——从《百花深处》看陈凯歌矛盾的历史文化情结[J].今传媒,2013(2): 99-100.
[3]樊黎明.浅析音响音乐在影片主题阐述中的运用——以电影短片《百花深处》为例[J].中州大学学报,2011(5): 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