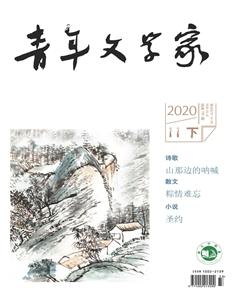被忽视的人:《大地》中老秦的形象意义探究
摘 要:《大地》是具有双重文化经历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代表作之一,老秦作为书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在学术界中未能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在作品中,老秦不仅是一个勤恳朴实、忠诚善良的农民,还是主人公王龙的半身,他不仅是王龙最亲密的朋友,最忠诚的仆人,他还象征着他与土地的联结。作为象征着土地的符号,“忠诚”是老秦的核心,他忠诚于王龙,也忠诚于土地,在这一层面上,老秦的形象具有独特的意义,而对其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作品中的土地情结。
关键词:老秦;《大地》;土地情结;符号
作者简介:何袁祺(1997-),女,汉,湖南株洲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3
一、引言
1931年,美国作家赛珍珠出版她的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凭借讲述中国农民故事,《大地》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在1938年获得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因描寫中国而获此殊荣的西方作家。《大地》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承认,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根据出版商约翰·戴公司的估计,《大地》的众多版本和重印本累计起来超过了二百万册。《大地》畅销的影响是显著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中国人在西方世界里面己经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形象,形成了一系列的‘套话。无论是明恩溥笔下的停滞和缺乏生机活力的中国乡村社会,还是傅满洲系列小说中阴沉、恶贯满盈并最终被绳之以法的傅满洲,所有这些连同美国媒介中奇异、不可理喻的种种中国风俗和中国人的特性,,使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美国成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邪恶“他者”形象[王东. 跨文化视域中的“乡土中国”——赛珍珠《大地》再思考[D].成都:四川大学,2006.,61-62.]。”但《大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固有阴暗印象,它的畅销很明显对于中国的“自白澄清”是有利的。
而这种情况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其中有“异国情调”的影响,有时代背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大地》满足了读者对于“相似性”的要求,即书中体现的土地情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表明,这种执着的爱是以人作为载体、世代承袭的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中国农民这个群体的同感心愿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它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了华夏子孙的深层意识与心理结构之中[2]。”但不仅仅是中国农民,其实全世界人民对于土地的热爱都是相似的。也正是在这份“相似性”的基础上,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切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以往的研究中,王龙、妻子阿兰、王龙的父亲、儿子王虎、孙子王源都有详细的人物分析,且学者在讨论土地情结时也多将目光放在主要人物王龙等人身上,老秦,作为王龙的邻居以及后来的管家,在研究中只是作为一个点缀一笔带过。但笔者认为,仅仅根据老秦在作品中频繁的出现次数,他便不应该被忽视,可以说,老秦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在作品中他才是那个离土地最近的人。
二、作为王龙半身存在的老秦
小说的主人公是王龙,一个农民。故事以他娶了黄家大户中的厨房女佣阿兰为开头,描写了他历经旱灾、洪涝、饥荒、革命、远离家乡南下打工等种种苦难,凭借自己的勤劳苦干与老天爷给的好运气发家致富的故事。故事的表面上,老秦是王龙可以交易白葱籽与猪腿肉的邻居,是值得信任的管家与朋友,是勤恳耕地的农民,但在更深层次上,老秦是王龙的半身,他象征着王龙的良心,他监督王龙,辅助王龙,同时,他还象征着王龙与土地的紧密联结。
老秦第一次出现,是在王龙准备去黄家接自己未来的妻子阿兰的途中,因王龙对大家大户的恐慌出现。当时王龙想着希望有个人陪着自己以缓解害怕情绪,他提到了自己的父亲,叔叔和老秦。在王龙的视角中,邻居老秦是作为与父亲叔叔这样的亲人并列出现的,其重要性已有所暗示。
第二次现身,是在王龙的成亲酒席上,这里有一处对老秦的正面描写:“这人姓秦,是个身材矮小沉静的人,除了万不得已总不愿开口讲话[3]”。这一处描写同阿兰的刻画有着惊人的重合:“除了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话以外,她从不讲话”“她像一个忠诚的、沉默寡言的女仆(27)”。老秦在之后也的确成为了王龙忠诚不二的仆人。阿兰在作品中象征着“地母”,她沉默无言,踏实肯干,默默地让自己的乳汁流进了耕种的土地里。阿兰与老秦的相似似乎暗示着老秦与大地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仅仅是作为农民身份,还是作为其他身份的。当然,在另一层意义上,老秦的沉默与阿兰不同,阿兰的沉默象征着千百年来被压迫着的“中国古老大地上妇女生存的一种普遍样态[4]”。老秦的沉默则是因为他不需要说话,作为王龙的半身,而不是独立的人,他不需要有太多想法。
但老秦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王龙的半身出现。他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自耕农一样,他还有属于自己的地。直到那年旱灾。这次旱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次灾难,老秦彻底脱离了尘世的羁绊,王龙得到了足以东山再起的财宝。在旱灾面前,老秦为了自己的妻儿,抢了王龙家里的豆子。他是所有抢了王龙家粮食的人中唯一一个想道歉的。因为这份愧疚和心里的良善,在王龙准备南下逃荒时老秦给了他自己用来保命的红豆(往南边走这个想法也是受了老秦的启发)。在南下打工糊口这段时日,王龙远离了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没有提及老秦一次,就像老秦同土地一起远离了王龙。而等到王龙携着金银回到家乡,老秦再次出现了。这时候,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仅有土地。王龙提出要买老秦的地,他答应了,并且“很高兴这么做”。在赛珍珠的笔下,农民应当是把自己土地当做生命看待,哪怕是死亡也不能让自己卖地,正如王龙所做。可是在对王龙有救命之恩的情况下,老秦把地卖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留下后代是一件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老秦之后却再未娶妻,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这不奇怪,因为这时候的老秦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了,他“属于”王龙,作为王龙的半身而存在。作者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无妻无儿,没有亲戚和土地,孤零零一人,没有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任何牵挂。在后文这点体现得更为明显,凡是在文中反复出现有一定戏份的角色,无不为自己的私利斗争抢夺。就连处处为王龙着想的阿兰,对于珠宝也有着女人的天性——为了两颗珍珠她第一次反抗了自己的丈夫。只有老秦,自那次旱灾过后,他仿若成为了王龙的影子,不再有自己的欲望和私利,或者说,他王龙的良心,是对大地的渴望,除去对王龙的“忠诚”,他别无所求。
三、作为土地符号的老秦
老秦象征着王龙与土地的联结。在被雇为管家后,老秦被王龙安排管理雇工与土地。“他很愿意干活,慢条斯理地从早干到晚,从不讲话,如果有什么事要说,他的声音也很低,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什么事都没有,这样他就用不着说话。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不停地锄地,早晨或晚上,他把水或人粪尿挑到地里倒进菜畦(142-143)。”王龙不用再操心地里的事,因为那些偷懒的贪吃的雇工老秦全都会一一汇报给王龙,这是一种绝对的信任。因为老秦就是那个最勤劳忠心,最为王龙着想的忠仆和朋友,是王龙的分身,永远不用担心背叛。沉默与忠诚是老秦贯穿全文的最显著的特点,就像土地一样。
正因如此,在王龙受情欲冲击决定娶妓女荷花并为她花费大量钱财的时候,他避开了老秦。老秦作为管家存在,应当是负责好王家的大小事务,包括主人纳妾事宜。可是王龙却对着自己的管家心虚了,因为对荷花的上心意味着对土地的忽视,而为荷花花的钱全都来自于土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老秦代表了土地本身。
当洪水退去,土地重新露出来,王龙心中对荷花的情欲稍褪,重燃对土地的热情,“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呼唤着——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他觉得这声音比他生活中的一切其他声音都响亮(p187)。”当这种声音在王龙的心里回荡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呼唤老秦:“喂,老秦,我的朋友,来呀——把人都叫来。我要到地里去(p188)”。“他把老秦叫来,将绳索交给他,而他自己却拿了一把锄,”“他累了的时候,就躺倒土地上睡一觉。土壤的养分渗透到他的肌肤里,使他的创伤得到愈合(p189)”。老秦与土地的深切联系在此处再一次得到体现。
作为王龙的半身、最忠实的仆从,老秦也把手头的所有事情都干得漂漂亮亮。在即将发生第二次洪灾时,“王龙在它的地里急匆匆地跑来跑去,老秦像影子一样不声不响地跟着他”。而当洪水退去,“王龙便这里走走,那里转转,查看着每一块土地。他和老秦讨论每一块地的土质,商量根据土质怎样变换所种的庄稼。”作为土地符号,王龙甚至直接用老秦指代土地了。最明显的一处是王龙买下黄家大户的院子后,家里人全都搬去了城里,只有王龙因为对土地的眷恋选择继续住在乡村,他这么对儿子解释,“我最好留在老秦住的地方。”他用“老秦住的地方”代指自己乡村的屋子。
事情的变故发生在大儿媳生了个儿子之后,王龙有了第一个自己的孙子,还修了家谱。就在这一时期,后继有人,子孙延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老秦发生了意外。文中是這么描述的,“但是,好像神不愿一味给予恩赐,在恩赐的同事也要给人带来某种痛苦似的(p271)。”王龙午饭也没吃的赶到了老秦的身边,老秦就这么一句话也没说的死了。当年王龙的父亲死时,他一滴眼泪也没掉,“他眼里没有眼泪,在他看来,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除了他已经做的,在没有任何事情可做(p242)。”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老秦死了以后,王龙趴在他的身上失声大哭。王龙为老秦的葬礼大操大办,不仅自己披麻戴孝,还让大儿子也扎了孝带,甚至想把老秦葬在埋葬父亲和阿兰的地方,王龙特地吩咐:“在他死了以后,要把他埋在离老秦最近的地方(p273)”。正如大儿子所说:“对一个仆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可老秦显然不仅仅是仆人,大儿子没有意识到这点。
老秦死后,王龙与土地的联结就这么断了。“王龙已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到地里去了。因为老秦已经去世。再说他对地里的活已感到厌倦(p273)。”于是王龙搬去了城里的房子。但远离土地住在精致的院子里也不使他感到平静和舒适,直到王龙意识到自己快死了,他才回到了乡下的屋子,回到了土地,在此之前,他特意叮嘱大儿子,在自己死后,“要葬在秦的上首,”哪怕是下葬,他要葬在与老秦最近的地方,为了强调,作者让它连续出现了两次。
四、结语
《大地》中的土地情结表现十分明显,在《大地》中,王龙乡村的屋子由他的祖祖辈辈用脚下的土地盖起,土地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钱财,家庭都从土地而来,也正是因为保持了对土地那份情感,王龙才能够在数次大灾难后东山再起。直到文章最后,老秦和王龙等人葬入了同样的土地,完成了轮回。
就赛珍珠的创作意图而言,《大地》的出版是为了向西方展现一个更真实更正面的中国。而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对“中国”主题的创作,作者必须考虑受众接受层面。赛珍珠为了让人了解她眼中真实的中国,人类普遍心理的土地情结就是一个引起共鸣的很好的利用点。
主人公王龙“长期生活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之中,他难免具有封建时代农民性格特征的烙印;但是,作为‘人,他心中又保留着许多生之为人的可贵本性[5]。”而作为王龙的半身与象征着土地的符号,老秦在文中的表现就像影子,他没有缺点,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但他却是最贴近土地的那个人。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存在,老秦作为王龙的半身,象征着主人公与土地的联系,但他更是土地的化身,象征着土地的符号,是主题的进一步强化,也是作品中人物对土地的深沉感情的又一次强调。而作为展现土地情节的重要隐性角色,老秦不应当被忽略。
注释:
[1]王东. 跨文化视域中的“乡土中国” --赛珍珠《大地》再思考[D].成都:四川大学,2006.,61-62.
[2]尚营林. 恋土: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赛珍珠作品主题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2):70-74.
[3]赛珍珠. 大地三部曲[M]. 王逢振,韩邦凯,沈培錩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2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谢玉娥. 大地上“从不开口”的女人——《大地》中的阿兰性格特征简析[A]. 许晓霞,赵珏. 赛珍珠纪念文集(第四辑)[C].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204-210.
[5]朱磊. 赛珍珠及其作品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54.
参考文献:
[1]赛珍珠. 大地三部曲[M]. 王逢振,韩邦凯,沈培錩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2]尚营林. 恋土: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赛珍珠作品主题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2):70-74.
[3]王东. 跨文化视域中的“乡土中国” --赛珍珠《大地》再思考[D].成都:四川大学,2006.
[4]谢玉娥. 大地上“从不开口”的女人——《大地》中的阿兰性格特征简析[A]. 许晓霞,赵珏. 赛珍珠纪念文集(第四辑)[C].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204-210.
[5]赵炎秋.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易丹先生商榷[J].外国文学评论,1995(02):127-131.
[6]朱磊. 赛珍珠及其作品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54.
[7]Shaorn R·Gunt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M].高鸿.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D].福建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