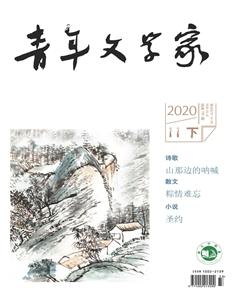中国传统小说模式重塑与其意识形态探究
基金项目:主客体传承关系中的华裔文化重构——以汤亭亭系列小说为中心;项目级别:校级;项目编号:XSYK18038。
摘 要:本文将从小说形式本身出发,对汤亭亭小说《女武士》中出现的各种中国传统小说模式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与作者(移民视角)对它们的重新塑造进行对比分析,探寻美国二代华裔移民内心的深层复杂意识形态投射。
关键词:《女武士》;中国传统小说模式;意识形态投射
作者简介:王帆,讲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1
1、前言
自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小说《女武士》(The Woman Warrior)1976年问世以来,就引起了美国、中国各社会学术领域的关注,美国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女性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时代等研究视角的不断涌现,探索小说所表达的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等含义。与之前侧重理论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从小说形式本身出发,对其中出现的各种中国传统小说模式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与作者(移民视角)对它们的重新塑造进行对比分析,探寻美国二代华裔移民内心的深层复杂意识投设。
2、无名女人与女鬼故事
女鬼故事最早出现在晋朝的《搜神记》,唐宋传奇中多出现在爱情故事里,而在明清小说中成为典型鬼怪形象。此类故事是伴随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加深而出现的,成为男性潜意识里的恐惧形象,其叙述方式的关键辨识特点大多集中在四点上:死亡、男性性侵害、复仇愿望及无理智的残忍行为。从表面上比较小说中的死亡动机和形式,我们很容易得出无名女人与典型女鬼故事十分相似的结论,都源于女性的不贞洁,结局多为投井自杀,然而在具体情节上却大相径庭。
首先,传统女鬼形象与无名女人表现出对于“贞洁”的追求与反抗之间的对立。传统故事中,女性多受节烈观的影响,为维护贞洁、名节,以死亡的形式将受到男性侵害的事实公开化,在道德上惩戒恶人,同时也为男权道德立牌坊。无名女人—即“我”的姑姑的死亡却表达出作者对于节烈观的强烈反抗。姑姑被强奸后怀孕后,强奸者便纠集一帮人,抄了她的家。她对于爱的向往,美的热爱也被歪曲了通奸的证据,于是,“她抱起婴儿,朝井边走去。(汤亭亭)”直至死亡,姑姑也没有说出“情夫”的名字。她的自尽代表了美好、善良的女性情感所遭受的摧残,选择与自己的女儿一同赴死正是她对所处世界残酷性的控诉和对孩子的爱与保护。这死亡没有牌坊作为奖励,只有母亲悄悄的话语,“别告诉任何人你有个姑姑。你爸不想听到她的名字。她从来没有出生过。(汤亭亭)”
其次,传统女鬼故事大多以正反两方的恨意消解、情感圆满作为终局,而姑姑在死后却被进一步抹去了其存在,怨恨无法消散。而男性在集体参与这场压迫和惩罚后,出于潜意识里的对于报复的恐惧,刻意选择了继续打压和遗忘;而姑姑则魂附“我”身,将这份来自女性的对于男性中心的集体共谋文化的恨意继续传递下去。
可以看出,传统故事的意识形态出自男性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与评价,在此之下的女性真实面貌是模糊的,其行为也是傀儡式的。汤亭亭赋予了无名女人内心的无奈与爱美之心,给了她选择赴死的自我意识,在叙述中使其成为人本身。
3、白虎与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我国通俗小说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类型样式,从唐传奇、宋话本一路发展下来,到清、明时期进入高潮阶段,其中著名的作家有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其故事叙述模式特点为:男性侠客的神化;遭遇偶然性改变命运(跌落悬崖等)的机遇及复古的教条主义(争夺古人秘籍等)。
从表面上看,作者在白虎的梦境中也遵循相似的发展套路:替父从军的木兰奇遇深山的老翁老妪,学习武功、兵法,牢记国恨家仇,率领军队上战场复仇的故事。但木兰并不是被简单男性化的强健女性勇士,故事中对于初潮的对话描写坦荡直白:
老妪对我解释道:“你已经成年,可以生儿育女了。”接着她又说,“可是,我们希望这几年你先不要生。”
“那能不能用你教我的抑控之術止住流血呢?”
她说:“不可。”人总不能不拉屎撒尿吧,经血也是同理。随它流吧。(汤亭亭)
而对于战场上的怀孕生子,与传统的被保护的孕期和不能见光的生产过程完全不同,孕中“我穿着改大的盔甲,看上去像一个孔武有力的粗壮大汉”(汤亭亭)。分娩后,“我”将脐带晾在旗杆上,“那段脐带随着旗帜在风中猎猎招展。(汤亭亭)”没有任何被保护的脆弱,也没有不能见血光的羞耻。此外,故事中的“背后刻字”与传统上男性以伤痕为英勇,女性以暴露身体,伤痕为耻的文化心理也完全相反,木兰、岳飞和“我”已融合为一,改写了传统女性气质,将女性本身与强健、无畏、冒险精神结合起来。
然而,木兰故事的重塑从表面上看是令女性振奋的,是英雄的被看见,但这场虚构的女勇士的浪漫华丽复仇故事本身的血腥正是来自于对于自身所处地不被看见的“鬼”身份的传统文化处境意识的悲切呐喊。
4、巫医与鬼故事(试胆)
试胆故事是传统鬼故事中最具有特色,也是常被讲述、改编为电影、电视的类型之一,说的是在闹鬼的荒村、破庙,或废弃建筑中,人主动与鬼进行正面遭遇和较量。《女勇士》中的母亲便是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鬼之间的勇士。
在医学院时,母亲遭遇的是压身鬼,即民间俗称的“鬼压床”。母亲的较量方式与传统鬼故事里人以反抗、挣扎、尖叫、念佛经等畏惧逃离压身控制不同,母亲与鬼叫阵“你赢不了,你这石头蛋”、“我不会让步,不论你怎么折磨我,我都受得了。你以为我怕你,那你可想错了。对我来说,你没什么神秘的……”(汤亭亭)她背诵医学课要学的功课,以自身的力量对抗鬼,果敢勇猛。在美国生活时,到处都是报童鬼、的士鬼、巴士鬼、警察鬼、灭火鬼、查表鬼、剪树鬼、杂货店鬼、送信鬼、垃圾鬼、社会工作鬼、护士鬼、牧师鬼、偷盗鬼、流浪鬼、黑鬼、白鬼、吉普赛鬼……母亲时时与鬼生活、与鬼较量,养大了6个儿女,辛劳老去。
如果说医学院遇鬼的故事还在传统鬼故事的框架内,那么,在后一个故事中,“鬼”的概念得到置换和拓展,具有了超现实的意味。母亲以中国家族文化概念为中心,在意识里将美国变为超现实的鬼世界。通过这个自我创造出的外在“鬼”空间,她使自己处于“人”的意识掌控空间的中心,边缘化“美国主流文化”,在对抗的紧张性中保持个人身份的完整性与在异国生活下去的心理稳定性。而华裔女性所遭遇的与西方主流社会文化的隔绝也通过人鬼殊途的差异性展现出来,母亲的奋斗史正是无数女战士与“鬼”的半生对抗。
5、西宫外、胡笳怨曲与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是古代叙事琴歌,叙唱的是蔡文姬坎坷身世,思乡幽情,别子隐痛,以及回归故国所见所思的情与景。西宫外中久居香港的月兰——母亲的妹妹,去与美国的丈夫和女儿团聚,但丈夫与女儿都已经变成了美国鬼,思念之情犹在,而重逢已是面目全非。月兰变疯,而“我”成了厌恶自己的四不像,讲着柔弱的美语和公鸭嗓的汉语,挣扎在“半人半鬼”的文化拉锯战之间。蔡文姬与她的匈奴孩子之间,故乡的人们、上一代的英兰们、月兰们和第二代移民的我们之间都已变不同,唯有在琴声中可以追思已不复存在的故乡。
胡笳十八拍与之前的故事不同,更多触动的是华裔在代际之间不断改变、隔离之中的共同性,虽然华裔移民历史与蔡文姬在故事模式上多有不同,但在情感上却有相似的皈依。
6、结语
《女勇士》的各个故事中都不同程度、层次的引入了中国传统故事,并以“我”的视角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对其进行了重塑和改写,在意识形态上烙上了对于传统、外来文化的伤痕记忆与英雄主义想象,与其抗衡并最终以一曲凄切动人的歌声与其共生共存下去。
参考文献:
[1]汤亭亭,《女勇士》[M].新星出版社,2018年4月。
[2]何丽野:关于武侠小说的叙事模式[J].社会科学报 2001(1):1-2。
[3]胡颖峰:叙事的琴歌与琴歌的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9(3):37-43。
[4]刘木丹:《女勇士》的英雄观探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19(8):33-37。
[5]孫东苗:刻板形象的解构与英雄形象的重构[J].中共郑州市党委学报2006(4):130-32。
[6]王铮:母亲的“鬼故事”[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7):48-49。
[7]卫景宜:改写中国故事:文化想象空间[J].国外文学2003(2):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