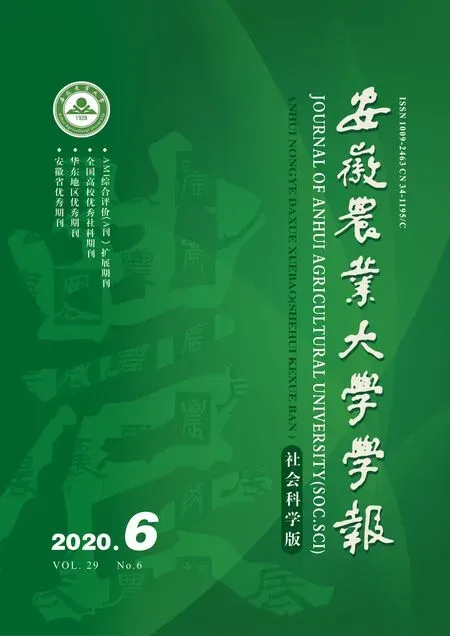公共管理哲学视域下的主体性消融及其路径*
王 芳,许 良,王 平
(1.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2.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3.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无论是行政管理、社会管理,还是执政党内部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公共管理的本质都可以概括为激发良情善意以及鼓励被管理者走向自我管理。所谓自我管理,就是通过有效管理或曰善治,将被管理者融入管理目标,实现被管理者的主体性消融。只有实现主体性消融,才能让被管理者达到“忘我”和“无我”状态,才能拥有基于精神信仰的形而上力量,才能为了实现管理目标,自觉对抗管理过程中的各种阻碍和诱惑。可以说,实现主体性的科学消融,是公共管理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老子》中“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论述,《庄子·逍遥游》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论述,以及《论语·子罕》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论述,都对主体性消融的涵义及其意义展开了思考。及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论述,通过阐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在更高层面揭示了主体性消融的重要价值及其科学路径。
一、就本体论而言,要实现主体性的科学消融,其逻辑起点是做到“我”的主体澄明
从逻辑上讲,“无我”状态的实现或曰主体性的科学消融,是一个从主体性强化走向主体性融解的过程,即把主体澄明的“我”,持续融解到作为精神信仰的管理目标中。在这里,精神信仰好比化学中的溶剂,“我”好比溶质。因此,要实现主体性的科学消融,逻辑起点只能是“我”的主体澄明或曰主体性强化。对此,可作三点分析:
首先,只有做到“我”的主体澄明,主体性消融才存在消融的对象。所谓消融的对象,指若缺失“我”的澄明,那么,究竟把什么东西消融在精神信仰这杯溶剂中,就会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更可怕的是,若缺失“我”的澄明,一个人稀里糊涂成为“无我”状态,就不是这里说的崇高精神追求,而是奴性文化摧残的牺牲品。如在古希腊,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这一称号,不仅描写了奴隶悲惨的生活境遇,更揭示了奴隶主对奴隶“人之为人”这一基本事实的否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封建社会摧残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也进行了揭露批评。他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阴影下,许多中国人还没有体验到“人之为人”的骄傲和主体性澄明的力量,就被迫异化为“物”和客体性存在。正是为了反对传统奴性文化,革命家秋瑾表达了“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决心(《满江红·小住京华》),诗人舒婷也写出了“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的诗句。
其次,只有做到“我”的主体澄明,主体性消融才有消融的必要性。所谓消融的必要性,指“我”在澄明后,人就成为一种“自觉”而非物我混沌的存在。此时,人们为了追求无限的人生意义,必须要把自己消融在精神信仰中。
人一旦成为“自觉”的存在,就要反思“我”的存在价值,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对这三个终极问题以及其他哲学问题的反思,尤其是对“我到哪里去”的反思,让人直面无限和有限的矛盾,让人努力追寻人生的无限性。如果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那么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问题。一切哲学都要从实践和思辨的角度,努力思考人作为“存在”,如何突破“虚无”,即如何立足有限而达成无限的终极难题。之所以如此,在于人作为有限性存在,在感受到“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后,就会希望超越有限性或曰“人终有一死”的生命悲剧,探求温暖的、明亮的、无限性的意义世界。无论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提出的“死生亦大矣”的千年之思,还是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发出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叹,无不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要追求人生无限,不能指望人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吃仙丹让肉体永恒,更不能学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逃避事实。唯一合理、积极的做法是,把自己消融在无限的精神信仰中,犹如一滴水融入大海,获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人生永恒。也就是说,物质生命无论如何延长,都是有限的;只有正视物质生命的衰老,同时展开赛跑,在物质生命到达终点之前,先一步找到精神信仰,生命才能升华。诚如雷锋所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5]。
再次,只有做到“我”的主体澄明,主体性消融才有消融的可能性。所谓消融的可能性,指“我”在澄明后,具有抗拒外界诱惑的主体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起到“定海神针”作用,保护“我”不受干扰,在精神信仰中持续消融自己。
把“我”持续消融到精神信仰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诱惑犹如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不断搔首弄姿,企图让人们“忘记初心”。马未都对诱惑的强大力量给予了形象描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一个幽灵无处不在,它大小不定,形态不一;它一会儿实一会儿虚,偶尔还会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蛊惑招摇,让施者快授者乐,且都乐在其中矣。……这个幽灵叫‘诱惑’。”[6]然而,人之所以了不起,在于一旦实现了“我”的澄明,就拥有了一种“凡事在我”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力量让人们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时,好比吃了《西游记》中灵吉菩萨的“定风丹”,在很大程度上能起到“护法”作用,帮助人们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7]。
从内容上说,这种主体力量包括“至诚”和“至坚”两个方面。就“至诚”来说,主体性澄明告诉我们,我们明明是有能动性、顶天立地的主体,不能自欺欺人,不能把自己降低为“一动不能动”的客体。《大学》中的“诚意”“正心”也可这样解释。一方面,“诚意”指“人不自欺”,既然人的类本质即主体性,每个人都要回到主体性,同时,只有回到主体性,人才能“遇到最好的自己”,才能做到“凡事在我”。另一方面,所谓“正心”,是指“人不欺人”,不仅自己具有主体性,他人亦有主体性。既然自己不愿意被视为客体,也要把心摆正,不把别人降低为客体[8]。就“至坚”来说,一旦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主体”,我们就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就能拥有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豪迈,并激荡我们在改造客体世界的征程中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这里“改变世界”的力量,就是一种主体相比客体的能动力量和实践力量。对“至诚至坚”主体力量的高度重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华。无论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孟子·滕文公下》),还是王阳明讲的“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10],无一不强调个体发挥主体性力量的重要价值和无限可能。
二、就认识论而言,要实现主体性的科学消融,其关键举措是破除“我”的逆向固化
在“我”的澄明实现后,为了追求人生无限,人们希望能把自己消融到精神信仰中,以实现“无我”状态。然而,人们陡然发现,在这杯精神信仰的溶剂旁边,还有一杯名曰“物质诱惑”的溶剂。后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断破坏人们对“无我”状态的追求。
所谓“成事不足”,指相比精神信仰这杯溶剂,能够持续消融“我”,给人带来无限的意义,让人实现“无我”状态,物质诱惑这杯溶液,只能间断性地消融“我”,给人带来有限的意义,最终让人遭遇“我”的逆向固化。对此,可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沉溺在物质诱惑中,也能让“我”得到一时的消融和忘我,也能得到一时的意义供给。第二,问题在于,物质诱惑这杯溶剂只能给人们提供有限性的意义。再“美好”的物质诱惑,都会产生“审美疲劳”,都有功能失效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很快从消融中醒来。无论是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的诗句,还是哲学家“人在吃饱饭前后,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的格言,都说明了这个道理。第三,及至醒来,“我”迅速从消融状态被打回原形,好比一杯盐水重新凝结为盐块。这就是主体性的逆向固化。第四,主体性的逆向固化,让我们感受到既有意义世界的破产,让人们比原初状态更为痛苦。也就是说,人们满心期待的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遭逢的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第五,虽然明知沉溺于物质诱惑,是一种“直把他乡当故乡”(李煜《浪淘沙》)的自欺欺人,最终会遭遇主体性逆向固化的绝望。可是,为了破解眼前的走投无路,许多人只能通过饮鸩止渴走上不归路,只能在“他乡”一条路走到黑,只能把自己消融在更大剂量的物质诱惑中。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等到审美疲劳再次降临,“我”将遭遇更可怕的逆向固化。哲学家黑格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恶的无限性”[11]。古往今来,多少人就生活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在物质诱惑的溶剂中反复消融又反复固化,成为“叔本华钟摆理论”的鲜活注脚。所谓“人在各种欲望不得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不停地在这两端之间摆动”[12]。
所谓“败事有余”,指物质诱惑这杯溶剂,虽然不具备持续消融功能,但相比精神信仰这杯溶剂,它具有更强烈的融“化”功能。一旦物质诱惑释放出迷人芬芳,尽管拥有前述主体性的“定海神针”力量,很多人仍然如中了魔障一般,飞蛾扑火般地扑向诱惑。关于人们对诱惑的“无能为力”,《西游记》中有一段猪八戒见到美色的精彩描述:“那呆子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流涎,心头撞鹿,一时间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也。”[13]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力度加大,一批腐败案件被曝光,从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腐败官员之所以走向堕落,重要原因就是无法抗拒诱惑。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道:有的党员干部“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弦,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4]16。
物质诱惑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会让人们承担沉重的机会成本。一方面,因为玩物丧志,人们再也无力、无心将自己消融在精神信仰中。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道德经·第十二章》),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一些人还会弃“明”投“暗”,好不容易有了精神信仰,却无法抵制物质诱惑的勾引,所谓“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冯梦龙《醒世恒言》)),“扑通”一声又跳到物质诱惑的溶剂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以及“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华严经》)。
显然,物质诱惑是主体性走向科学消融的致命障碍。要破除物质诱惑,除了前述不断澄明人的主体性,让人的主体力量起到“定海神针”和“护法”作用,还要让人们拥有“审丑”思维,以看到诱惑背后的丑陋本质,使其不攻自破。只有同时具备“定海神针”和“火眼金睛”的双重保护,人们才能在充满诱惑的客体世界中不为所动、不忘初心。
关于“审丑”思维,可以追溯到庄子“道在蝼蚁”“道在稊稗”“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的论述。在庄子看来,只有让人们拥有“审丑”思维,才能发现各种诱惑背后的暗黑丑陋,才能摆脱诱惑的勾引。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烟草制品包装正面和背面,都须印有占据烟盒面积50%以上的健康警示,健康警示必须大、明确、清晰、醒目,不得使用如“淡味”“柔和”等误导语言,并标明烟草制品成分、释放物信息、所引起的各种疾病。一些国家从上述规定出发,在香烟包装盒上印上不健全的人体部位、腐烂的肢体或是因受父母吸烟而病倒的儿童照片,以此实现控烟目标,就是对“审丑”思维的运用。
从哲学上说,要拥有“审丑”思维,就是让人们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当下看长远、透过部分看整体”的辩证眼光[15]。第一,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指诱惑犹如《聊斋》里的画皮,只要揭开现象,揭开貌美如花的画皮,就会露出丑陋、狰狞的枯骨。第二,所谓“透过当下看长远”,指诱惑犹如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和白玫瑰。玫瑰再美,时间长了,也会产生审美疲劳。红玫瑰会变成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则变成衣襟上的饭米粒。第三,所谓“透过部分看整体”,指诱惑犹如著名儿童绘本《爸爸,公主也会放屁吗》里的白雪公主和美人鱼,公主们固然美不胜收,但美丽光环的背后,亦有无法藏匿的不完美。
显然,“审丑”思维是人们抵抗诱惑和破除主体性逆向固化的重要哲学智慧和思维工具。在“审丑”思维的帮助下,人们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诱惑摆布,进而能对诱惑实现“祛魅”,能打破内心的执迷不悟,能做到有“诱”无“惑”,以及练就 “金刚不坏之身”。诚如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言:“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16]此时,即便有一大杯物质诱惑泼了过来,我们依然能做到“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三、就价值论而言,要实现主体性的科学消融,其根本要求是实现“我”的科学消融
“我将无我”或曰主体性消融的科学路径,是把自己消融到作为管理目标的精神信仰中,以在形而上的意义世界中追求人生无限。所谓“双手握无限,刹那是永恒” (布莱克《天真的预言》)。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7]人们只有拥有了形而上的精神信仰,才能实现“道”“器”融合,才能在“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18]的过程中,把无限性的意义赋予形而下的物质世界。诚如诗人冰心在《繁星·春水》中所说:“平凡的池水,临照了夕阳,便成金海!”然而,精神信仰这杯溶剂,又从来都是花开两朵的。第一种是唯心主义的精神信仰,第二种是唯物主义的精神信仰。因此,为了追求无限的人生意义,人们不仅要拥有“审丑”思维,睁开“审丑”眼睛,努力破除物质诱惑的干扰;还要睁开“审美”眼睛,努力选择一种真正科学的消融方向,即唯物主义的精神信仰。
所谓唯心主义的精神信仰,指把“我”消融在各种超验的“理念”“绝对精神”和“神”中。唯心主义的精神信仰包括一些宗教信仰,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它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歪曲反映,是颠倒的世界观。列宁深刻指出:“唯心主义哲学是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19]因此,如果选择了乞灵于神的唯心主义信仰,人生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甚至会因为信念动摇与无路可走的绝望,又滑向沉溺物质享受的泥沼。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也背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改投唯心主义信仰,要么希望于神灵护佑,要么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有的还花大钱去咨询请教所谓大师、算命先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道:“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14]17
所谓唯物主义的精神信仰,指把“我”消融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信仰中,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相比选择唯心主义信仰,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唯物主义信仰坚持无神论的世界观,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从而告别虚无缥缈、虚妄无稽的人生轨迹。诚如《国际歌》歌词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唯物主义信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世界观,能够拥有更为开阔的人生格局。因为“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20],否则,一旦离开了人民的需求,任何利己主义包括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早在一百多年前,青年马克思就表达了同样的价值观:“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1]同样早在1912年,青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也在震撼之余无限悲悯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从而“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2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4]78从这句话出发,还可以发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信仰,能同时让我们收获基于“爱”的人格力量和基于“逻辑”的真理力量。所谓基于“爱”的人格力量,指只有把“我”消融到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中,我们才能从“物质之我”变成“精神之我”,从“有限之我”变成“无限之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23],“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24]318,“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24]317。所谓基于“逻辑”的真理力量,指只有我们做到献身人民,才能真正推动历史发展,才能真正触及历史规律的逻辑之美和真理之美。因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25],“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26]。相反,任何藐视、无视甚至仇视人民群众的社会运动,都会因为与历史规律和真理之美相违背,最终遭遇螳臂当车的失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