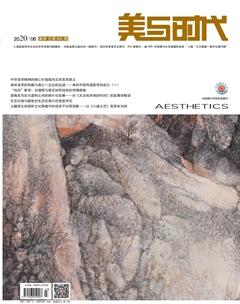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中的叙事伦理问题研究
摘 要:《沉重的肉身》以小品文集的形式展示了作者对于个体自由伦理的关切及叙事伦理的思考。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中的叙事伦理问题研究从叙事伦理的视域出发,对该书中的可能生活及个体生命感觉的强调进行论述,阐释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可能生活是一种多变性的存在,而个体生命感觉的强调是一种积极性的建构。而叙事伦理的一系列因素对于叙述者以及接受者都会产生影响。
关键词:叙事伦理;偶然;可能生活;生命感觉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是一部小品文集,其中蕴含许多作者对于叙事伦理的真知灼见。国内研究者对书中所表现的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的区别或人义论与神义论的自由伦理的阐释较为关注,对书中的身体表情较为感兴趣。但该书探讨个体自由伦理的背后更多指向的是叙事伦理,强调更多的是叙事所带来的伦理意义,因而深刻发掘作品中的“叙事伦理”问题并以此为核心展开对其包含的多层涵义进行再探索、再分析有一定的必要性。
针对该书所呈现出的叙事伦理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个体自由伦理问题的展示及重要性的强调,大部分研究者已注意到刘小枫所关注的“叙事伦理”,而关于叙事伦理内部的具体包含因子涉及较少。本文将着力去挖掘隐藏在叙事伦理背后的一系列较为重要的因素,并揭示其重要意义。
一、叙事与伦理的交合
“叙事伦理”这一术语最开始是在查里克·纽顿所著的《叙事伦理》被提出,他在文中指出,“讲述本身就蕴含了伦理本质,因此所有叙事都是伦理性的”[1]。叙事是“叙述事情(叙+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2]。倫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3]9,而作为反映生活世界的文学作品,“只要关涉人的生存,就必然或隐或现地呈现某种伦理秩序”[3]9。刘小枫《沉重的肉身》贯穿叙事与伦理的交合,试图用叙事伦理去看待与解析具体文本。“没有叙事,生活伦理是晦暗的,生命的气息也是灰蒙蒙的。”[4]13“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4]6在引子中,童年时期的作者与小伙伴们在黑夜中听大孩子讲故事,大孩子所讲的他人已叙述过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4]5。时间在叙事过程中被不知不觉地填满,而黑暗的空间看起来也不再可怖,这种由于叙事而带来的时间与空间意识上的改变是极具魅力和无法言说的存在。叙事本身作为一种文学活动,具有客观意义上的冷静、无动于衷的意味,“叙事讲的要么好像是自己亲历的事——‘我如何如何,要么好像是自己亲眼目睹的事——‘他、‘她或‘你如何如何”[4]12-13,但叙事的内部同样存在一定的伦理思想意识。叙述者通过叙述这一话语行为,与听者进行心理上潜在的伦理意识沟通。听者此时处于思想静止的状态,等待着叙述者的叙述,而选择讲什么样的故事,选择权最终是在叙述者那里。叙述者掌握了叙事主导权,且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当时的思想情绪等现实状况对叙事内容进行选择,因此这选择的结果是对于听者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潜置。“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解释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4]10叙事是一种生存伦理,叙事与伦理的交合,使得它们各自的活动范围合二为一,在叙事中传递伦理,在伦理中把握叙事。叙事伦理追求的不是向听者灌输规范化的伦理,而是在对故事内容叙述的同时,使听者心理产生安慰感与共鸣。叙事伦理撕裂了规范伦理,它不在乎规范伦理所传达出的既定道德规范,相反,它背离规范伦理,不阉割读者的自由意志,而是通过叙事尝试与读者进行沟通,在此过程中了解读者的所思所感。叙事伦理使读者思想得以解放,不再受到规范的束缚,而是在听之中追寻自我的存在意义。叙事与伦理的相互交合,碰撞出具有生命意义的更新万象。叙事的书写场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处于动态流动中,读者在此书写场中不必感到幻灭,因为在此场域中更多的是自由因子,它不和读者的原在思想意识拉拉扯扯,而是作为一个叙述者与倾听者出现,要做的只是包容与抱慰,让读者的心灵在听完叙事后变得较为明朗。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对几位作家作品的复叙事,让读者了解叙事伦理的真实存在以及所带来的思想革新意义。叙事伦理从事的是创新意义上的话语言说活动,所显示的是非封闭性的、非隐匿的开放叙事空间,在这里读者可以尽情地自娱自乐,而不用受到外界的约束。
总之,叙事与伦理并不是相互排斥与对立的两个概念,它们可以互相交合形成新的事物。叙事伦理立足于叙事本身,通过叙述他人讲过的故事来使听者得到心灵上的抱慰或陪伴,这是叙事伦理最具有利他性的目的与功用,它相悖于规范伦理,为的是在讲故事中追寻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
二、叙事伦理中的可能生活
赵汀阳先生曾就“可能生活”的概念提出:“可能生活是现实世界所允许的生活,但不等于现实生活。可能生活是理想性的,它可以在现实生活之外被理解。”[5]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存在着距离,并不是每一个可能生活都能成为现实生活,而在叙事中,可能生活的存在,可以让人在现实生活之外去实现另一种可能生活,得到自身的心理满足。“可能”本身作为一种概率,具有随机性,选择权在于个体。“叙事不仅讲述曾经有过的生活,也讲述想象的生活。生活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带来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4]9想象生活即可能生活,代表一种多变性,它不固定于此时的生活,而是力求摆脱现存的既定秩序,进入一种纯粹代表个人价值的生活。个体生活在伦理社会,或多或少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而可能生活的存在,让人暂时脱离规范伦理,进入到某种不自知的虚拟生活世界中,在这生活中人的感受不再局限于社会冠以道德规范的某种温和境遇,而是超越其上,显现个体的偶然亲在。叙事伦理中的可能生活代表叙述者与读者的主动展望,通过此种展望而展开对生命别样意义的追寻或遥想另一种唾手不可得的生活景象。对于叙述者来说,他人已叙述过的故事作为一种可能生活,是不曾在叙述者真实生活中出现的,可能生活构筑的是个体在无法重拾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叙述者借讲述他人已讲过的故事使自身的现实生活与第一叙述者的故事生活发生联结,在此联结中感受可能生活的存在意义,消解个体现实生活中的单一与贫乏感受,增加自我的精神想象。在叙述过程中对于他人故事的阐述而带上的伦理见解就会与自身原有的伦理认知产生对话。在对话过程中,也许彼此的伦理认知合二为一,也有可能产生碰撞,自我伦理认知与第一叙述者的伦理见解产生分歧,那么这种颇具戏剧性意味的分歧就会使得第二叙述人的言说在何种程度上迎合或者背离原叙述人的叙述。如果第二叙述者的伦理观念与原有叙述者的言说是相互契合的状态,则呈现出完整故事复述,在复述过程中可以感知到第二叙述者的言说对于原叙述者的高度尊重和迎合,故事的重合度高,意味着第二叙述者对于原叙述的认可并自觉接受其伦理影响。假若是背离情况,第二叙述者的叙述在复述故事的过程中,受到自身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故事所体现的伦理观念与自身不相匹配,那么第二叙述者就会对文本产生一些抵触抗衡动作,他要另行组织语言来进行言说,并把自身的伦理观念自然地融入其变化叙述中,在对原有叙述者的背离上加入自身的伦理理解与感受。这是另一种可能生活的显现,代表意义更为复杂,它不只是原有叙述者的伦理思想,还掺杂第二叙述人的伦理见解。两者碰撞所形成的可能生活更为生动有趣,下一秒故事的原有内容会因为第二叙述者的心理而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可能生活的意义,即不可确定的多变性。第二叙述者所讲的他人故事会对接受者产生不平衡影响。对于听者而言,听故事的过程不仅是感知的过程,还是自我对于世界认知重新构建的过程。因为叙述者所讲的他人故事是自我真实生活中未出现过的,带有陌生感,而正是这种陌生感引领接受者更为深入地去感受故事情境以及领悟故事真谛。陌生所带来的刺激与新鲜感迫使听者对这种可能生活呈现开放性的体验,把自身代入他人生活,感受他人生活过的世界。而在虚拟生命体验中,接受者会无意识地在自身头脑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想象生活。但这种想象生活须是他人故事的一种投影,始终带有他人生活的印记。叙事伦理中的可能生活,给叙述者与接受者不一样的伦理认知。叙事伦理是在讲故事中追寻生命的意义,而可能生活的存在就是给叙述者与接受者提供更为多样的生命意义的选择。叙事伦理带来的不只是“仅限于”,更多是“基于”。与其无止境地固定拥缠某一个对象,还不如基于自身的欠然而后体验无穷多元的生活可能性。
总之,叙事伦理中的可能生活对于叙述者与接受者而言是多变性的存在。他们在叙述与倾听的过程中主动展望原本疏离自身生活的多变可能性,开放自身的多种精神想象,通过与现实的短暂剥离,获取可能生活带来的快感,在虚拟的可能生活中体感自为性的个体存在,并且在多样生命体验过程中根据自我的尺度去涵育新的伦理认知。
三、叙事伦理对个体生命感觉的强调
“叙事伦理学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而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只是在道德的特殊状况中出现的。叙事伦理学总是出于在某一个人身上遭遇的普遍伦理的例外情形,不可能编织出具有规范性的伦理理则。”[4]7叙事伦理不同于规范伦理,侧重每一独立个体的生命感觉与价值偏好,它并不走普遍伦理观念的道路,而力求展现个体自身的独特性。“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4]7个体的生命感觉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包含对于世界的看法还有对于自身的认知。正是这种无法终结的生命感觉才使伦理世界的意义变得无法穷尽。个体是整体中的分子,而无数独特个体才形成整体。规范伦理从整体出发,要求“我们应该做什么”,这种“应该”忽略了个体的自我独特性,采用统一标准来建立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必定是削弱个体自身的特殊性,试图用一种大众化的思想去套路个体。个体生命感觉的呈现,摆脱伦理规范的日常束缚所带来的倦然与虚无。在规范伦理引导下,个体失却自身的“想”,而趋向社会的“应该”,这使得自我跌入一种患得患失的虚无幻影中。“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它讲的都是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个体感觉的深刻痕印的语言描述这些经历,一个人经历过这种语言事件以后,伦理感觉就会完全不同了。”[4]11個体的生命感觉是跳动、鲜活的,它触摸到自我心灵的真实想法,真正从切身感受出发。它并不抹煞规范的既定秩序,只是要求在既定的道路旁拥有一条供行人行走的小径,在这条小径上个体可对自我的生命感觉与价值偏好进行询问,而不用依附于大众的伦理规范。自我只有对自身的个体存在进行体察,真正感触自身的所思所感,在漂浮境地中才能明确自己到底置身何处,而不是茫然地随波逐流。“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4]7叙事伦理返回到个体本身,不再强调规范的引导借鉴意义,而是撕破规范的面纱,争取把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叙说出来。人是独立的个体,无需将自我压抑在规范之下,而是让其呼吸自由的空气,叙述自我的生命故事。叙事者在叙述他人故事中不必按照规范伦理进行阐述,而是从自我的生命感觉想要侧重表达什么意蕴的角度进行叙述。这种叙述并非完全脱离原文本,也没有完全按照原文本的叙事进程行事,而是在其叙事基础上进行自我生命感觉的潜入,再以全新的面貌讲述给听者。而听者为叙事中的“这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动了感情,叙事语言就会在不经意间改变人的生命感觉,使其真实生活发生变化。“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4]7-8强调叙事伦理中的个体生命感觉,是对规范伦理遮蔽大众视线进行的去蔽。规范伦理遮蔽个体的价值认知,而叙事伦理就是要使之重新流动起来,并从个体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感觉来把握生命的应然。个体有其生命感觉的复杂性,规范伦理只是给出比较普遍的劝导。叙事伦理使得个体的生命感觉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解放,并通过叙事表达出来,最终使个体的生命境地变得澄明,这是叙事伦理所要做的最微不足道又最具有革新意义的探究。
总之,叙事伦理中对个体生命感觉的强调,使得伦理世界的意义无法穷尽,个体带着自己的生命感觉找到的是不一样的伦理意义。自我生命感觉的独特性在规范伦理中被部分掩盖,而叙事伦理所要做的就是使之暴露在叙事中,让人的个体生命感觉得到重视。世界正是由于每一个体的特殊性以及生命感觉的独特性而变得精彩纷呈。
四、结语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向读者复叙述了几位作家作品的伦理故事,并试图通过故事的重新解读来让读者体会叙事伦理的重要性。叙事伦理并不等同于规范伦理,它不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只是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给予个体抱慰与陪伴。叙事伦理中的可能生活对于叙述者与读者而言是多变性的存在,对个体生命感觉的强调则让伦理世界的意义无法穷尽。总之,叙事伦理强调感受,这种感受是最为根本的生命体验,是栖居在大地上的重要认知。
参考文献:
[1]董晓烨,张冉冉.叙事伦理探究: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J].文教资料,2016(24):5-6.
[2]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
[3]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16.
作者简介:廖燕,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