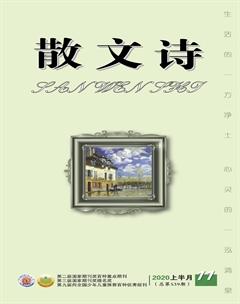当我走过这片熟悉的稻田
南城小圣
当我走过这片熟悉的稻田
当我走过这片熟悉的稻田,一眼望过去,叶子都如开水煮过了一般。这时候我们知道,秋天,已经熟透了。
看着父亲在用镰刀收割稻谷,母亲弯着腰在埂间,捡拾一个个沾着泥土的稻穗。父母认真拍掉稻穗上的泥,就像迎接玩耍归来的孩子,伸手就抱。
那些落下泥土的句子,镶在一首首诗歌里。秋风吟唱,撞击黑瞳,落叶的风景,没有斧正回忆里分枝的细节。大地已经张怀,收容时间,往事。爱和忧愁顺着秋水从眼眶流到心田。
有人,在泛舟;
有人,在桑田。
像是众多的昨日,走在返青的路上。
帕勇和拜媛
风在山兰酒的杯中打坐,我在一场婚宴上看到帕勇和拜媛。围绕在一对新人的身边,我像看木棉花盛开热烈的火苗,从山底窜至山巅,再到流水的岸边,进入一座山的腹地,好似春天沿着视线燃烧,几百年如一季,不远不近,炙手可热。
拜媛,是个幸福快乐的黎家人,身体里有奔流溪泉的女人。她溢满爱的眼睛,波光粼粼,身着嵌银描金的黎锦,正陈述着岁月的纹理。
原来,春天的词语不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发现的,而是此刻让我感同身受一个深爱着她的帕勇,拥有一座山的花语。
这幸福的甜,无止境地从山顶泻下来,胜过人间的蜜语甜言。一些幸福的人被山兰酒撞怀,年老的歌手唱起多情的黎歌,年轻的舞者跳起了一支支欢快的竹竿舞,你的歌,我的歌,开在一片日珥燃烧的山坡下,翻开了黎族浪漫爱情的续集。
我走出村口,看木棉树和凤凰木合成爱的混交林,每一片靠近衔来的光影,都长成幸福的模样。
正如草木上阳光的歌声,翻耕了纸上的时光,让所有的句子学会了呼吸。
夜宿卡法岭下抱班村*
夕阳西下,这一次,我悄无声息地路过,树都背过身去,只偶尔用力抖动叶子。
那些年轻过的绿、幸福过的黄,像一个美丽的秋收预言,收获满满的爱。
山下,一对相互搀扶的老人在路上披着霞光走来,而我像一个归客,从他们身边路过。随风声加快迈出步子,而这正被一场凌空赶来的雨,梳理起长长的发丝,停在耳边的一些细节学会了倾听。
雨点越来越密集,有的流在大地上,有的忘了走成曲线,有的发出季节的鼻息,舔舐着这个部族的单音。
华灯初上。我在老友家的南瓜藤下纳凉,清沏一壶五指山红茶,品茗一段卡法嶺传说。看村落坚挺着椰树般的身影站立在山间,慢慢闭上眼睛,想象这漫山的彩蝶从城市飞往一个个村庄,好似千万盏路灯打着灯笼回到了家。不必去想,这城乡互动的羊肠小道,不用走也能回到家里。
注*:卡法岭,抱班村,均为海南岛腹地的山岭和村寨。
织锦的拜奥雅*
我前面的这位织锦老人都七十多岁了,但精神矍铄,像黄昏里的一截儿活着的木桩。
年纪给她冠以拜奥雅的尊称,织布机于她腰间盘了六十载的漆面,却任它流尽了血色。
小桥,弯眉,紧赶慢赶,点缀在流水的衣襟上。雨水点播过黑白相间的大力神图纹,把青丝逐一还原,拜奥雅好似顶着蓬松的乌发,掬一缕织布机上熟睡的乡愁,嗓子一扬,一首首童谣便飘出了黎寨。
黎寨,在溪的上游流淌着故事。
我在拜奥雅的额纹里,读出山、读出水、读出日子漫过脚踝的辛苦。那个常以手背遮羞的少女,早已解下抱襟的腰篓,为她和她家族织出护身的黎锦。
谁看不出呢?
盘扣布鞋和黑筒裙,从旧日的巷口走过来时,风里带着刺绣的美和疼。
其实,我看到的整个织锦过程,安静得没一丁点风声。像一些流年,坐在果枝间随着季节熟透,而那些安静的流水,撩开水面,在织布机的色调里,只剩下拜奥雅鬓角的白发。
这刺眼的芒,生生地系住了开阖的篱门,也深深地系住了黎家的根。
注*:拜奥雅,系黎族方言,指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