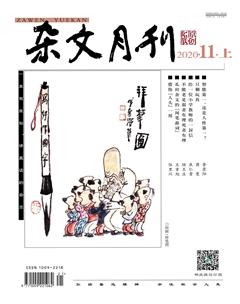说说韩愈的“马说”
宋志坚
韩愈的《杂说四》常被人称为“马说”。开篇就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谓“开门见马”,这句话的逻辑,却是违背常理的。伯乐原是春秋时期的相马师,以善识良马即“千里马”著名,后人便将杰出人才比作“千里马”,将能够发现“千里马”的人比作“伯乐”。按常理说,世上得先有“千里马”,方才有善于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只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使得“千里马”不成其为“千里马”,只能“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可见“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乃是正话反说,表达了韩愈对“伯乐不常有”的强烈不满。
韩愈正话反说,有其切肤之痛。据有关学者考证,这篇短文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这个时间跨度有点大,这个背景却很重要。在此期间,已经进士及第的韩愈,曾三次参加吏部宏词科考,三次落榜。也曾三次上书负有用人荐人之责的宰相,第一次上宰相书后十九天,就复上宰相书,叫《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十天后又复上宰相书,叫《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上书相隔时间很近,口气也颇为凌厉。韩愈甚至把自己比成是“溺于水而爇于火者”,大声疾呼宰相能援手相救。如此,如果宰相不援手相救,则是置人于水火而不顾了。连周公都搬了出来,说是以周公的圣人之才,叔父之亲,以周公辅成王时的天下之治,尚且依然迫切求贤见贤,以至于“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发”,宰相您虽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握发”,难道连“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也做不到,只能“默默而已”吗?韩愈如此上书言事自荐,自有他的底气,那时候才学能与韩愈比肩的确实也不会太多。但这三封上宰相书均如石沉大海,他没有收到来自宰相府的任何信息。
在这个背景下去解读“马说”,就不难理解,韩愈为什么大声疾呼“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了。
中国的科举制始于隋唐,這是底层士子上升的一条通道,却并非都能使“天下英才”各尽其用。韩愈也曾参加科举考试,他先后考了四次,方才进士及第。但进士及第也未必就能使“千里马”跳槽而出,于是又参加吏部的宏词科考,也是先后考了四次。还有比韩愈更惨的,满腹经纶却始终未过科举之关,明代怪才徐文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此,“伯乐”依然有其生存空间。韩愈说“伯乐不常有”,因为有荐贤之权位的权贵,或是缺乏识贤之眼光,或是缺乏荐贤之观念,或是缺乏容贤之胸怀,何况还有“唯佞是荐”的,在他们眼中,就“天下无马”或“野无遗贤”了。这使得有真才实学的“千里马”困于山谷,或一直处于“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的尴尬境遇。
韩愈将自己比作“溺于水而爇于火者”并非危言耸听。以此自比,包括形而上与形面下两个层面。形而上的是精神的层面。韩愈饱读诗书,他要为国为民效力以实现自我价值,需要有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华的岗位,不能年复一年地荒废年华。形而下的是物质层面。韩愈出身很苦,未成年时父亲、兄长先后去世,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十八岁那年只身前往长安投奔族兄,族兄也不幸死于非命。在那样的境遇下读书求学,不顾“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参见《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极需有一份稳定的俸禄。故他写“马说”时的情感相当复杂。有无奈,有希冀,有埋怨,有不平。古时不少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士子恐怕都有类似的境遇与心情。
当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这种焦虑感,韩愈也有,这才会接连给宰相写信。但韩愈不能载质出疆去谋求官职,这是韩愈之时与孔子之时的区别。韩愈之时,天下一统,人才处于“卖方市场”,他们别无选择。韩愈心里很清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外就是去当隐士:“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但他既不愿“去父母之邦矣”,也不想埋没了自己。“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参见《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其理直气壮的底气也在于此。
“马说”能够引起诸多士子共鸣而绵绵不断地流传,原也事出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