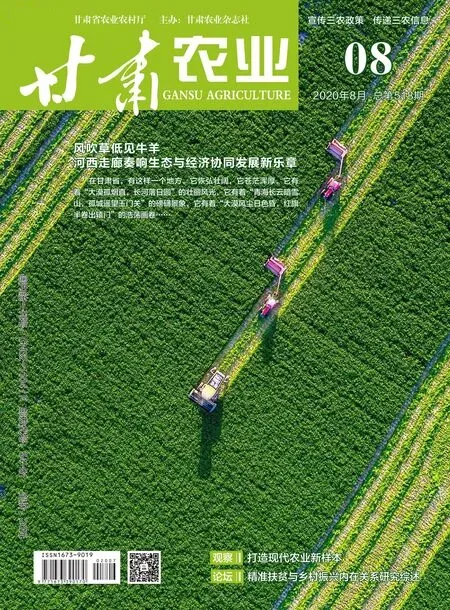我国国情适宜实施“农药扶农”政策
李含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我国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但是,又是世界上农业的“小国”。讲大国是指我国的农产品占全世界的26%以上,因此必然是农业大国。讲农业小国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农业基本生产模式是以小农户为主,我国农村目前有2.3亿农户,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天下。这种生产方式是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过高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大农业战略,用“农药扶农”的政策,将农药使用方式调整成计划经济的方式,把农药生产和使用纳入政府“扶农”的轨道。
一、我国是世界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
(一)我国农药产量
农药生产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4t,到2001年增加到69.64万t,成为世界第二的农药生产大国。据我国产业信息网报道,我国从2006 年起,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农药生产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化学农药原药产量为377.8万t,从2017至2018年,我国的化学农药原药产量为一直维持在370万t至380万t左右。我国也是世界上比较大的农药出口国家,根据我国农药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06-2016年,全世界农药市场销售额从325.1亿美元增长到499.9亿美元,增长54%。预测到2020年,全世界农药销售额将达到600亿美元左右。2015年,我国农药产值总销售额达到1 063.34亿元,约折合为156亿美元,约占全世界农药总量的25%,我国是世界农药生产大国。[1]
(二)我国农药进出口量
2017年,我国农药进出口量为150.84万t,其中,出口量为146.76万t,进口量为4.08万t;农药进出口总额达到71.71亿美元,其中,我国农药出口金额达到67.60亿美元。由此可见,2017年我国农药出口量占农药进出口总量的97.3%,农药出口额占农药进出口总额的94.3%,贸易顺差63.5亿美元,[2]我国农药进出口长期以出口为主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三)我国农药实际用量
农药出口能力。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主要农作物的害虫有20多种,但农药使用品种却有1 000多种,每年农药生产用量约380万t,出口量约为140~150万t,国内实际用量,即自己生产加上进口,约为240万t左右,国内用量约占生产量的60%~65%。按照240万t计算,我国有20.26亿亩耕地,平均每亩耕地的农药使用量约为12kg,考虑到目前有大量耕地撂荒,部分使用耕地的实际农药用量应该在15kg左右。这些农药分摊到14亿人身上,人均约为1.2kg左右。
(四)我国农药的分解结构
我国不仅是世界农药生产大国,又是农药使用量大国,我国是世界农药使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测算和对比,目前,我国平均耕地的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从农药的分解结构来看,在我国使用的农药中,有70%进入土壤、空气和水域中,有30%直接作用于目标生物体。我国原农业部在2012年公布过一项数据,我国制定了322种农药在10大类农产品和食品中的2 293个残留限量,较之2012年之前有大幅度增加[3]。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中,我国农产品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农药残留,将越来越难以进入国际市场。
(五)农药使用的国际公约
在国际上有许多农药使用的国际约定,比如《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巴塞尔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等。这些明文要求严格管控剧毒高毒农药的使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自己研发后生产的农药90%以上是低毒农药,发达国家不仅对蔬菜和水果有农药残留的限制标准,而且对粮食和油料也有明确的限制标准。西方国家的农产品大多数都有生产方面的“身份证”号码,违规使用农药几乎无处遁形,自然也就没人敢滥用。日本的《肯定制度列表》规定的农药限量标准甚至达到62 410个。也就是说,一根大葱要出口日本,必须进行200多项农残检测。由此可见,农产品出口的标准限制有多严格。
二、我国农药残留程度与政策措施评估
(一)农产品农药残留程度
农药使用量是影响农产品农药残留的关键指标,农药使用量与农产品农药残留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药残留是农业生产中农药大量使用的必然结果。农药残留是施用农药后的必然现象。随着农药的大量及不合理使用,我国蔬菜、果品和食品中农药残留问题日益显露。医学界的研究证明,在以往的致癌因素中,农药因素占到约60%的比重,这是因为,90%以上的农药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的各个环节的,只有10%是通过大气和饮用水的渠道[4]。农药品种、使用次数与使用量是影响农药残留的主要因素。
(二)农产品农药残留的国际比较
近年来,由于国家严格执行农药控制政策,加大了控制力度,使得部分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比重有一定的下降,目前,我国农药残留水平已经与欧盟接近。根据原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蔬菜水果农残合格率是96.3%,畜禽产品是99.7%,水产品是95%。欧盟食品安全委员会2017年5月蔬菜水果农残检测结果是97.3%,我国是97%[5]。在农药残留的结构中,甲胺磷、对硫磷等禁用农药基本没有检出;氧乐果、克百威等限用农药的检出和超标的次数也大大降低;检出值也逐年降低,虽然仍有部分蔬菜有农药残留检出,但普遍检出值并不高,基本都低于限量值。
(三)农药利用率差异
根据原农业部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农药利用率也在提高,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农药利用率在50%~60%,比我国高11至20个百分点[6]。从2015-2017年,由于受到国家政策措施的严格实施和控制,我国农药使用量已连续三年负增长,提前三年实现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当前我国农药利用率提高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生态效益。据测算,农药利用率提高2.2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农药用量3万t(实物量),减少生产投入约12亿元。在减少农药用量的同时,提升了作物品质。[7]
(四)政府政策和措施的低效
为了控制农药使用量,增加出口农产品的比重,近年来,我国原农业部实施了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基本政策要求是“一减一提”政策,将农药使用量减下来,把农药利用率提上去。据有关方面的抽样调查和测量,2017年,我国农药利用率达到38.8%,比2015年提高了2.2个百分点;粮食、蔬菜、果树、茶叶等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27.2%,比2015年提高4.1个百分点;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37.8%,比2015年提高5.1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尽管我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近几年的成效也十分难得。另外,我国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完善了相关的制度和规定,这是基本保障条件。到2015年底,我国所有的省、88%的地市、75%的县市和97%的乡镇,已经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落实监管服务人员11.7万人,支持建设农产品质检体系建设项目1 710个,对质检机构负责人及主管局长实行轮训,全国农检机构达到3 332个,落实检测人员3.5万人。在执法体系方面,99%的农业县开展了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落实在岗执法人员2.8万人[8]。与此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责任逐步强化,我国还建立了107个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试点,这批创建试点单位涵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五)生物农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生物农药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为了减少传统农药的使用数量,我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一直坚持发展生物农药,到2016年底,我国已经有近100家研究机构在开展生物农药的研发,生物农药类别也比较齐全。我国已登记生物农药有效成分102个、产品3 500多个,分别占农药登记的16%和10%,同时每年仍以4%左右的速度递增,其中,苏云金杆菌的研发能力和推广利用居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人才、技术和成本的原因,我国的生物农药产量仍然比较低,近年来也只有年产30万t的能力,约占农药产量的8%。[9]关键是成本比较高,所以使用范围非常有限。
三、我国农药残留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一)农药残留高的责任在谁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过高的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甚至是谴责,大体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观点:一是农民的良心有问题,大量使用农药;二是政府不作为,不下决心解决问题;三是相关政府监督部门不作为,工作不认真;四是残留过高是影响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这里的关键是第一条,农民的问题。把农药残留的主要责任归于农民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按照2018年我国全部使用农药的市场价格1 200亿来看,使用这么多的农药,农民基本上是非自愿性的,难道农民自己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吗?事实上是农民不得不为之,不打农药不行,打少也不行。
(二)小农生产方式是根本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农民使用大量的农药呢?是生产方式,是制度和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生产量的大国,但是又是一个农业生产方式的“小国”,到目前为止,大量农村基本生产单位仍然是“一家一户”。根据原农业部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测量,截至2016年底,全国实有耕地面积20.26亿亩、园地2.15亿亩、林地37.95亿亩、牧草地32.9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除去国有农场和集体耕地之外,由农户承包的耕地面积实测为15.2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5%,由2.3亿农户来具体进行承包,平均每个农户的耕地面积为6.6亩,约合为0.44hm2。在承包耕地中,目前已经有4.7亿亩耕地被进行了流转,占比约35.1%。这样折算下来,我国农户实际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应该在9~10亩之间,不到1hm2[10]。
(三)家庭农场发展才起步
国内外农业经营的发展历史证明,家庭农场是农村小农户过渡到适度规模经营最有效的路径。根据统计,截至2018年6月份,我国家庭农场数量已超过87.7万户,家庭农场的平均使用耕地面积小的几十亩、大的几百亩,超过100hm2的极其少见,与发达国家不能比。从西方发达国家中家庭农场的发挥模式来看,一般分为大、中、小型家庭农场。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本都属于大型家庭农场,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属于中型家庭农场,日本则属于小型家庭农场。在美国占农场总数的25%的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产品总量的85%。在德国大型家庭农场的经营土地规模在100hm2以上,全国有2.93万个,占德国农业企业总数的8.29%;德国的中型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在30~100hm2,全国有10.4万个,占总数的29.44%;德国的小型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一般在2~30hm2,全国有21.85万个,占总数的61.94%。从占有土地或者耕地的数量来看,家庭农场一般都比较高。美国人均占有耕地0.53hm2,也就是接近8亩。美国有约1.6亿hm2耕地,同时有约200多个万个家庭农场,平均拥有80hm2耕地,即1 200亩。在西欧国家中,法国平均为28hm2,德国为17hm2,荷兰为1hm2,意大利为8hm2,英国为63hm2。
(四)中西方国家农药使用模式的差异
之所以比较中西方国家之间农村经营单位的耕地经营面积,这只是分析农药使用和残留的基础制度因素。我国农户给农作物使用农药的模式是固定的“一家一户”,而大多数农作物病虫害是会自然流动或者流传的,东家打药,而西家不打药,本来农民打一次农药的量可以有效30d,结果只能保证一周,怎么办?接着打,这样就形成了“小农户+循环打”的恶性循环模式。反观发达国家,农业经营的主要环节全面实现社会化、市场化、科技化和专业化。一个农业农药经营公司可以为几十万亩农田同时打药,而且多数是运用飞机进行操作。另外,还有生物工程、计算机技术和农村各种协会等在起重要的辅助作用。这样一来,农药的含量肯定就低得多,农药的有效期就比较长,农药的使用效率就比较高。
四、农药扶农政策的设计和运行
(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
我国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从长远战略的角度看,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农药残留过高的症结,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基本思路上进行调整:一是必须彻底打破“一家一户”的制度架构,单个经营单位必须以大面积耕地或者适度耕地规模为基本标准,这就必须大力促进土地流转和经营大户、家庭农场等;二是农药使用模式必须走公司化、专业化和科技化的道路,只有专业农药使用和防治公司,才能够真正提高农药的使用效率。许多调查发现,我国不仅仅是农药使用量高的问题,还有使用手段十分落后的问题;三是政府应该在扶持农业发展方面进行政策创新,扶持农业发展不能只保护耕地和帮助农业生产,还要考虑农药使用方式的改革;四是保证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在加强农药和农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上下功夫,还要在解决小农经济上想办法。
(二)模式选择和可行性评估
根据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国情,在选择新的农药使用模式上,一定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不仅仅要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具体做法,而且要学习、借鉴和转化他们的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下面提出四种可行性比较大的模式:
1.家庭农场封闭式使用模式。大型家庭农场,比如经营耕地数百亩或者上千亩、草山上几千亩、草场几千亩的,要建立生产经营的封闭模式,使生产单位成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农产品生产和病虫害防治体系,在这样的生产单位,农药使用可以做到全面积集中使用。政府对这些生产单位实施农药购买补贴,标准另行研究和确定。
2.公司化农药使用模式。在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城镇和农村资本投资创办农业科技病虫害防治专业公司,将病虫害防治环节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环节,由专业公司进行专业管理,对农药进行专业技术的使用。从政策意义上将此类公司与农业科技公司同等对待,可以完全享受有关科技扶持政策,购置农药的补贴标准需要进行研究。
3.温室农药购买补贴模式。在我国的各个农村地区,目前已经建设了大量温室农业,其中,温室农业33.4万hm2(约500万亩)、塑料大棚67万hm2(1 000万亩),合计为1 500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0.75%,面积为世界第一。由于温室和塑料大棚不宜进行集中施药,所以,可以选择经营者自己使用的模式,但是,必须按照规定集中全部用药。政府给购置农药的进行政策补贴,标准另行研究和确定。
4.露天作业集中使用模式。我国大面积农业生产是露天作业,这是农药使用方式改革的重点。对于这部分农田的农药使用方式改革,基本原则是统一指挥和集中使用,既可以是政府统一组织进行,也可以是专业公司集中统一进行。政府模式基本上可以参照我国过去多年使用的林业飞机播种的方式。由此,在广大农村发展专业农业病虫害防治公司,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我国政府应该实施“农药扶农”政策
以上分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逻辑推导,但是,又是合情合理的推导,是为了高效解决问题。归纳笔者的以上分析,实际上对政府这方面的宏观决策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决策建议:一是解决我国农产品农药含量过高的问题,必须创新宏观政策,在“一家一户”的基础上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二是创新扶农政策体系仍然有很大空间,在客观上需要将农药使用方式的改革纳入政府扶农政策体系,与扶贫政策和农村科技政策同等对待;三是扶持农村发展经营公司等新型主体,也要充分考虑农药经营公司和农业病虫害防治公司的发展。
当然,实施“农药扶农”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是中央财政的投入需要增加,按照目前我国农药使用量和市场价格的估算,2018年,我国农药总产值在180美元左右,也就是约1 200亿人民币。如此类推,今后每年中央财政就农药补贴和农药买断,需要支付数百亿元。但是,必须考虑到,如果在未来若干年中,随着生物农药、农药使用方式改革、加强农药使用管理、农产品优良品种的推广、有机农业生产方式的普及以及农药使用效率的提高,全国农药使用量也会大幅度下降,这就会自然减少中央财政的支付压力。
(四)农药扶农政策的界定和可行性
另外,按照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思路,将农药扶农作为一项农业和农村的主要政策,也是完全可行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到2021年,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将基本消除,但是,相对贫困人口依然长期存在,再考虑到返贫因素和情况,也可以将“农药扶农”政策,纳入扶贫的认识领域,也就是针对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扶持政策。所以,不管的扶贫政策,还是扶农政策,农药都应该列入视野。
同时,建议国家农业农村部考虑,将农药生产、销售、使用和管理,纳入公共产品的渠道,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将农药列为政府统购的农业重要的生产资料,并且按照公共产品的模式来使用和管理,甚至比农业生产机械的政策性销售更加迫切和重要。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不用掏钱就可以使用农药,又对农作物有利,农民肯定支持,只要按照政府规定的统一时间操作即可。当然,考虑到不同区域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露天作业和温室大棚以及不同的养殖区,要根据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操作非常方便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