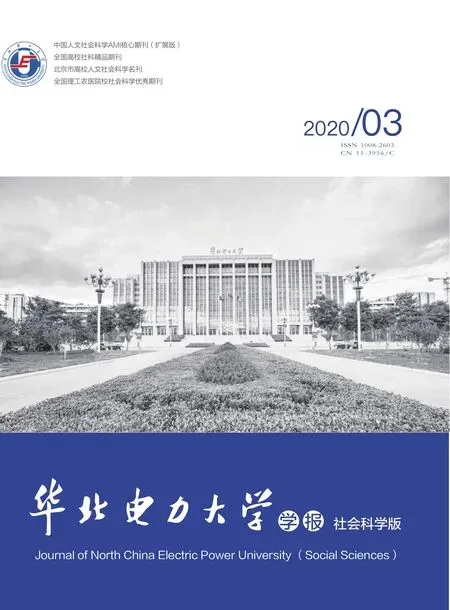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中的空间建构
左金梅,周倩倩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多丽丝·莱辛(1919—)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一名思考者—种族矛盾、两性关系、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她都尝试去探索。独特的流散经历使她有别于英国本土作家,因而对空间认同和文化形态有深刻的体验。她长于借助空间的转换、空间意识的表达以及空间叙事的建构探索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目前国内外关于莱辛及其作品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大都关注《金色笔记》《野草在歌唱》等名作,对于《幸存者回忆录》[1]这部小说的研究不多,其中国外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写作技巧[2]、天启[2]和乌托邦[2]这几个角度,国内研究则集中关注成长主题[2]、复兴意识[2]、伦理研究[2]和苏菲主义[2]这些方面,也有少量学术论文从空间理论视角[2]进行过解读,但对这部作品中具体的空间建构研究鲜有人涉足。
近年来,空间批评研究逐渐升温,“空间转向”意味着文学疆域的再度拓展,也对文学作品的再解读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在空间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文学与文化中的空间被视为一个连贯性、指涉性的象征景观和隐喻系统,人们由此开始更加重视空间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2]96《幸存者回忆录》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灾难过后,城市沦陷,一个中年妇女独自居住在公寓中,旁观着女孩艾米莉在墙两侧的生存状态。正如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空间”是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生存与写作中一以贯之的重要问题,是建构其写作体验的核心力量。[3]62由于这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极具空间感,小说中主人公的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想象交叉出现,碎片化的故事情节常常使读者感到迷茫,因此对作品中的空间建构进行解读能够帮助读者理清故事脉络,掌握空间元素在故事情节中的推动及表征作用。关于空间建构,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曾构建了地志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这一三维模型,被称作“最有价值的理论模型”。[4]12
一、空间对立—权力与性别的差异性表征
福柯认为空间的历史也是权力的历史,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到住所的小策略,从教室这样制度化的建筑到医院的设计”[5]152权力的状态“总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并且是不稳定的。[6]112社会活动都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发生,阶级、性别、文化等因素决定了人们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幸存者回忆录中》,莱辛刻画了主体与边缘、内与外、现实与异质空间多组对立形式,空间不再单纯的作为故事发生的场域,对立的空间成为权力、性别的差异性表征。
(一) 生存空间:空间的等级化
福柯用空间来诠释权力的运作,将权力的空间化视为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7]事实上,不同的空间会形成封闭而复杂的等级系统,空间之间存在操纵、抵抗等冲突,空间内蕴含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对立的空间表征了人物的社会等级关系与人物的命运,权力的运作机制可在对立的空间之中得到体现。在《幸存者回忆录》中,莱辛主要描写了主体与边缘空间、公寓内与公寓外空间、墙外异质空间与墙内现实空间的对立。小说中对“我”居住的公寓是这样描述的:“我住在底层,贴着地面。在这里的感觉与那些高层住家不能同日而语;在他们那里,鸟儿在窗与窗之间沿着无形的固定路线飞来飞去,飞翔的鸟群中投来好奇和思索的目光,道路交通和尘世远在下面。在高处,窗户通风要好得多,前门通向公用电梯,然后往下,往下,然后就听到了交通的喧嚣,闻到了化学制品、植物......以及大街的味道。[1]3这段文字从视觉和嗅觉方面将富人居住环境的优雅与穷人居住环境的简陋进行对比,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建构,居住环境的不同表明居住人的阶级与身份大相径庭,高低不同的生存空间展示了权力的等级化,暗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边缘身份。实体空间中资源分配不平衡,社会为人类群体贴上不同标签,塑造了从高到低各个阶层或高贵或卑微的身份。空间分布上的阶级属性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而且使位于衰落空间的弱势阶层更加缺乏话语权。[8]131
(二) 性别空间:沉默的失语者
小说中的“我”整日呆在破旧公寓内观察外面人行道上的一切,昏暗破旧的公寓是“我”终日生活的场所,“我”凝视他们,却不融入他们,表明“我”内心缺乏存在感。“内”与“外”的对立则象征着“我”与男性主流社会群体的隔离。除此之外,小说中的艾米莉多次来到公寓外想要加入人行道上的男子群体,却因肥胖的体形被拒,她回到公寓内迅速进行节食,表明她非常在意男性的眼光,暗示了男性主导审美的社会规则。而当她成为群落首领杰拉尔德的女友之后,境况却截然相反了。“她身处的场景如同一个交易会,成百上千的自我在彼此碰撞、竞争,互相供养。她是艾米莉,杰拉尔德的女朋友—人们这样提及她,这么说到她。”[1]158人们提到艾米莉时总是先想到她是男性领袖杰拉尔德的女友,而非她自己的名字,同时艾米莉也不具有话语权,是一名失语者,一切都要依从恋人杰拉尔德。这表明女性个体在社会中处于他者的地位,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庸被接受,暗示了男权社会中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以及大众对女性身份的否定与忽视。
文中占篇幅最多的就是墙外空间与墙内空间之间的对比。墙外空间即某天突然出现的非现实的异质空间,其中“个人空间”展演了艾米莉儿时的不幸遭遇。“个人空间”是指艾米莉儿时的家,“家”本应是温暖、爱与责任的代名词,而文中对艾米莉“个人空间”中的家这样描述:“幽闭恐惧症,一种心智与热望的窒息。”[1]39可见,这个家没有给她带来温暖,反而是痛苦的回忆。“我”穿过墙壁看到的是艾米莉呼唤母亲的场景,她渴望得到母亲的拥抱,而母亲却不由自主地摆脱了她的胳膊,并不在意她的呼唤声,同时还厌恶自己两手抱着的身体。同一个房间内还有一个小婴儿,他始终能够得到母亲的关爱,因为他是艾米莉的弟弟,是男孩,于是作为女孩,“她被宣告有罪”。[1]62艾米莉只得默默在一边旁观一切,变成沉默的失语者,无人在意她的呼唤和愿望。不只是艾米莉,个人场景中的母亲也是男权社会规训的产物,“她的婚姻和子女正是她先前自己想要并视之为目标的—是社会为她选择好的”。[1]65她听从丈夫的一切,她完成社会为她做好的分工,尽管她内心苦闷,她那丈夫也只是冷眼相待。封闭的“个人空间”表征了人物的共性或群体的集体性格,“我”进入墙背后的世界,看到父权制主流意识下女性的压抑及焦虑,轻视女性的教养方式体现出集体无意识的恶性循环,这正是末世的人性灾难。反观墙内的现实空间,即“我”所居住的“简陋而舒适”的公寓,“这房间太好了”,她认定这是她的避难所,这是呵护她的四壁,这是她的窝。[1]14艾米莉对这样一个破败简陋的房间表露出欣喜愉悦的心情是匪夷所思的,表明在她的心目中,这个房间是属于她的自由空间,在这里她有名字,有身份,也有说话的权力,只有在这里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
二、空间变动—女性自我主体的构建
佐伦曾提出作品中事件和运动会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在共时与历时层面有不同体现,前者指任一叙述点上或运动或静止的客体在文本中的相互联系,后者指故事情节的运动具有确定的方向和性质。[9]318在《幸存者回忆录》中,人物的运动状态与空间变动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深意,空间的转换表征了女性人物意识觉醒的轨迹,而空间变动的方向不同则绘出人物相反的命运之轴,展现出女性构建独立自我的艰难历程。
(一) 空间运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说中人、事物的动静状态与人物的空间转换展演了女性自我成长的轨迹。首先,参照的叙事点不同,人物的动静状态便不同。“我终日在公寓内观察,以公寓内的事物为参照,“我”是运动的,表明“我”在自己的自由空间内可以随处走动,没有顾虑。但以整个公寓为参照物,“我”几乎不离开公寓,“我”又是静止的,此时的“我”拒绝与他人进行交流,旁观一切,身体被困在公寓里,与男性主流文化产生隔离。参照的叙事点不同,人物空间运动状态也相异,而这种运动状态恰恰界定了“我”心中的自由与隔阂。
小说的主要事件都发生在人行道上,人行道具有交通职能,也是见证小说中女性人物成长和蜕变的活动场所,可以看作是运动的空间,艾米莉完成一次次从公寓到人行道之间的空间转换实则对应着她自我意识觉醒的三个阶段。起初,艾米莉疯狂地要加入人行道上的男子群体,“她务必是以一个姑娘的身份,准确地说是以和姑娘同等的身份去这么做的,可他们并不接受这样的挑战。”[1]33这个阶段的艾米莉迫切想要得到男性的认可,以姑娘的身份初探男性群体,尝试融入,但以失败告终。第二个阶段,人行道上的艾米莉被男性嘲笑体形肥胖,回到公寓禁食减肥,只是为了得到英雄们的欣赏。而后她作为杰拉尔德的女友出现在人行道上,“她想要的仅仅是做这个公社首领的女人。”这个阶段,艾米莉欣然接受社会赋予她的“第二性”角色,依附男性生存,深受男性社会主导价值的影响,衣着和言行举止都要符合相应的规范,被社会规则的绳索牢牢套住。第三个阶段,艾米莉经历了孩子帮一次次袭击,依然被别人请求着、劝说着去付出,但她的内心已经有一种致命的疲惫了,“外面的人行道上连个人影儿都没有”[1]202暗示着艾米莉离开人行道,不再想依附男性,内心的女性意识觉醒。艾米莉在人行道与公寓之间的空间运动对应着的她在这三个阶段的成长变化,展演了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
(二) 空间转换:相反的命运之轴
故事情节中的各点可被看作历时关系轴上的“出发点”、“目的地”、“中途站点”或“岔路口”等。[9]319切入到小说当中,艾米莉和她的好友琼都疯狂地迷恋群落领袖杰拉尔德,但两人的故事发展却是一条相反的轴。群落领袖杰拉尔德被莱辛描述成救世英雄的形象,是正义、力量和仁慈的化身。起初,二人都沉迷于追爱不能自拔,经历一次次人行道集会后,两人作出不同选择,琼跟随一个女人的帮派离开此地,“那个女人群体”自命不凡,她们大声批评男性权威,她们形成了谴责的合唱,对其首领的描述是“带有某种男性气质”,表明琼的自我是不完整的,尽管她努力脱离男性寻找真正独立的自我,最终仍然需要依附他人生存。而艾米莉则对自我产生清醒的认识,她不再因为不牢靠地被大王爱着而患得患失,而是扮演着顾问和信息来源的显眼角色。[2]55对艾米莉和琼来说,这座城市既是二人的出发点,也是二人的中途站点,没人知道琼离开后去了哪里,因此这个城市更是二人命运的岔路口。佐伦强调情节发展的方向是一系列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阶级出身的琼不懂标准语言,童年生活艰辛,遭受压迫,潜意识中认同女性作为第二性存在这一现实,空间的变动也改变不了她必须依附他人生存的事实。与之相反,艾米莉则不再作为男性的“他者”被建构,而是逐步探索,逐渐觉醒,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我救赎。福柯指出,拯救自身需把注意力集中于自身,不去诉诸其他任何事物,不需要什么救世主。[10]273因此,若想在困境中找到完整的自我,最好的方法是改变自身。小说中“我”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次次探寻个人空间,依靠个人力量对童年的创伤进行修复,对家庭、爱情中的男女关系深入思考,逐渐成为一名独立的女性,找寻到完整的自我。
三、文本的空间化—流散写作与空间感的再现
文本的空间化建构需要读者带着整体性思维去探讨,空间逻辑是依靠空间方位分布组织段落和情节的,而这些并不是指向外界事物,而是内指、反射,形成互相照应的关系。莱辛的文本呈现有其独特的空间逻辑,而这种逻辑与她的流散经历相关,最终形成了她自己的立体化空间形式。
(一) 流散化写作
若想熟悉语言的艺术,就要努力地揣摩语言大师的文本,而文本空间的构建主要受语言选择、文本线性时序和视角结构的影响。首先,语言无法表述空间的全部信息,语言选择会决定叙事中空间重现的效果。莱辛对语言的选择与她的流散身份联系密切,最终形成了她独特的流散写作特色。莱辛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流散者,在战后的英国并没有归属感。很多年后,莱辛仍坚持,“在伦敦我依然处于边缘,只靠手指攀附着。”[11]134作为非英国本土长大的流散作家,莱辛的作品中隐含了对其自身越界生存状态的认识,在语言的选择使用方面亦与本土作家大相径庭,而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其作品被自然地赋予了异域的空间特色。小说中,作家的语言在某些地方是刻意为之的含糊,如小说正文中数次提到了“它”,“在我们讨论它之前,我要把情况描述一下。它让人感觉到的是不可避免的紧迫的威胁。”[1]3“它”究竟是指什么?是灾难危机,还是内心的创伤?“它”在这里被指定为一种危险、一种接近和一种疏远。在这里,“它”是什么并不清楚,但“紧迫的威胁”让人联想到莱辛本人的流散经历。她提到,从儿时起,“英格兰的遥不可及已深深印在我心中。”[12]38莱辛心目中的英国是人间天堂,是不可触摸的神圣存在,而多年后来到这里,她看到的英国却是一片废墟,肮脏无比,破败不堪。这样破败的形象与莱辛向往的人间天国相去甚远,也使她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一切,身在其中却始终不能融入其中。这个中性的主语“它”是个无面者,因此所有语言都变得可能,亦近亦远,是一种内指,也是空间跨度下身份焦虑的反射。笔者认为读者阅读时不自觉地会联想到莱辛的经历,对“它”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除此之外,文中用了许多“或许”“可能”之类的含糊词语,描写现实生活时的无序、混沌,也隐喻了莱辛作为流散作家心理状态的迷茫。而在描写“个人空间”中的场景则非常注重细节,含糊词语的使用则较少,这也是作者自己童年创伤的写照,暗示童年的创伤难以抚平。读者在整体把握语言文本的条件下,会自觉产生一种模糊的空间感,距离亦近亦远,空间画面亦混沌亦清晰。
(二) 立体化空间形式
“空间”理论的提出,将叙事从遵循时间规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结构上,现代小说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一种抽象的知觉空间,这种形式只有当读者理清小说线索,对小说有了整体把握之后,才能在读者意识中呈现,换句话说,空间形式即读者反应的产物。《幸存者回忆录》以“我”的公寓、窗外的人行道、墙背后的空间为线索进行叙述,叙述随心所欲,形成了空间化的效果。文字中表露出各种非理性、荒诞等因素,使读者在脑海中编织一张网,一种特殊的空间感在创造中产生。当读者抓住以上三个空间点进行反思时,可感受到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三个并置空间作为情节展开的背景各自独立,因此这种结构被叫做“桔瓣”式结构。在这种空间形式中,所有的叙述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进行,即“我”的无意识。“我”通过一次次造访艾米莉的个人空间来探索自己的无意识空间,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勇敢地面对,积极地修复,成长。
佐伦曾提出文本的空间视角由一系列“此在”与“彼在”构成,即某个叙述点的空间和其背后整个世界构成的对立关系,某一叙述点被视为前景或背景的事物之间形成的“此在”与“彼在”的空间关系。[9]322这种空间关系亦可资解释小说中混乱的都市意象与当时混沌的英国之间的关系。二战后的莱辛怀着敬畏激动的心情来到英国,却大失所望,她终于来到梦中“天堂般的英格兰”,而眼前却满布战争的阴云。她观察敏锐,精准地指出英国混乱腐朽的一面,并将伦敦作为原型写作,将其镜像化处理,勾勒成文中末日废都的形象,在这里,废都则是破败伦敦的化身,二者构成“此在”与“彼在”的空间关系。小说《幸存者回忆录》中语言、时序及视角等元素使文本空间化,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主动联系前后内容,获得独特的空间阅读体验。
四、结语
莱辛对人类生存空间的转换以及社会空间的构建等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这点从其作品《幸存者回忆录》中可窥一斑。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除了作为故事发生的载体,还具有自身的表征意义与隐喻功能,对立的空间作为一种权力符号,象征着英国森严的社会等级关系,空间亦作为身份性别的隐喻,暗示了女性被历史建构的边缘身份。小说中三个女性人物在空间中的运动状态及轨迹展现出女性主体建构与成长的不同命运,表明建立在依附男性基础上的女性自我实现是不完整的,暗示了女性实现人格独立的可能性。在文本方面,结合莱辛特殊的流散经历对小说的语言、叙述时序及视角进行剖析,发现莱辛对语言的考究影射了她的流散经历,并置的空间形式也使读者耳目一新,获得独特的空间感。而虚构的“废都”与现实的伦敦城构成“此与彼”的空间关系,使读者感受到莱辛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处于困境中人的鼓励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