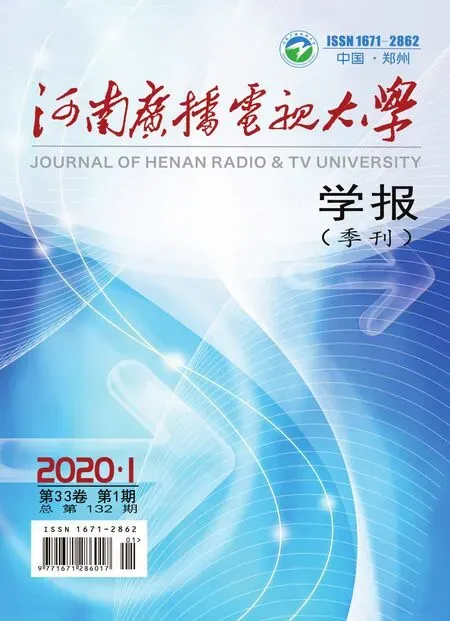王阳明思想中“乐”的探析
田晓丹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乐”一直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对于“乐”概念诠释,历代儒者主要集中于寻“孔颜乐处”这一范式。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李泽厚先生提出了“乐感文化”,并将儒家的“乐”文化纳入了审美体系去研究:“‘乐’在中国哲学中实际具有本体的意义,它正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成果和表现。”[1]“乐学”成为宋儒及其之后所追求的体认功夫之一,王阳明对此也是多次提及。在近代学术界,关于“孔颜乐处”之“乐”或者王阳明思想中“乐”的研究,也不乏大家。但在近期的阳明学学术界,有关“乐”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牟宗三认为,王阳明所谓心之本体之乐是就超越的道德本心辗转引申的分析辞语。[2]张铁君认为“乐”是“内省而不穷于道”[3]。陈立胜认为王阳明虽有“乐是心之本体”的说法,但这毕竟只是对心之体的一种描述,而不专属于“乐”本身的厘定上面。[3]
一、王阳明“乐学”渊源
在王阳明思想中,不仅有“良知是心之本体”之说,更有“乐是心之本体”的阐发。王阳明对于“乐学”的重视,有着某些渊源,主要包括家传和学统两个方面。
王阳明曾祖王杰自幼有志于圣贤之学,受儒佛影响,崇尚曾点之乐:“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4]王阳明祖父王伦,“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视纷华势力,泊如也”,世称竹轩先生。“雅善鼓琴,每风月清朗,则焚香操弄数曲。……识者谓其胸次洒落,方之陶靖节、林和靖,无不及焉”[5]。王阳明父亲王华因忤刘谨而致政归,曾有一客人劝他学道家神仙之术,他谢之曰:“人所以乐生于天地之间,以内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亲,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从游聚乐,无相离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者何异?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圣贤之学所自有。吾但安乐委顺,听尽于天而已,奚以长生为乎?”当时也只有岑太夫人稍稍信奉佛教。王华既归,“即息意邱园,或时与田夫野老同游共谈笑,萧然行迹之外”[6]。由上可知,儒家“乐”的思想在王氏家族中历有遗传,对王阳明的寻“乐”处思想影响甚深。
除了家庭的影响,王阳明的“乐学”与传统儒学的“孔颜乐处”也有着不解之缘。《河南程氏遗书》卷二记载:“昔受学于周茂叔,每另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7]自周濂溪始,寻“孔颜乐处”便成了宋儒的必修课。孔子有着积极的人生观,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对于颜子之“乐”的资料,主要是出自《论语》中孔子说的话,如:“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子一直秉承着孔子所倡导的仁者风范。可见,孔颜之“乐”是与“仁”“道”联系在一起的。
自先秦儒家对“乐”问题的诸多思考之后,宋儒再次高度重视并将这一命题提高到本体论的角度,由“仁”之乐发展为“理”之乐。二程从学于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濂溪时,每每被告之要寻求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在周濂溪看来,“孔颜之乐”是与“诚”一体之乐,亦即与伦理道德规范及与“生”“成”之天道合一之乐。[8]明道秉承濂溪先生超越伦理道德之境的“孔颜之乐”,并进一步发展为“浑然与物同体”之乐。而伊川对于“乐”的体悟更是绝妙:“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7]其中伊川有关“乐”的思想对王阳明影响甚大。在《答王虎谷》中,王阳明写道,“程子云:‘知之而至,则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自有不能已者,循理为乐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则知仁矣”[9]。王阳明认为,若以“循理为乐”,也必能体仁之乐。继二程之后,朱子面对弟子关于“孔颜之乐”的追问,说道:“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10]“人之所不乐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则乐矣。”对此“孔颜之乐”的回答,朱子这一不外求、而反其自身的理路与后来阳明的“乐”的分析很接近,尽管一个“克己”、一个“致良知”,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王阳明认为,“常快活”就要去除私蔽:“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11]
二、本体之乐:致良知
在王阳明思想中,心之本体有很多,其最主要的便是“良知”。“良知”的观念出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12]。
在这一语境下,王阳明将“良知”的概念侧重于孟子的“四端”,并认为四端就是良知,比孟子更明确地把良知与四端结合起来。[13]其相关解释,在《〈大学〉问》中亦有表述:“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得,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11]王阳明的“良知”,是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这一道德意识,不仅具有内在性,还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答顾东桥书》中谈及朱子晚年定论时,将“良知”与“天理”等同:“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14]致良知于万事万物,则万事万物之天理也自会显现。王阳明将《大学》的诠释放置于孟子的思想理路,其“良知”之乐的感悟与孟子“四端”的发觉是一致的,皆是顺应“天理”的体现。
王阳明说“良知,心之本体”(《答陆原静书》),同时也说“乐是心之本体”(《答陆原静书》)。二者皆是本体,那么此二者又有什么关系呢?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乐之本体”,他在《答陆原静书》中说: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12]
在王阳明看来,心之本体之乐,虽然与七情中的乐不是一回事,但也不外乎七情之乐。王阳明所说的“心之本体”之“乐”,不仅是形上的道德主体,同时也是行下的实践主体。虽说圣人有纯真的快乐,这快乐与常人并无不同。只是常人有这种快乐而不自知,却自寻烦恼,致使自己处在迷惘之中。即便是处在迷惘之中,这种快乐也未必不存在。只要一个念头豁然开朗,反身内求,感到诚意,这种快乐也就能体会到了。“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15]王阳明认为,七情是人心本有的,没有善恶之分。情之所发,非因外在的善恶所定,而是由于主体的心所导致。因此,本体之乐就是顺七情的自然流行,并且无所着。有着,便不是心之本体,也不能称之为天下之大本。不着,任何一情都能表现出它的“真乐”,此乐也就是忘情之乐。冯友兰先生曾说:“忘情者,无哀乐。无哀乐则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与哀乐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16]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15]
在这里,“乐”与“哀”不只是七情中相对的一对情感,而更加突出的是作为自然流露的感情表达范畴。二者同为本体范式,当乐则乐,当哀则哀。情动,而心不动。这也便是“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而此乐亦在的原因。这一范畴上的“乐”,上升到了具有道德自由主体性的“乐”。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曰:“请问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15]
正德十五年(1520),陈九川问王阳明如何找到稳当快乐的办法,王阳明便说“致良知”。那一点良知,就是自己的准则。当意念所致之处,对错都是明白的。只要依照良知而不欺瞒,便会自然地择善去恶。王阳明之乐、之安,在于“致良知”。“乐”的体验就在于自我复得了“良知”的所有意蕴,是作为自我生命的本性所在,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的生命本体,实现自我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这也就达到了真正的“乐之本体”自身。[17]
三、乐与忧中体认圣人之志
“圣人于忧劳中,其心则安静,安静中确是有至忧。”[7]伊川敬慕圣贤之志,对于圣人有关忧的态度和境界,也是体会深刻,而有了这“忧中有静、静中有忧”的认识。后期的王阳明,与伊川一样,对圣人之志尤为重视。成圣是王阳明年少时就有的志向,在他11岁那年便有“等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的先见。在其18岁那年,“始慕圣学”,提及宋儒格物之学时,便说“圣人必可学而至”[18]。尽管阳明明志如此早,但其证见过程却是坎坷忧苦,可谓“百死千难”。虽是忧苦,阳明也依然秉承“乐”这一心之本体,在“乐”与“忧”中体味圣人之志。
七情乃人之常情,最易束缚于人而使之不能得道。七情也是王阳明及其身边人常提及的话题,多次说到如何从七情中体悟心之本体。王阳明认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15]圣人与常人并无太大差别,不过是一个明心见性,一个迷失本心。所以对于圣贤所有的乐,常人有了却不能察觉,反而自寻许多烦恼,致使自己忧苦迷惘。然而,即便是身处于这忧苦迷惘之中,这本体之乐也未必不存在。只需要反身内求,使心至诚,这种快乐便会显现。“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12]。圣人能立于天地之间,教化万物,也都是从喜怒哀乐还未生发之中逐渐涵养的结果。王阳明还以种树为喻,让人立志当下的功夫。他还说,就像自己心痛一样,一心都在疼痛上,自然不会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也正如“哭则不歌”,圣人的心体也自然会如此。此外,王阳明还认为当乐以忘忧:“‘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15]“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本出自《论语·述而》有关叶公问孔子与子路,而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和总结,认为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9]。王阳明以此来陈述圣人无论是乐还是忧,都是无“私”,也就是在至诚的境界。如此,方能致知。而致知,也不过是各自顺应自己天分的程度去做,“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15]。
虽有“至人无梦,圣人无忧”①出自邵雍的《忧梦吟》:至人无梦,圣人无忧。梦为多想,忧为多求。忧既不作,梦来何由。能知此说,此外何修。的说法,但圣人也常忧,甚至是“终身之忧”。《五行篇》中有言:“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20]圣人之忧,忧不在己,忧在成人、成物。王阳明在述“拔本塞源”之论时略曰: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4]
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之人,也并无内外远近的区别。圣人的心如此,常人的心,最初也并无差异,只是后来心中有了“私我”的念头,被物欲蒙蔽。因此,圣人便有了忧虑,便推阐他们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来教化天下,希望能使人们克服私心,扫除蒙蔽,以恢复本来所共同的心体。王阳明一直致力于圣贤之道,在与他人的对话说,也多次提到“圣人”,并认为圣人是可以学得的:“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是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以为圣人。”[12]孔子曾将人分为三种——上人、中人、下人,并说上人下人不可移也。王阳明认为,不是不可移,是不愿移。并认为,常人与圣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因为一个迷失心性,一个明心见性。并且,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若要真正成为一个圣人,只需致良知即可。圣人之忧,不仅在以仁推施于天下,也忧其教人不能尽。王阳明立志成圣,却并非只是自己成圣,而是要天下人皆为圣贤。以王阳明的思路,若致良知,满大街都是圣人。所以,王阳明亦有终身之忧,忧其“良知”学不能人人致得。一日,阳明喟然发叹。九川问曰:“先生何叹也?”曰:“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致良知”三字被王阳明称之为“真圣门正法眼藏”,若能致得,如同“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21]。想到这义理如此简单明白,却“经沉埋数百年”。“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此阳明之叹,有如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呼。圣人不忧,忧则忧道心不显,忧则忧不能成人成物。阳明之忧,便在这“良知”简单明白若此,却长期不被人挖掘。想要将此理说给人听,却又恐一语说尽,得来容易,不加珍惜,只当是“一种光景玩弄”,不能落实到日用之间,只怕是辜负这一本心。“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人,乃是天地之心,而天地万物,与我本为一体。百姓的困苦荼毒,哪一件不是自己的切肤之痛?“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己”。应该是他有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就像自身有迫切的疼痛一样,即使想撒手不管,却仍有不容撒手的冲动。“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22]
王阳明思想的“乐”正是在寻孔颜等圣人所乐何处之时,有了自己的“乐”,悟得了人人当如何常“乐”。无论是寻“孔颜乐处”,还是求圣之道,都不过是发明本心,致良知而已矣。无论是在王阳明所处的纷乱时代,还是如今物化世间,这一“乐学”的体悟便是一股自然清风,使得心体存养达到与天同德的程度,人人皆“不器”,也各得其乐。对于“孔颜乐处”的探寻,王阳明对“乐”的诠释和体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具有了他个人的鲜明特色。“乐为心之本体”这一内化以及超越的理路,为后人在相关方面扩展了思维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