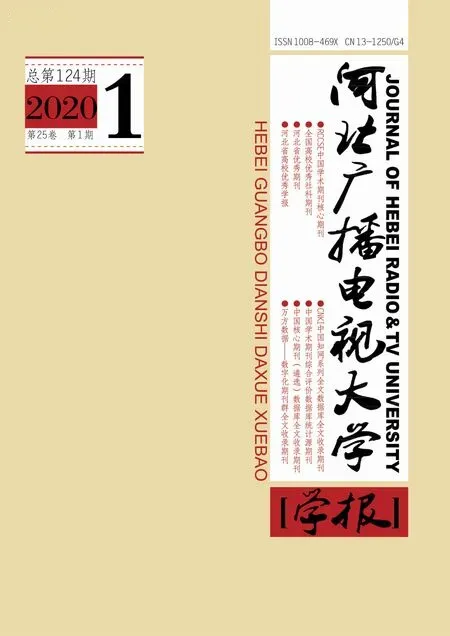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京师社会救助机构探析
韩雨楼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处于困境的人民具有义不容辞的救助责任。民国北京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出台和完善相关救助政策,组建了粥厂、收容所、教养机构等慈善场所。赈委会和新设置的警察厅是政府救济的主要实施者,此外,来自社会上的多元救助方式是对政府救助的必要补充,为处于底层的边缘人群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一、粥厂
“民以食为天。”在京师百姓的日常开销中,占比最大的是食物消费,达到了68.8%,①李景汉:《北京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社会学界》,1929年第3卷,第3-5页。在特殊时期甚至达到85%左右。社会救助体系中,食物救助是关键性的一环。对于陷入贫困的人群来说,获得食物是生存的当务之急和根本需求。解决食不裹腹最直接且具有代表性的救助,莫过于设立粥厂。民国初期私人团体设厂较多,1926年后政府逐渐成为粥厂救济的主导者,赈委会、京师警察厅作为主要负责部门,制定并形成了一套富有成效的运作模式。
官办粥厂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另有部分社会捐款(私人团体和个人捐助)。粥厂花销与贫民数量关系密切,工具、燃料、人头等费用基本稳定,以1915年为例,上述费用占全部运作费用的18%—26%。②(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01页。美国经济学家甘博在1915年的记录中,统计出7家粥厂共施粥963 201份,费用合计为11 260.61元,所用粮食1 723.17担,每担价值为5.10元。当贫民数量激增导致粥厂入不敷出时,警察厅可以向总统府、内务部、财政部申请拨款。
粥厂的开放时间大多具有季节性。开厂闭厂的时间都受到季节影响,一般在秋冬季天气寒冷之后开设,气温转暖之际闭厂。部分粥厂会登报告示,通知“粥厂提前开办” “粥厂续办一月”等。粥厂提供的粥由小米和大米混合熬成,其中7/10是小米,3/10是大米③(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300页。,盛于木桶中抬至放粥处以铁勺散发,每人得一勺之粥,约合4两之米。④张金陔:《北京粥厂之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页。粥厂的救济对贫民来说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保证了贫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使得冬季因冻饿致死的人数大为减少。
粥厂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为使真正贫困者享用救济粥,各粥厂也是煞费苦心。如有的粥厂会自备碗箸,要求贫民在厂内食用,既使贫困者较为体面的食用救济粥,也避免偷奸耍滑者领粥回家饲喂鸡犬,造成食物的浪费。有的粥厂实施定时关门制度,防止无良人员重复领取。颁发粥牌是粥厂通用的管理形式,粥牌由竹制、木制或厚纸板制成,作用相当于领粥证。除了一般粥牌,还有特殊的“优待牌”,对残疾、老弱或者孕妇等不便领粥者颁发优待牌,上面写明牌主信息,可以委托他人代为领取。有的粥厂粥牌用颜色加以区分,按性别区分(红色女用,黄色男用)或按贫困程度区分(红色极贫,白色次贫),领粥时以红色优先,以此来维持秩序。据1920—1921年统计数据,京师的粥厂每厂每季领粥人数不下二十万人,如计算全市每季领粥人数在5 167 000万人左右。①张金陔:《北京粥厂之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其中“男丁人数相对较少(12.21%),女丁(43.72%)和幼孩(44.06%)占有绝对数量”。②丁芮:《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2011年,第218页。领粥的男性多有残疾,少有强健者,妇女由于缺乏谋生的手段,更容易落入无以为继的境地,需要接受救济的数量远多于男性。由此可见,每日的施粥维系着数十万贫民的生计,粥厂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救助方式,其作用无可替代。
二、收容所
1.育婴堂
民国初期,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城市发展带来的道德上的开放,弃婴问题变得凸显起来。加之旧有的育婴堂设施陈旧、资金紧张、管理散漫,改造势在必行。1917年,政府正式设立育婴堂,经费主要来源于警察厅、市政公所、内务部和私人捐助。据1918年的财政报告显示,官方的资助占 2/3,民间捐助达万元以上,占1/3。③段正华:《近代中国儿童救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71页。不过限于北京政府的财力,育婴堂的经营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接手后才有所好转。京师新的育婴堂既保留了传统育婴堂的特点,又采纳较为科学的管理方式。依照管理条例,育婴堂对0-3岁的婴幼儿进行救助,一旦婴儿被送入堂中,不具备抚养能力的父母不能将之领回。申请领养婴儿的家庭要经过审核,领养后如出现虐待等情况,育婴堂有权将婴儿接回。在婴儿的照料方面,育婴堂采用传统的寄养制与留养制相结合的方法,既节省了经费,也能促使乳妇对婴儿产生感情后进而收养。育婴堂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弊端是制度难以得到很好的实施,育婴堂督查不力,出现婴儿死亡而乳妇仍冒领工资的情况。④黄忠怀:《从育婴堂到救济院:民国时期传统慈善事业的危机与转型——以保定育婴堂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第1期。在日常管理中,北京的育婴堂有明确的职能划分,会计、文牍、庶务等各司其职,职责划分清楚,体现了管理方式的进步。
2.养老院
京师的养老院是无依无靠老人的终老之所。甘博把西方慈善机构设立的机构称为“养老院”,中国本土的机构(尤其是官方的)称为“老人院”。甘雨胡同设有一所由外国教会组织、商业界人士筹款、外籍妇女管理的养老院,专门收容年老妇女,为她们提供较为稳定的食宿。每月的衣食总花费仅有2.10元,但是环境清洁卫生,管理也更为人性化。一些中国妇女借鉴甘雨胡同养老院的管理经验,创办了类似的老妪院,有66名妇女得到养老救助。⑤(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30页。与外籍人士创办的“养老院”相比,老人院仅仅是维持老人生存的状态,对其精神毫不关心,这也是中国慈善机构里的一项通病。
民国后大部分私人养老院被警方或政府接手,民间创办养老院先经过政府审批,“大慈善家朱秀峰,现在联合同志,集资在北城鼓楼苑地方,创办养老院,专收年老无依贫民,已妥订章程,呈请内务部立案,但不知能否批准”。⑥《立养老院》,《京话日报》1918年第2559期。官办老人院需要警方推荐方能进入,也有通过“派人分赴各街市散发一种养老券”⑦《设贫民养老院》,《顺天时报》1923年5月3日。的方式,使贫苦老人得以入院养老,生活条件要优于贫民救济院,入院后就可以在老人院安度余生。⑧(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00页。
3.疯人院
疯人院是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机构。北京精神病患者数量较多,落后的社会观念和医疗条件,使得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许多精神病患者走失或者被遗弃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歧视,其身心受到的伤害往往更甚。
疯人院设立始于20世纪初,建立疯人院的目的,一是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民政部于1907年提议设立疯人院,“大略以男女分为两院,已谕令司员群议章程,不久即奏请实行矣”。①《议设疯人院》,《顺天时报》1907年10月。1908年疯人院首设,1913年由警察厅接手管理。多数精神病人生活难以自理,病发时还可能伤害他人,对病人的核查须由警察厅负责,病人由驻地警察上报区警察署批准后住院治疗,或者由家人、邻里上报申请入院。《顺天时报》载:“刘某向有疯疾……乃于日前其疯疾忽然大发,捉刀弄杖……其家属畏其凶祸,遂告知巡警,许其拘至警厅。经官医诊治,确保疯疾尚能医治,故经警厅送派刘某入疯人院医治矣。”②《疯人送院医治》,《顺天时报》1915年9月4日。1918年疯人院搬迁新址,扩大了规模,条件也有所改善。随着疯人院的宣传和人们认识的提高,增强了疯人院的社会影响力,收养病人人数从1918年的32人③(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120页。发展到1927年的100人以上④丁芮:《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2011年,第225页。。虽然疯人院救助的病人数量,比之全城应有之数量有很大差距,对病人的收管也更侧重于有暴力倾向的病人,但作为全国第一批创立的精神病院,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三、教养机构
1.儿童救助机构——以香山慈幼院为例
一般情况下,3岁以上的孩童不符合育婴堂收养的要求,但这些儿童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民国初期有许多民间的儿童救助机构,各方人士的筹款义举也时常见诸报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私人孤儿院,往往都体现出明显的“养”“教”结合的特点。创立于1912年的北京孤儿院原为收养烈士遗孤而设,后来扩大到收养孤儿和贫儿。龙泉孤儿院由龙泉寺的僧人主持,自清末以来,该院收养孤儿总计达3 000余名。⑤北京龙泉孤儿院编:《北京龙泉孤儿院报告书》,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 5 页。孤儿院除了收容儿童,还对其进行一定的文化和工艺教育,体现出明显的人道主义关怀。1918年,一所基督教残疾儿童养育院由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开设⑥(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19页。,属于私人慈善事业,规模不大但象征京师地区关注残疾儿童的观念开始萌发。
北京政府救助儿童的机构以香山慈幼院最为著名。1917年直隶水灾后,遗留下200余名儿童无人认领,负责督办灾情事务的熊希龄决定建立长效的救助机构对这些儿童进行教养。经过多方协商,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赵尔巽任董事会会长,熊希龄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参加开院大会的学生共700余人。香山慈幼院分男校和女校,基础设施齐全,另开设图书馆、理化馆等教育类场所,为儿童提供了较好的成长环境。“1922年下半年,熊决定男校增设中学部和中等职业部,学生接受工科教育。女校设师范部,训练乡村教育师资及培养本院蒙养园及小学之教师。”⑦李友唐:《北京香山慈幼院始末辑要》,《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除了较为完善的基础教育,香山慈幼院还对进入大学深造的孩子进行资助,为离院的学生安排出路。在熊希龄的经营筹划下,香山慈幼院并未出现经费短缺的困扰,并在20年代发展迅速,1930年在院人数达到1 670人,为慈幼院历年所收儿童数目的峰值。⑧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北京政府时的香山慈幼院经历了最辉煌的时期,不仅完成了对儿童的“教养”,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救助体系,代表了中国本土儿童救助的最高水平。
2.妇女救助机构——以济良所为例
“济良之意为凡在沦为下贱之人,济之使得从良,而不致永陷于火坑水井也。”⑨《济良所衍义》,《申报》1905年1月28日。北京济良所1906年由外城巡警总厅督同绅商办理,1907年重定章程,1913年1月由京师警察厅接管。⑩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纪要》,北京:北京民社,1944年版,第54页。搬迁后与京师的女习艺所和妇女感化所合并,成为综合性的收容所。济良所的人员构成复杂,有“诱拐抑勒来历不明之妓女,被领家需索重价掯阻从良之妓女,被领家凌辱之妓女,不愿为娼之妇女,无宗可归无亲可给之妇女”①田涛、郭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被送到这里接受救助和监督。
济良所的内部环境宽敞整洁,有缝纫工作的厂房,其他屋舍为传统的四合院形制,另设有年龄较小女性所需的学堂,以及专为受救助妇女的孩子准备的房屋。妇女感化所所处位置偏僻封闭,内部环境脏乱,但管理上却更为严格。除了待遇上的差别,被救助的妇女和感化所里的妇女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济良所的妇女须结婚或被其亲戚收留后方能离所,而感化所里被“关押”的妇女在刑期内无自由,在满刑期后即可离开。②(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278页。从成立之初,经费主要源于民间的筹集,政府虽有补助,但资金一直比较紧张。京师警察厅接手后,经费缺口由警察厅填补,以维持济良所的正常运作。相关数据显示,济良所的年终总人数多时达到123人(1917年数据)。③孙高杰:《1902-1937北京的妇女救济——以官方善业为研究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南开大学,2012年,第123页。济良所的另一项资金来源来自于所内妇女的婚姻。妇女的照片会挂在陈列室内,甚至在大门外公开展示,有相中者就可以进入申请流程,男方需要有三家商铺对其进行信誉担保,禁止虐待、买卖女方,并且填写涉及个人信息的申请表。警方核实无误后,即可缔结婚姻。男方需在喜结良缘之后向济良所捐款,数额据男方对女方的满意度捐付,一般来说在10元至200元不等。④(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279页。济良所为陷入不幸的妇女以新的选择,体现了社会对妇女的关怀和人们观念的进步。
3.贫民教养院
贫民教养院以收留、教化贫民为目的,属于政府创办的救助机构。教养院中“幼童大者十余岁,小者四五岁” “男女疯人院等处”皆有,但凡贫民,不分男女老幼、是否残疾,都可以进入贫民教养院。入院者既有自愿求助于教养院的,也有被警察强制带入的。尤其冬季或出现自然灾害之时,贫民和灾民更需救助,除了原有的贫民教养院,还会另设灾民教养院、儿童教养院等。
教养院内部设施简陋,人满为患。美国人甘博调查的一所教养院里,屋中九平方米的面积,由一层木板分隔为上下两层,通常会住15人左右。如此逼仄的住所,即便在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也难以维持房间的卫生状况,特别在寒冷的冬晚,由于供暖不足,人们只能尽量把通风口封紧,致使屋内空气无法流通。教养院给贫民提供衣食的救助,贫民的衣物很多是警察换下的旧衣,“所穿之衣服者,系巡警换下之旧制服,涤去泥污而改造者”,⑤《教养院参观记》,《顺天时报》1916年12月30日。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足以御寒。贫民能得到的食物是小米粥和咸菜,大致是每人小米1斤,咸菜2盎司(50克)。⑥(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27页。教养院内设有养病室安置病患,重病患者有单独的屋子,但是由于卫生条件及医疗水平的有限,病人的死亡率较高。
贫民教养院具有了初步“教”的性质,教养院里的儿童“应对进退皆有秩序”,院内设授课室,聘请教员教课。其他有劳动能力者每天要出门劳动,劳动者每日得到5个铜板,但单纯体力劳动无法使他们掌握可以谋生的技能。如果贫民选择离开教养院,就不得不沦为乞丐。如果贫民无法谋生,可以回到教养院,但若有行乞之事,则不会再被收容。从贫民教养院的实际管理来看,教养院“教”的成分仍然较少。政府希望教养院起到指导贫民自立的作用,但从实施效果看,显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贫民的困境,出院者禁止行乞的规定则更像一种警戒。
4.教养局
教养局主要为收容“轻刑”犯人所设立,目的侧重于维护治安和施行教化,另附有教养贫民的职能。教养局收留的犯人来自各个阶层,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刑期均不超过一年。其中有因虐待买卖济良所领回的妻子的商人,有素行不良、行偷盗之事的乞丐,有因违反规定被送至教养局“以示惩戒”的巡警等。⑦《巡警送教养局》,《顺天时报》1917年10月30日。也有一些人是被家人送入教养局的,多因家中无法管教,希望教养局能代为约束管制。男性贫民、灾民也可以进入教养局,但需经警察核实情况,符合贫困的标准方可入局。局内的工作有“搓绳子、剪裁、木工活、铁匠活和纺织”⑧(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14页。,这些劳动有些在专门的工棚进行,有些在露天进行。犯人和贫民在一起劳动,衣食由教养局提供,但是他们拿不到报酬,还需要戴着脚镣。每周日允许贫民出门放松,而犯人不享受这项权利。贫民和犯人是分开住宿,居住拥挤不堪且卫生条件极差。即便如此,教养局提供的帮助对身处于困境中贫民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1927年3月警察厅统计数据,教养局每日人数在180人左右,成为京师社会救助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游民习艺所
北京政府时期京城里开办有不同类型的习艺所,有为女童所建的女童习艺所(属私人慈善机构,所内女童40人左右,主要学习刺绣),有为囚犯所建的监狱习艺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游民习艺所。游民习艺所最早由清政府的刑部设立,北京政府时期先由内务部负责,1917年转由警察厅接管。①(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14页。游民习艺所仅招收8岁以上的男童和年轻男性,并为入所人员提供食宿。
《顺天时报》曾对游民习艺所进行过详细的介绍,内容包含生活环境、教授课程、管理制度等。习艺所的宿舍为“X”字形,共分四间,每铺都有规定名额,可容纳700人生活。房间内部注意通风,床铺、地面清洁。所内浴室、理发室、病房、操场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所内人员“每周洗一次澡,每十天剃一次头,吃饭时有一定的开水供应”,主要食物是咸菜、菜汤和小米粥,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平均为2元。②(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18页。游艺所的课业“等于普通小课程度,有图文、修身、国书、算数、手工、体操、歌唱等科目”,工徒每日还要做工,有木工、制肥皂、织布等项目。这些工徒制品“名目繁多,各种皆有”,在国货市场上也占有一定份额,是游艺所收入的重要补充。18岁后工徒可以离所另谋职业,或由警察为他们寻找一份工作,也可继续由游艺所雇佣。甘博在评价游民习艺所时,指出习艺所存在预防时疫的不足和娱乐项目的匮乏等弊端,影响青少年的教养效果。
晚清到近代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就是北京政府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社会的激烈变化,各种自然灾害也频频来袭,对社会救助的需求急剧增加。上述原因促进了北京政府时期社会救助事业的快速发展,政府既延续了旧有的社会救济制度和机构,也有所创新发展,新变化体现在新的管理模式和新开设的机构上(如济良所等);民间的社会救助事业更加繁盛,救助方式和机构的设置更加灵活多样,可谓百花齐放。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下,政府作为社会救助的最大主体,对社会救助事业与其应尽的职责虽然有较大差距,但其社会救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切实救助了数量众多的底层人民。社会救助事业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救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