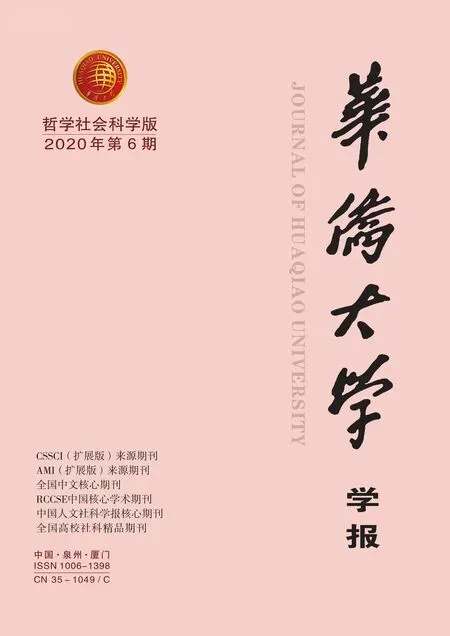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双重认知及治理
○朱志伟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引发的革命浪潮正在重塑着现有的社会形态与组织关系,改变传统公共领域的生态范式。因信息传播空间的虚似化、流变性及技术化,新媒体与网络平台得到了迅速发展,恰好促进了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影响网络空间的社会秩序。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情境中,网络谣言给原本复杂的疫情治理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谣言内在价值与认知差异性存在关联,正确把握这种内在的差异性对于重大疫情的防控具有积极价值。
一 网络谣言:技术赋权下话语再造的双重性
长期以来,谣言一直伴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它处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并因社会情境的不断变迁有所不同,是一种“没有得到证实的解释行为”(1)Peterson W A,Gist N P.Rumor and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1, (2), pp.159-167.“缺少可靠来源的信息沟通”(2)Pendleton S C.Rumor research revisited and expanded.Language & Communication,1998,18, (1), pp.69-8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与经济模式的改变,初处探索期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不完善、理念滞后的情况,各种社会矛盾、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为谣言滋生与传播提供了环境。正如勒莫所认为的那样“谣言本质上是对失衡或者社会不安处境的一种客观反应”(3)[法]弗朗索瓦丝·勒莫:《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唐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5页。,社会发展、经济改革、重大疫情、特定灾害等领域的网络谣言不断涌现。谣言之所以传播主要取决于事件主题对造谣者的重要性与事实要素被掩盖(4)Allport G W,Postman L.The psychology of rumor.New York: Henry Holt,1947.pp.89.。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重要性与模糊性是谣言的基本要件,两者缺一不可,并以此提出谣言产生的公式是:谣言=(事件的)重要性× (事件的)模糊性(5)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刘水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4—95页。,但这种划分忽视了个体层面的心理因素,如焦虑、不确定性、强调结果(6)Rasnow.R.Rumor as Communication: A Contextual Approach.Journal ofCommunication.1988,38,(1).pp.12-28。谣言具有很强的流变性,会随着传播者与传播介质的不同而产生变化。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信息技术促使传统媒介下的单向度传播模式走向一种双向互连甚至多向联动的模式,所有的个体、组织都被整合在网络节点中,这恰好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网络谣言不同于传统谣言,网络新媒介的传播力更强,舆情的影响更容易出现群体极化(7)李静,谢耘耕.《网络舆情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0—2018 年10600起舆情事件的实证分析》,《新闻界》。https://doi.org/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00221.006.,其零成本转发机制与信息检索机制让谣言的获取与传播更容易,而网络信息的高度虚似性与隐蔽性提升了谣言的辨识成本(8)刘鹏:《网络谣言界定及法律规制》,《学术界》2016年第4期,第89—96页。,同时也会受到网络技术结构与谣言扩散速率的影响(9)Nekovee M,Moreno Y,Bianconi G.Theory of rumor spreading in complex social networks.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2007,374, (1) pp:457 -470.。
但无论是谣言还是网络谣言,两者本身就蕴含着真实与虚假的双重性,这极大地增强了这种话语形态的复杂性。在信息技术赋权之下,谣言与网络空间的虚假性、不确性相结合,很容易引发“真相淹没”(10)周亚越:《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80—84页。。以此导致学术研究中更加注重谣言虚假性的研究,如认为网络谣言对政治安全提出挑战(11)李昊青、洪礼博:《面向政治安全的网络谣言风险分析与防范策略》,《现代情报》2019年第5期,第156—165.、产生自我强化,引发社会恐慌或对政府公信力危机(12)顾金喜:《“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93—103.、降低社会信任水平(13)滕婕、夏志杰、罗梦莹等:《基于Multi-Agent的网络谣言传播事件中信息主体信任识别研究》.《情报杂志》,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200203.1449.002.html等。尽管如此,学者对谣言蕴含的真实性因素的讨论仍然没有停止。如有学者认为网络谣言是对特定事件的一种反应,本身具有“真实”的一面,它是客观真实、媒介真实、主观直实于一体的递延偏差(14)刘力锐:《论网络谣言的媒介化再生产:三种“真实”的偏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108—117页。,在特定的利益博弈下,信息流通的真实性比较模糊是真实被淹没的主要因素(15)王理:《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实证分析——基于2010—2012年网络谣言信息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86—99页。,而卡普费雷也指出“谣言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引发论证尴尬是因其蕴含着真实性”(16)[法]让·诺埃尔·卡尔费雷:《谣言》,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页。。可以说,网络谣言的真实性与虚假性是正确理解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重要维度。
然则,反观现有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关于网络谣言双重认知的研究还比较分散,缺少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的分析视角,特别是对于网络谣言的真实性与虚假性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机制研究仍然不足,而这恰好是把握网络谣言传播规律,认识谣言复杂性的关键,对及时识别网络谣言,合理回应,避免辟谣失灵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以新冠疫情为例,通过案例分析法研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双重认知与治理机制,材料涉及到政策文件、新闻报道、音频视频等方面。同时,为了全面呈现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流变,笔者十分注重网络谣言的纵向发展,以期通过考察较长时期内网络谣言认知的差异性,为较好地掌握网络谣言的不确性与复杂性规律提供启示。
二 虚无的谎言与迟到的真相: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双重认知
2019年12月初武汉发现了不明原因的重症肺炎事件,后经过不断论证、确诊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武汉市宣传封城、多地区相继出现确认病例。一时间关于新冠疫情的网络讨论不断增多,各种网络谣言也随之泛起。其中,讨论程度最为激烈,影响范围最广的即属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被界定为网络谣言传播者,但最终被感染去世一事。本文就该事件的兴起与社会影响研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双重认知。
(一)虚无的谎言:事件兴起阶段的价值定性
与一般卫生事件相比,重大疫情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破坏性大、不可预见性、资源投入量大、社会舆论关注度更高的特点,更容易引发社会关注,需要建立及时预警与响应机制。从2019年12月初开始武汉陆续发现了不明原因的重症肺炎患者,因感染人数持续增多,作为在医院工作第一线的李文亮首先觉察到事件的严重性,于12月30日在同学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提醒同行医生与家人注意防范。随后,李文亮还在群里发了一份写有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SARS冠状病毒阳性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和患者胸部CT与病毒分裂的消息。鉴于事件的严重性,这个有关生命攸关的预警随之传了出去,此事成为李文亮事件的行动起点。
任何一事件的形成都处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官方态度与社会情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事件的发展与定性。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也在网络上流传,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同时,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正式介入检查核实。2020年1月3日李文亮被所在辖区派出所传唤签署训诫书,“平安武汉”也发布了主题为“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报道称李文亮即在其中。至此,李文亮面向特定群体的疫情预警行为被定性为不实言论。
在李文亮发出预警到被定性为不实网络谣言的过程中,有三个层面的基本要素,即网络传播、疫情发展、执法机关的态度。其中,网络传播即是李文亮的言论是通过以微信为代表的现代信息媒介进行传播的,可以通过复制式蔓延、转化式蔓延与复合式蔓延(17)张玉亮、贾传玲:《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蔓延机理及治理策略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年5期,第91—96页。带来更大的影响力,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疫情发展即是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下,相关权威医疗机构还没有明确把握病毒传播途径与传播机理,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调查还没有结束,缺少对疫情的权威性判定。在此种情境下李文亮当时的预警被看作是非专业的、非权威的。如果说病毒尚不明确是影响预警行为的社会环境,那么公安机关的介入则是判定预警行为的决定性力量。在疫情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李文亮的网络预警是一种影响社会稳定,引发公众恐慌的越轨行为,而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因不确定性信息的散布引发新的社会混乱则是公安机关的具体职责,也是网络谣言治理的客观要求,是一种维稳导向的行政逻辑,具有很强的行政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
(二)迟到的真相:事件发展下的“辟谣失灵”
网络谣言是在假相与真相之间、信息传播力与辟谣能动力间形成的一种认知鸿沟,当这种认知鸿沟越大时谣言就越容易产生,认知的差异性很容易受社会情境的影响,在判定观念与行为时形成差异。但网络谣言也是对现实情境的一种回应,并不会随着话语性质的定性而发生变化,最终会在实现中得到验证。在被警方定性训诫之后,李文亮继续在岗位上工作。直到1月10日,他因接收一名新冠肺炎的病人后被感染,2月1日第三次核酸检测为阳性。李文亮也随之证实,“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18)新浪微博:李文亮2020年2月1日10:41分发文.https://weibo.com/u/1139098205?is_hot=1,2020-02-01。。从李文亮被训诫到感染入院再到最终确诊,直接反映出其在微信群中预警内容的真实性。
从当时疫情发展的社会情境来看,自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人传人之后,社会开始广泛认识到事件的危害性。随后,因确诊人数不断增加,武汉市宣布“封城”,全面进入战时状态。至此,有关李文亮在微信群中的预警又再一次得到了证实。2月7日李文亮去世,一时间社会对李文亮事件的讨论长时间占据热搜榜首。鉴于事件的影响程度,国家监委调查组抵达武汉,对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展开调查,并于3月19日发布最新调查结果,认为武汉中同路派出所对李文亮出具的训诫书不当,执行程序不规范。随后,武汉市公安局撤销训诫书,并就错误向当事人家属郑重道歉。关于李文亮的谣言定性随之得到更改。
网络话语是对特定社会情境的能动性反应,在实事话语与虚假话语之间发生作用,外界力量的影响容易使两种话语的价值定性发生变化,过早地将网络话语定性为网络谣言,稍有不慎即可引发“辟谣失灵”。李文亮事件的反转恰好说明网络信息识别与治理的复杂性与流变性,一方面要立足于事件发展,考察网络话语的证据是否充分,这是判定网络话语性质的关键;另一方面要关注社会情境,注重公众的态度与社会影响力。在发展视角下前文提及的网络传播、疫情发展、执法机关的态度都会随之发生改变,阶段性认知会有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有些信息即使政府部门没有公开或者辟谣其本身也经不起论证,而有的谣言则不都是虚假,也有可能是有事实依据的”(19)Grant M,Suchitra M.Rumour and gossip in organizations: a conceptual study.Management Decision,2000,38,(5),pp.339-346.。在互联网传播场景下,网络谣言的真实性是客观存在的,谣言治理是有限的,也需要因时因地做出调整。国家承担着网络信息“首要定性者”的角色,中央调查组对李文亮事件的调查结果是对此前被定性为网络谣言的回应,体现着对事实证据的尊重与民众言论自由权的保障,是一种保障民权,还信于民的社会性逻辑,以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正是在此逻辑下,李文亮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为首批抗击新冠疫情的“烈士”,充分肯定了他早期的预警行为与贡献,对于保障公众言论自由,发挥其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好的价值导向,体现着网络谣言分化治理的行动策略。
三 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分化的内在逻辑
传统谣言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让网络谣言流变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得以加强,其治理行为是一种传谣者与辟谣者之间话语权的博弈。但无论是传谣行为还是辟谣行为两者都是基于特定社会情境与技术媒介以达到其目的。在李文亮事件中,李文亮在信息平台上发布预警之后被看作是传谣者,具有公权力的公安机关是辟谣者,但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公安机关对预警信息的定性做出更改。要正确理解此种网络谣言分化的内在逻辑可以从场景事件、信息技术、行动主体三个层面做出具体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如下所示:
(一)场景事件层面
网络谣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谣言的兴起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蕴含着事实性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谣言是一种过度放大社会现实的认知形式,有脱离基本事实的价值倾向。两种不同性质的观点都是对网络谣言发生的社会情境与引发事件的现实认识,需要首先做出明确。就网络谣言发生的社会情境而言,它的生成不仅需要焦点议题、时间、地点、公众的社会心态等这些柔性形态的融入,也离不开网络技术、主体参与等硬性条件的支持,任何一方的缺少都很难形成网络谣言。李文亮早前预警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因其行为正处在社会公众对新冠早期的流行症状影响不确定,但却期待可以获得比较明确的认知时期,全社会都处于对此种症状的大讨论中,而李文亮在微信群中的预警行为恰好满足了社会公众对新冠认知的好奇心,且李文亮提供的预警信息具有很高的事实价值。在信息技术平台发布后,因网络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一时间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公安机关的介入、国务院调查组的论证与表彰都体现出网络谣言的复杂性,而双重认知行为产生的直接动因恰好是因这种复杂性增加了不同主体认识网络谣言的成本,干扰了对现实的正确判断。正是基于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多个组成要件在特定条件下都会受到影响,以此发生变化,具有很强的多变性。李文亮起初的预警信息只是发布在特定的微信群,直接受众是以往的同班同学,但因社会公众对疫情信息的关注度高,此预警信息被转发、再加工,受众群体向普通大众扩展,引发信息真实性与虚假性发生流转,导致信息结构失衡。这直接影响到了事件性质的改变。
在考虑社会情境性因素时,还需立足于引发事件本身的证据充足性、社会关注度。证据充足性是判定预警信息性质的重要维度。李文亮事件中的证据主要有自身提供的临床证据与社会证据两方面。起初李文亮提供的临床诊断与CT图像即是对疫情判定性质的有力证据,专业性很强,但因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与权威性认证的缺失,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被看作是网络谣言。其后,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与专家的认证,感染事实为李文亮早期的预警提供了现实证据。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这些证据的显示直接反映出李文亮早期的预警是对客观事实的反应,双重证据为之后国家检查机构调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是国家机构对证据科学性的回应。网络谣言具有传染性,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很容易形成群体极化,引发群体性不满。李文亮早期的预警则被看作是有效减缓疫情的重要方式,但在疫情初期这种预警没有得到社会与权威机关的重视,甚至当李文亮被公安机关定性为网络谣言的传播者时,仍然没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直至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社会与权威机关才意识到当初李文亮预警信息的前瞻性,政府开始审视李文亮早期预警行为的正确性。因此,引发事件的证据充足性与社会关注度则会直接影响到网络谣言性质的认知程度。
(二)信息技术层面
网络谣言之所以比依靠传统纸媒传播有更大的破坏性与影响程度,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谣言的组织结构,使谣言的话语形态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网络信息的生成是对现实社会情境的一种主观反映,承载着社会情境本身的价值。正因如此,网络信息常常同时具有真实性与虚假性。真实性是因网络信息基于特定的社会事件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承载着某种社会功能。虚假性则指因网络信息对社会事实的依据或信息来源的把握不准确,主观性的信息加工很容易偏离现实。李文亮在微信群中发出预警,这一行为的形成是建立在事实材料上,是对疫情在社会中扩展的能动性反应。但因这些事实材料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所形成的感染病例还没有得到临床认可与论证,可能具有虚假性的因素,公安机关以此做出网络谣言定性具有一定的情境合理性。同时,网络信息在实事依据没有明确时即形成一种价值判断的超前性,而这很容易满足社会公众对事件真实性探寻的心理,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形成个体与组织以后对事件的认识的“第一印象”(20)刘延海:《网络谣言诱致社会风险的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情报杂志》,2014年第8期,第155—160页。,形成加速信息的传播速度,带动了李文亮事件的关注度,使决策机构在及时性与有效性间产生决策困境。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化的信息传播与媒介功能日益突现。在当下,之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与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化的传播媒介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组织结构与存在方式,信息传导机制呈现出信息化与技术化的特征。在中国现有网络情境下,自2005年博客出现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以抖音为代表的直播平台、以淘宝为代表的商业平台、以科技论坛为代表生活服务平台、以喜马拉雅为代表的有声平台,传播媒介平台化也已成为当前网络谣言传播的重要方式。谣言在网络传导载体的助力下,以此呈现出“圈层式”或“放射式”扩散。李文亮在微信群中发布预警信息的行为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被传播,受到公安机关关注,离不开现代网络传播媒介的支撑,是技术赋权下的网络话语结构的变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相比传统传播媒体,借助网络媒介的信息自我审核机制相对较弱,更容易发布相关信息,传播影响范围会更加广泛,也更容易所大众所熟知。
(三)行动主体层面
行动主体是网络谣言被传播、被关注的重要因素,是网络谣言分化的主观性动因。就发布者而言,每个发布者都具有特定的目性。从以往网络谣言发布者的动机考察看,发布者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向社会发出预警,提醒社会公众关注某社会现象,以解决社会问题或维护特定群体利益;其二,追求特定政治利益,借助社会公众的认知与力量,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以获取特定的政治利益。其三,报复性或打击性行为,通过散布不实谣言达到对某特定对象或群体的报复与打击;其四,进行自我表现,利用公众的好奇心,以制造网络谣言的形式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同时,也要看到真理与谬误有着同样的传播方式,为了达到目的,一些变革性的信息或因群众接收度影响而会在有限的范围传播(21)[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8—39页。,在某些情境下,发布者对谣言的传播对象具有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则是对谣言传播效度的一种维护。综观李文亮事件的发展,起初的李文亮散布关于新冠疫情的信息从根本上讲是出于维护公众利益,防止公众被感染的目的,正因如此,李文亮在微信群中的提醒被外界称为是疫情的“吹哨人”。但因早期疫情症状不明确与权威机构对其定性尚未明确,李文亮选择在微信同学群发布预警信息,这既是出于提高信息被认可、增强辨识度的考量,也是在不确性的社会情境下防止信息失真后被传播的一种理性选择。
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受众群体对网络信息的认知与接受是有差异性的,会出现不同版本的、不同形式的网络谣言,引发谣言变异。美国学者克拉帕在研究网络谣言时也指出受众对网络信息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一方面因理性价值判断不同,另一方面受众者的年龄、经历与立场不同,也会影响传播信息的选择(22)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页。。同时,也要看到网络谣言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将一些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达成共识,他们得出的结论或产生的行为会比之前更加极端,形成群体极化,降低受众群体主动辟谣的意愿与社会信任水平。李文亮首次向外界发布新冠疫情的预警之后,起初的受众群体是其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大学同学,这些受众者成为首批预警信息的接受者。但注意的是,即使是具有专业性背景的医务同行也会受到预警信息的影响,个人在群体极化中容易失去理性,思想情感易受其他人暗示。既使李文亮在微信群里提醒在群人员不要外传,但这些首批的接受者还是将信息外传,以致出现二批、三批甚至更多的网络谣言受众群体,在此过程中形成谣言变异,再次扩大了网络谣言的社会影响力与复杂性。
当未经证实的网络信息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且这些信息可以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冲击现有社会秩序时,辟谣的直接管理者就会介入,这也是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发布训诫的直接动因。但因网络谣言传播的多渠道、多形式、复杂性,政府部门会采取分类治理的方式进行。就我国目前的谣言治理方式而言,政府会对网络信息本身的真伪做出澄清,而将其定性为网络谣言的行为即是表达态度的一种方式。对于正在传播的网络谣言,政府一方面会对发布者以训诫、警告等方式惩戒,防止发布者肆意发布其他形式的不实言论;另一方面政府特别重视网络信息传播平台的管理,通过明确网络谣言的平台管理准则,加强对传播媒介的监督,以阻止网络谣言的传播。这种平台式管理的方式被日常化之后也往往成为政府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手段,既可以起到预防网络谣言的作用,也能让网络平台承担起监管网络谣言的职责。而政府部门在劝阻社会公众不传谣、不信谣的同时,也会通过动员基层组织和借助专家解读等形式,让社会公众提高理性认识,防止群体极化与从众行为的产生。李文亮事件中,专家调查组、研究所、社会媒体的语话对社会公众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成为公众判定网络信息真伪的重要标准。此前 公安机关对李文亮进行训诫后,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与疫情临床表现的逐步明确,让社会公众认识到了李文亮首次在微信群中发布的预警信息是对疫情的一种正确、及时的反应,一时间对李文亮事件的关注与讨论进一步增强,引发政府信任危机。
四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分化的治理
李文亮事件反映出网络谣言具有虚假性与真实性的双重属性,且随着其属性结构与社会情境的变化两者会发生转化。为了提升网络谣言的治理效度,需要在把握场景事件、信息技术、行动主体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治理优化。
(一)建立重大事件“吹哨人”制度,合理回应吹哨人诉求
任何网络谣言都是对社会情境的反应,蕴含着真实性与虚假性信息,在对信息的真实性没有考察清楚之前,需要谨慎地对其定性。李文亮被外界称为疫情“吹俏人”,是因他是第一个体制内工作人员向社会发出预警,随后因其没有受到良好的保护被社会关注。鉴于李文亮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与网络谣言治理的复杂性,建议我国积极建立重大事件“吹哨人”(whistleblower)制度。“吹哨人”即是通过告密者、内部举报人揭发举报违法违规线索,其最早源于美国。当下社会分工日益精细,重大事件发生日益复杂,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开展调查与审计,越来越难见成效,在以后的工作中,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吹哨人”参与到重大事件预警与监督中,另一方面要做好对“吹哨人”的保护。就前者而言,不仅要立足于“吹哨人”制度的建立,完善举报的立法、举报渠道、调查跟进的配套措施、反馈情况等,而且要对吹哨人进行激励与救济,包括精神层面与物质奖励,做好吹哨人权利受损的补救工作。就后者而言,要保护好吹哨人及家属,确保吹哨人免遭被吹哨人报复,这是吹哨人制度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因为健全的吹哨人保护制度利于保障公民的监护权与知情权、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利益,加强政府监管与透明度(23)彭成义:《国外吹哨人保护制度及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42—54页。。
同时,还要注重“吹哨人”的回应,对“吹哨人”提出的举报或预警行为要及时、有效地跟进,避免因调查不清晰而损害“吹哨人”权利。现实中很多网络谣言的泛起是因为当事人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回应,致使传播者陷入悲愤引发恶意传播事件,而这也是李文亮事件获得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重点。一套良好的、行之有效的重大事件“吹哨人”保护制度可以在全社会内形成一种关注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共精神的氛围,每个“吹哨人”可以明确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且吹哨后可以获得相关部门的跟进与道义层面的奖励。
(二)完善信息发布渠道与机制,打造全过程现代信息技术链
网络谣言的滋生是因事件的事实依据不清晰,现有信息无法还原事件本身而引发,在真实性与模糊性间产生信息鸿沟。在李文亮事件中,公安机关辟谣失灵的根本原因是因网络谣言的信息传播力大于辟谣信息传播力,导致信息功能性与网络技术性的双重失灵。可以说,明确网络信息发布的渠道与机制,让真实、权威信息可以及时传送到社会公众,维护社会公众对事件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消除社会公众的疑惑心理,避免当社会公众的正当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猜疑既是网络谣言治理的基础,也是防止网络谣言认知分化的重要条件。实际的网络谣言治理要立足于社会公众,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方式,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需求设计不同的参与方案,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文本,打通社会公众自下而上的参与渠道,确保信息获得的权威性。同时,要明确重大疫情中信息发布机制,从网络谣言产生前的监测、传播过程中的阻断、终结后的问责都要制定明确的规范标准,必要时出台专门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信息披露意见》,将信息诊断、信息发布、处理过程、责任主体、奖惩事项做出详细解释。以事实证据为本,政府部门要注重信息话语权的抢夺,建立信息发布的梯度机制,根据信息内容、紧迫性、发布级别进行确定。
当网络谣言的信息传播力大于事件真实性的知晓率时,受“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影响(24)[德]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那些可以真实地还原事实真相,与谣言传播相反的观点会被淹没在大量的虚拟信息中,导致谣言进一步变异、分化。为此,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重点加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将区块链技术作为疫情管理的底层技术架构,引入“数据输入系统”“Gossip传播协议”“数字验证机制”为核心的区块链传播机制,明确信息发布源头、基础要件、传播路径、受众群体,减少对网络谣言的误判,有助于提升政府发布信息的整体公信力。
(三)以公共利益区分评判网络谣言,注重专业人员的群体意见
网络谣言的治理需要在明确何为网络谣言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这就涉及到网络谣言的评判标准。网络谣言的评判标准需要采取动态性、综合性的指标进行衡量,稍有不慎即可定性偏离,引发治理失效或辟谣失灵。李文亮事件经历了网络谣言的定性到网络谣言的纠正,体现出现有网络谣言评判标准存在一定问题。在笔者看来,评判网络谣言的首要标准是考察某一网络话语是否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重大疫情场域下的公共利益是化解利益冲突的理念先导,要充分考虑到事件涉及到的对象是谁、事件的影响程度、事件证据的充分性、事件处理的及时性四个层面,其中事件证据的充分性是关键。若某一重大疫情的对象很明确、事件影响程度也较大、事件处理及时,但事件证据不清晰,则该事件不宜过早定性为网络谣言。正如卡普费雷所言:“控制谣言的神奇秘方是没有的,只有对情况有了确切肯定的了解,才能做出诊断,提供建议。”(25)[法]让·诺埃尔·卡尔费雷:谣言,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3页。为提升评判标准的科学性,需要注重专业人员的群体性意见,尽管网络社会加强了不同领域的协作,但不同领域间的专业鸿沟仍然存在,需要在界定网络谣言标准时听取与之相对应的专业性意见,准确评判事件证据的充分性、事件的影响性程度。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网络谣言评判标准的公共性,也要在“公共人物” 理论下听取社会影响力大的党政官员、文艺明星、企业家、教育家的意见,寻找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公共人物”理论看来群体自由是与公共利益保持平衡的,且公共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优先性。这主要源于传统的自由哲学认为开放、自由的政治环境可以促进社会自治、民主及对真相的发现(26)郭春镇:《公共人物理论视角下网络谣言的规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58—174页。。但对于公共人物的重视程度仍要做出区分,对于那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人物需要在把握语话动机的基础上,采取实际恶意原则判定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是否构成网络谣言。这样,即可以实现网络谣言标准的科学认证,也有助于对公共言论的保护。
(四)促进多主体参与、协同,明确主体间权责利关系
网络谣言是技术赋权下话语形态的异化,通过主体间传播最终影响于人,作为网络话语主体的信息人成为网络谣言治理的直接对象,而治理效果的集中体现在信息人不信谣、不传谣。因其具有真实性与虚假性双重性价值,治理的重点之一就是防止将真实性话语定性为虚假性,损害信息人的合法权益。重大疫情下的网络谣言治理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与流变性,要及时对信息人提出的网络话语做出真实性论述,积极构建官方网络话语体系,提高政府处理网络谣言的能力,及时披露真实信息,防止网络话语权失衡引发辟谣失灵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但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是多方参与的结果,其治理仍然需要精准把握到不同传谣者的需求,做好真实性论证、资源共享、制度保障。利用网络“去中心化”优势,动员多主体参与,重视市场与社会力量融合,甚至有学者认为在网络谣言治理中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规制应该在市场机制失灵时介入(27)林华:《网络谣言治理市场机制的构造》,《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66—76。。且从国际谣言治理经验来看,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日本建立行业自律式的谣言治理方式,重大疫情发生后政府会责成网络管理协会、联盟团体在负责报道时也要承接起消除谣言的措施。网络社团作为与网络谣言一同生成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在专业性、持久性、客观性中的优势,通过与政府的项目合作、邀请协作、职能转移与委托授权的方式进行协同合作。社会公众不仅要通过理性认知提高自身辨识网络谣言与网络信息的能力,更要注重责任意识与自律意识的培养,避免从众跟风。
在动员多主体参与的基础上,要积极构建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相关主体为核心的协同治理结构,根据不同主体的组织优势将其纳入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明确各个主体在其中的权利、责任、利益诉求。特别是在明确权责利的基础上建立主体间议事协调与沟通服务机制,强化主体间监督与奖罚机制,跨专业协同机制,积极推进主体间合作。
五 结 论
网络化的信息传播已经成为影响社会交往与生活形态的重要方式。网络谣言是技术赋权下的一种话语形态,蕴含着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双重认知,且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流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辟谣失灵,引发新的治理困境。网络谣言治理需要在及时评判信息的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基础上做出针对性回应。第一,网络谣言的双重认知除了要考虑网络信息、发布者动机、传播媒体、受众群体这些属性因素之外,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环境和事件发展等因素,以及与个人情感的重要性、感受性融入其中。第二,防止网络谣言治理失灵的关键是根据事实依据的充分性及时调整治理策略。网络谣言的流变性很强,随着事件的发展网络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辟谣机构要因时、因地调整治理策略。第三,网络谣言的双重认知治理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重视源头治理与技术治理的积极作用,要防止治理时的“一言独大”,促进多主体间的协同参与。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网络谣言是公民自由发表言论的一种话语形式,在治理过程中要防止对公民自由言论权的过分规制。此前已有学者认为现有的行政规制存在网络谣言打击范围过大,规制方式的合法性存疑(28)张新宇:《网络谣言的行政规制及其完善》,《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63—69页。。李文亮事件的发展从侧面反映出在自由与管制之间,网络谣言治理的底线在何方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判定其言论是否有违客观事实,符合客观事实的网络言论应该受到保护与重视,反之需要做出持续性跟进调查,及时识别那些为满足个人私利的虚假信息。另一方面还需评判其言论是疏忽还是蓄意所致,有些网络谣言的滋生可能因其发布者疏忽所引起的,既要客观允许此类话语的存在,也要加强治理,防止带来更大的社会冲击。在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时,除了要考虑事件发生的依据、重要性、影响力等因素,还要重视社会情境的变化,体制环境的约束,形塑综合性、动态性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