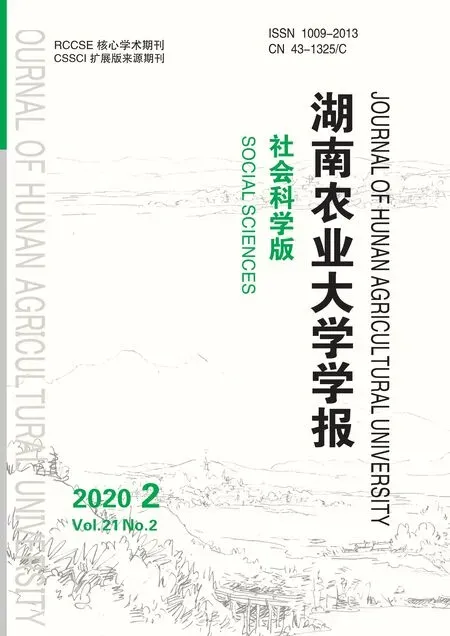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风险及其应对
唐玲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风险及其应对
唐玲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质在于从传统的“法律报应”走向“法律激励”,具备法规范意义上的积极价值。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时,需考量其是否带来刑法体系功能紊乱及罪行关系结构失偏的潜在风险。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适用时需要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并从实体规定、权利保障以及权力监督等方面着手,化解现阶段适用该制度所带来的风险,为刑法正当规制职务犯罪案件提供规范性框架和制度保障。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风险;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随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有序地展开。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从立法层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确立,至此,基本完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提出到实践再到法律确认的过程。作为刑事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因此也成为理论界普遍热议的话题。虽然现阶段学界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颇具成效,但将其与具体案件类型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结合起来研究的却寥寥无几,导致理论与实务之间严重脱节。事实上,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问题,理论研究应具有指导性与前瞻性,为制度的实践运用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引。基于此,本文拟立足于法规范学的视角,围绕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对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的有效治理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与实施有所裨益。
就我国《刑法》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定来看,主要体现在自首和坦白的规定中,且自首和坦白被认为是认罪程度较高的两种表现形式[1]。《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紧接着《刑法》第67条第3款又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该规定为自首与坦白的“从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针对职务犯罪案件,我国《刑法》第383条第3款载有明文:“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这一规定意味着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规定了特殊的从宽处罚制度,其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可以被看作是行为人认罪的表现。而这些规定相比《刑法》第67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的规定而言,其从宽幅度更大[2]。可见,立法者为了鼓励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尽早认罪认罚,将认罪悔罪发生效力的阶段限定在提起公诉以前,且突破了酌定情节不能减轻的限制,使得认罪和退赃挽损的从宽作用更为突出,这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意旨所在。
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刑法赋予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来获得裁判量刑的优惠,是否会给刑法既定的体系带来冲击从而造成刑法体系功能的紊乱?同时,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形下,主张与职务犯罪者进行合作量刑,是否会与罪刑法定的原则相悖呢?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在于解决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有限的困境,那么在承认司法效率与公正的同时,又是否会出现过度适用、膨胀适用而导致的法益保护不均的现象?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价值进行正确审视,然后找出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再去寻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限度与原则,探究其实现机制,从而准确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功效。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价值
根据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与立法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一旦实施职务犯罪行为便不可逆转,职务犯罪者甚至再难以顺利地回归社会。据此,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意味着以职务犯罪行为人之犯罪后的认罪认罚行为所带来的法益恢复作为从宽处罚的条件。亦即,职务犯罪者在犯罪后的这种“合作”是以实际行为来弥补其实施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侵害与损失,因而具有特殊的法经济学意义[3]。
法经济学的重要分析维度在于成本与收益,即强调基于保障法的安定性基础上,考虑惩罚犯罪的经济性效益既是必须的也是理性的。事实上,职务犯罪案件同时具有法益侵害的规范违反性和可补偿性。规范违反性意味着职务犯罪者以犯罪行为侵害国家、社会的合法权益,就会当然受到来自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处罚,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之正当性的法治根基;可补偿性是指职务犯罪案件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后果是可以通过罪后的行为予以努力补偿的。申言之,通过对职务犯罪者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两得其利,反之则两受其害,这就为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可实施的空间。从法规范性的角度来看,由于法的规范性包涵互惠互利维度下的成本降低,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意味着职务犯罪者与国家由“对抗”走向“合作”,不仅降低了国家惩治职务犯罪案件的成本,更是及时弥补了由犯罪带来的法益侵害损失,具有重大的法经济学价值和意义,是法律现代化的一种择优路径选择。由于法律的价值追求具有多元化的特质,面对同一问题时选择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多元价值的平衡,这就需要从功能判断出发,选择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实现方式,此亦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根据法经济学的思想,人都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总会追求限度内的效用最大化。法律通过设定约束条件——建立个人行为准则——改变个人偏好——协调个人预期的方式,最终达到结果的协调与衡平。具言之,一项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引导个人行为,而不是强制,法律的有效实施必须以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为前提,法律必须具备这种激励与约束的特质[4]。具体于职务犯罪案件而言,当且仅当一项法律下认罪认罚不能成为个人实施职务犯罪之罪后行为最优选择时,这项法律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惩罚规定是无效的。正是基于这个层面的考量,可以将法律理解为一种激励机制 (incentive mechanism),即“法律制度可以作为有秩序地变化和社会控制的工具”[5]。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必须对个体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而刑罚减轻作为激励的形式之一,与刑罚应罚性相对应,构成个人行为时需要进行考量的一对双向度、异质性的对立思想,惩罚的轻重程度、力度大小均会对个体是否选择认罪认罚行为产生效用。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的经济性是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合理配置实现的[6]。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若权力与权利的分配天秤越倾向于国家,则职务犯罪行为人罪后“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这种分配方式忽略了行为人的个人偏好,未充分赋予其参与司法的合理方式,只会带来职务犯罪行为人在衡量利益得失的基础上“对抗到底”,最终不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侵害法益得不到弥补,甚至还可能出现更多的司法不公现象。因此,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质就是权力与权利的再配置,行为人认罪认罚所带来的“从宽”结果有利于激励犯罪行为人选择与公权力进行“合作”,激励行为人以自己的行为积极弥补损失、争取宽大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基本上符合法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实体法上设定了职务犯罪者的行为规范体系,根据刑法的明确规定认定职务犯罪案件的成立标准以及处罚轻重,尔后通过程序法设定职务犯罪者罪后的认罪认罚行为,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从宽”处理,然后再以职务犯罪者罪后积极的认罪态度来恢复受损的法益,最终实现法的安定性。可以说,从“对抗”走向认罪认罚的刑事司法“合作”,带来了职务犯罪案件惩罚模式的改变与创新,实现了职务犯罪案件领域国家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价值平衡最大化,因而,从“法律报应”模式迈向“法律激励”模式,是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突破与改进。
三、制度检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潜在风险
在探索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范畴时,既要看到积极因素,也应考量其消极影响。因此,需要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存在动摇刑法根基的潜在风险进行审思与斟酌。笔者以刑法体系为标杆,从刑法体系的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两个层面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行剖析。
1.规范外风险:带来刑法体系功能的紊乱
规范化体系决定着刑法具有稳定性、科学性与正义性,这也是刑法发挥犯罪预防功能、树立社会正面影响力的必然需求。如果职务犯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忽视了刑法的稳定性、科学性与正义性,则必然会带来刑法体系性功能紊乱的后果[7]。
第一,破坏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刑法作为犯罪控制工具,其内部系统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虽然在面对社会重大变迁或改革时,刑法应当予以适度回应与调整,但仍需以原初设定为基础,以维护刑法体系的稳定性。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会面临刑法的稳定性担忧。刑法是对已然犯罪的惩罚,目前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至少在观念上显现出对犯罪的积极遏制性不足而消极惩罚性有余,带来刑法对社会秩序保护不力的风险[8]。就刑法体系稳定性而言,立法者通过法秩序维持、构成要件的明确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等来寻求刑法的稳定性。故而,为迎合刑事政策的社会性改革需求而提倡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可能带来案件适用上的经济效益,但却有产生刑法功能改变、国家权力失控等刑法稳定性之忧。
第二,危及刑法体系的科学性。刑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其内部应当协调一致。体系的科学性是刑法立法质量的保障,更是司法效果得以实现的前提。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高估计刑法的适用效果,而忽视其现实及潜在的风险,因而其科学性有所欠缺。就职务犯罪案件而言,我国采用职务违法处理与职务犯罪制裁的二元规范体系,强调法律之间的协同运作关系。因而职务违法处理与职务犯罪制裁之间不可任意混淆、替代或逾越,以避免规范体系内部职权适用的混乱,造成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9]。一方面,职务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刑法予以明确规定,该标准亦是监察人员办案的依据所在。当然,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监察人员可以考虑在定罪量刑的标准内是否赋予行为人一定的从宽合作空间。因而,对职务犯罪者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意味着定罪量刑标准的降格,更不是对定罪量刑标准的僭越。另一方面,科学的刑法体系强调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刑法不应逾越干预的界限,不能过分依赖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扩张刑事司法圈。事实上,过度强调刑法打击的廉价性与象征性,会导致大量职务违法类案件升级为职务犯罪案件,从而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带来刑事司法的不能承受之重[10],同时也会带来选择性司法的恶果。申言之,针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者可以塑造刑法的积极、民主形象。然而,倘若过度依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分强调职务犯罪者的自主合作意识,不仅不能确保刑法的科学性,反而会致使刑法滑入道德的陷阱之中。
第三,弱化刑法体系的正义性。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是借助刑法的社会属性而对社会生活进行适度的干预,这种干预若逾越界限易产生“崩坍”的秩序。从宏观上看,一旦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超出一定的负荷,就不再只是展现刑法的正义,而是通过认罪认罚的“合作”来替代刑法的正义。从微观上看,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会带来量刑体系上的“平均正义”缺失。意即,通过采取“合作从宽”的方式来强化职务犯罪者的人权保障,这会带来罪刑失衡的责难,造成认罪认罚者与不认罪认罚者之间的量刑“失衡”。事实上,刑法的处罚效应不只是追求刑法调整的短期效果,更在于其是否能发挥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作为刑法适用的产物,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代表的是一种法文化现象、一种非规范性的评价,因而所带来的过度效应可能会使民众对司法权威产生质疑,冲击法律的稳定性根基,最终造成严重的法律适用问题。
2.规范内风险:导致罪行关系的结构失偏
刑法并非无所不能,通过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惩罚职务犯罪案件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之双赢局面,这可能会带来立法的左支右绌,导致解释的价值失偏。
一方面,从宽的功能取向对冲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近现代刑法的“帝王”原则,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张国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合作,具有忽视罪刑相适应原则下的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定位,从而导致罪刑相适应原则被颠覆的风险。具体而言,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安全防护网被突破,从本质上根源于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带来的量刑从宽问题。其一,自19世纪以来,因人身危险性概念的引入,各国立法也开始注重对犯罪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的考量[11]。由此,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开始凸显。从人身危险性来看,仅通过认罪认罚的行为表现来判定犯罪行为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并不具有确定性,且其罪后的主观态度更不能仅以是否认罪认罚来决定,这样的“从宽”不仅会带来恣意量刑现象的产生,还会使得认罪认罚者与不认罪认罚者在量刑上的绝对失衡。从主观恶性来看,认罪认罚行为仅代表职务犯罪案件人的罪后态度,并不能反映其犯罪时的主观罪过及其程度,因而不能将其作为评价犯罪人主观恶性大小的维度。其二,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激励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更早的阶段答辩有罪,以便提高诉讼效率。在英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早期答辩有罪,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量刑折扣[12]。该做法后来遭到普遍批评而被废除。因为重罪犯罪人通过答辩有罪就可获得较低的量刑会严重损害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与信心。刑罚应受责任大小的约束,差别量刑的主要标准应当是犯罪行为人的罪行及其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程度,过度放大刑事司法经济效应的价值追求,赋予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过大的量刑折扣,这与对拒绝认罪认罚、坚持完全审判的行为人加重量刑的本质是一样的,同样都会造成裁判结果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严重悖反[13]。亦即,相对于通过认罪答辩获得量刑折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那些坚持无罪辩护并选择普通程序接受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获得量刑的从重处罚,这与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完全相背离。而且,过大的量刑折扣还可能刺激无辜者答辩有罪,易造成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14]。
另一方面,价值错位导致从宽适用的膨胀。刑法既保障自由又限制自由,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是国家管控权在刑法领域的延伸,如果缺乏有效规范,刑法就会面临危险的处境。从法理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带来新的社会风险与安全需求,使人们对于犯罪本身及控制犯罪产生了新的认识,刑法需要改变以往刑罚权单向度、冷冰冰的对抗立场,转向经由国家的自由。而对于维护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安全的刑法期望又使得集体法益的重要性被逐渐凸显,在某种意义上,侵害集体法益就等于对国家权力的侵害[7]。从这个层面来看,刑法倾向于通过集体法益的强调与保护以扩大刑法的适用能力,然而,由于集体法益概念的内涵过于抽象化,致使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会过于强调个人法益的保障,而忽视集体法益的考量。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所有试图针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努力,都必定会把刑法对犯罪的控制变成一种国家与犯罪人合作协商的管理模式,刑法功能由此体现了经济效益的价值实现与个人法益的保护。就此而言,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于强调法的经济效率与个人法益,而忽视集体法益的保护,难免会出现过度适用、膨胀适用的风险。
四、应对策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规范适用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原则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确保刑法对法益保护的位阶性,以化解现阶段带来的刑法风险,为刑法正当规制职务犯罪案件提供规范性框架。
1.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源于古老的报应刑论:即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惩罚轻重[15]。该原则强调刑罚必须和犯罪的客观危害性相当,贯彻等质报应之思想[16]。但是,职务犯罪案件行为人罪后的“认罪认罚”并不是犯罪行为的危害本身,只是一种罪后的行为表现,不能成为刑罚的等质要素,因而不能超越刑法对职务犯罪案件之量刑的实质性规定。虽然现阶段,随着司法理念与司法方针的变化(如恢复性司法理念、教育改造方针等),会对该原则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以及作比例上的协调,但是任何制度改革与推进均不能以突破罪刑相适应原则为代价,在原则适用的主次顺位上仍应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红线要求。亦即,调整性的法理与原则不能偏离罪刑相适应原则而适用,其只能作为微调性的补充而存在。
一方面,职务犯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刑事司法制度对于公正的追求。职务犯罪案件行为人罪后的认罪认罚的确能反映其具有真诚的悔罪态度,因而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能较好地符合犯罪预防目的的刑罚论要求。但是,英国刑法学家威尔逊曾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很多因答辩有罪而获得减刑的被告人而言,他们对于这种减刑的认识只在于法律对于那些选择完全审判的人的一种强加的惩罚,就被告人来说,如果因此感到不公正,只会导致他们更难改过自新[17]。因此,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以防止量刑失衡、裁量恣意等现象的产生,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另一方面,职务犯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路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实质是以职务犯罪案件行为人罪后行为表现——认罪认罚——实现刑罚从宽、程序从简的处理,以实现正义基础上的效率观。因此,在对职务犯罪者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应当同时兼顾正义与效率,以实现司法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据此,对于犯罪行为人之量刑以及有责性程度的降低就不能只为了实现刑法的经济效益,而需要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实现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兼顾司法正义与经济效率。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既能够以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来实现其经济效益,又能够通过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坚守来保证其正义价值的存在。此外,拓展到程序处理上,需要严格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规范标准,确保认罪的自愿性与规范性,通过程序规范实现认罪认罚的理性[11],防止虚假认罪,避免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行为成为刑事司法协商的讨价筹码。
2.法益保护位阶原则
刑法保护的法益分为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法益的本源性价值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集体法益的核心则是维护秩序。因而,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在形式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且通常被置于二元对立的状况中[18]。据此,为维护刑法体系功能的正常运转,当刑法中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保护出现竞合或冲突之时,就应当着重注意法益保护的位阶性,按照轻重、主次关系对法益形成阶梯式保护[19]。
法益保护原则是刑法实现其目的的工具,价值导向逻辑使法官从形式推理转向借助价值衡量进行判断的实质推理,从而为法益保护的位阶性提供了存在的空间。法益保护的位阶性要求刑法对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区分,明确法益之间的主次顺序关系,这也表明了法益保护位阶性的规范特征:一是刑法保护法益的轻重关系反映出不同法益之间的比例问题,体现出刑法评价意义上不同法益之间存在的次序与轻重。二是法益保护位阶性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重要维度,维护秩序、保障自由是刑法目的的法理解读,而法理所表现出的深层次内涵是法益保护。但是,法益的保护不仅仅体现为对法益侵害的笼统保护,而且还体现为针对不同等级法益的多元保护逻辑。因此,对法益保护位阶的重视有助于刑法目的的有效实现。毋庸置疑,法益保护原则的上述理念同样体现在刑罚的妥当性上。
关于职务犯罪案件侵害的法益素有“廉洁性说”“不可收买性说”“公正性说”等观点,但不管是哪种学说,其实质都是一种集体法益[20]。然而,就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其法益保护的价值理念却偏重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法益的保护。亦即,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建立在“为了限制刑罚处罚而存在”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制度,其价值导向就是为了实现个人法益的保护原则。不难看出,这种立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法益保护的理论建构没有认真考虑法益保护的位阶层次性,亦没有细致地区分各法益在评价位序上的差异,这可能会导致刑法对法益保护的顾此失彼,进而影响刑法终极价值的实现。事实上,刑法体系绝不仅是个人法益保护机能的“独享天下”,这就要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机制必须与法益保护的位阶性形成合理的对应关系,保证量刑比例的均衡,实现“重罪重打击、轻罪轻打击”策略。而要对法益保护的位阶排出优位序列,首先就要明确刑法保护的重点与方向,这不仅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更是实现法正义性的基础。据此,在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发生冲突或竞合时,应该首先强调作为“恶”的犯罪人所侵害的集体法益保护优先于职务犯罪人的个人法益保护,这意味着在此类案件中出现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发生冲突或竞合之时,应当强化一种国家秩序保护优先的解释或者严格限制绝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释。因为职务犯罪行为首先是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集体法益,且此类法益涉及广大民众的普遍利益与国家利益,因而应当在法益保护位阶上予以强化。
一言以蔽之,现代刑法重视刑事政策的重要影响,不再只强调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单一认证逻辑,而是从犯罪治理出发,对案件中的诸多法益予以兼顾,这就会带来犯罪与刑罚模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仅不应当违背法益保护原则,而且应当体现刑法对法益保护的阶层化与精细化,以实现刑法处罚的妥当性[21]。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规范适用的实现机制
虽然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一系列的潜在风险,但可以在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完善相关措施来减少职务犯罪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从实体规定、权利保障、权力监督等多方面着手,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规范适用。具体而言:
第一,针对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制定相对统一且具体的“从宽”量刑幅度。从纵向角度来看,该量刑幅度的设置应当综合考虑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诉讼阶段,即应当根据认罪认罚作出的具体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作出不同的量刑幅度标准。从横向角度来看,具体应当综合考虑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罪行轻重、退赃比例、悔罪程度等情况规定从宽的具体幅度[22]。只有在科学考虑上述诸多影响从宽量刑幅度因素的基础上,设置统一的、具体的从宽量刑标准才能有效保证法官在认定职务犯罪认罪认罚从宽时的具体刑期,以增强法律规定的明确性与具体性,避免法官从宽判断的恣意性,防止因认罪认罚是否从宽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刑法体系功能的紊乱,保障刑法体系的稳定性、科学性与正义性,并继而解决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的模糊性所带来的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击,确保刑法能够正义地对待每一个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人。
第二,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现阶段,在我国认罪认罚刑事诉讼体制改革以及高压反腐的环境背景下,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职务犯罪案件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所在,也是确保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正确量刑的前提与基础。虽说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在于从“法律报应”迈向“法律激励”、从“对抗”走向“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就会因此受到克减。相反,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的权利保障才能真正使其具有与控方进行平等合作的“筹码”,以促进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整个诉讼流程能够得到良性的发展,减少因程序性问题而带来的对实体适用的负面影响,为职务犯罪案件能够在刑法规范的框架内合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程序性契机和基石。据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办案机关的多方告知、全程留痕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权,确保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知性;保障律师的充分参与,扩大值班律师队伍,发挥律师的说理作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效辩护权;此外,还可以基于被告人上诉的真实动因进行分类,设置有条件的上诉权,以防止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行为人的上诉权受到不当的限制等等。
第三,建立诉讼全流程的权力监督机制。即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所有诉讼流程中建立监督机制,以促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相关工作均能够在合理的监督之下进行。具体而言:其一,在侦查阶段,由于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权统一由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机关一跃成为决定职务犯罪案件是否进入司法流程的掌控者。但根据《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不仅无法准确确定律师是否能够介入监察程序,而且无法断明其作为法定监督机关是否能像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一样对监察程序进行有效监督。据此,监察程序在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时对于证据合法性、证据真实性等的监督就只能依赖于其内部系统的自我监督。因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察程序才能从源头上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规范适用。据此,笔者认为,应当以立法形式确立检察机关对监察程序的监督作用,并明确律师介入监察程序的合法性。监察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并听取律师的意见,以规范国家监察权力的行使,从源头上提高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质量,继而为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安全、科学与正义提供前期的制度保障,降低因前期适用不当而导致的后期诉讼流程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冲击力度。其二,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除了要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当事人监督、陪审员监督以及其他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之外,尤其要充分发挥律师的监督作用,通过保障律师的有效辩护,使其不仅能够有效对抗控诉,而且能积极影响法官对于认罪认罚合法性的正确认定,从而为被告人获取合理的从宽量刑,确保法官既不受控方强势的干扰,也不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定从宽”的影响,继而能够在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作出正确、合理的量刑,以保护刑法体系功能的正常运行以及罪刑关系结构的合理与科学。
[1] 王瑞君.“认罪从宽”实体法视角的解读及司法适用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6(5):112.
[2] 李仲学,宋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应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J].福建法学,2017(2):68.
[3] 姜涛.刑法中的犯罪合作模式及其适用范围[J].政治与法律,2018(2):96-97.
[4] 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3):101.
[5] 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M].李琼英,林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1.
[6] 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工具[J].法学研究,2004(4):134-146.
[7] 姜涛.社会风险的刑法调控及其模式改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9(7):122-125.
[8] 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5.
[9] 姜涛.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重大问题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02.
[10] KADISH S H.The crisis of overcriminalization[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67,374(1):157-158.
[11] 吕泽华,杨迎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基、困惑与走向[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3):132-138.
[12] JACQUELINE Beard.Reduction in sentence for a guilty plea[OB/EL].http://researchbir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SN05974,2017-11-15/2019-07-09.
[13] 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J].法学,2016(10):102.
[14] BARKOW R 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criminal law[J].Stanford Law Review,2005,58:1034,1047-1049.
[15] [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M].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41.
[16] 陈兴良.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5.
[17] [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M].刘立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37.
[18] 孙国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J].法学研究,2018(6):37.
[19] 张平华.权利位阶论—关于权利冲突化解机制的初步探讨[J].清华法学,2008(1):49-65.
[20] 马春晓.受贿罪构成要件与法益关系的检视与展开[J].宁夏社会科学,2019(2):63.
[21] 姜涛.基于法益保护位阶的刑法实质解释[J].学术界,2013(9):102-111.
[22] 谭世贵.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视角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法学杂志,2016(8):21-22.
The applicable risk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in duty crime cases
TANG Ling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he essence of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in duty crime cases l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legal retribution" to the "legal incentive", so it has the positive value in the sense of legal norms. However, when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in duty crimes, we also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it brings the potential risk of the dysfunction of criminal law system and the deviation of criminal relation structure. Therefore, in the application of duty crime cases,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needs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uiting crime to punish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and start from the substantive provisions, rights protection and power supervision, so as to resolve the risks brought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at this stage, and provide normative framework and system guarantee for criminal law to regulate duty crime cases properly.
duty crime case; leniency on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risk; response
10.13331/j.cnki.jhau(ss).2020.02.006
D915.3
A
1009–2013(2020)02–0041–08
2020-02-2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137)
唐玲(1989—),女,安徽桐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责任编辑:黄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