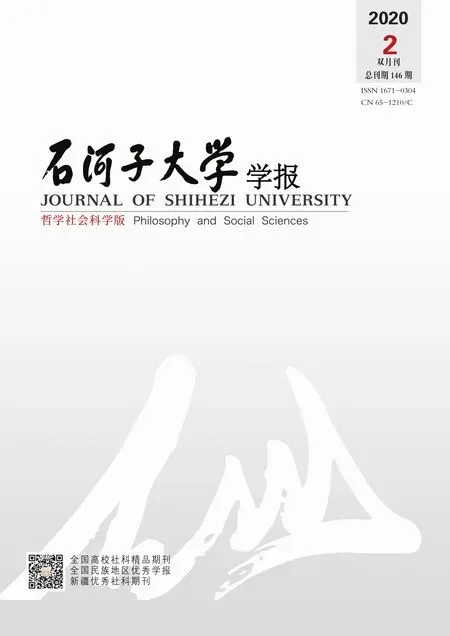作为一种虚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韦伯劳动天职观
——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批判对象
张卫良,何秋娟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推动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至少在工作的时候去除掉不断计较怎么样才能最悠闲最不费力又能赚到同样薪水的想法,并且把劳动当作绝对目的——“天职”来从事的心态[1]37。简言之,就是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1]40。劳动天职观是其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内核之一。基于劳动天职观,韦伯顺理成章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自发性地产生了自由工人,自然性地进行了资本原始积累,工人自主地承担了超额劳动。基于劳动天职观,资本主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们争做上帝选民的结果,是人们的社会本质的必然体现,也是人们精神与肉体完美统一的活动;资本主义则是在人们对自己本质占有中牧歌式向前发展的。劳动天职观绘制了一幅令人炫目的资本主义劳动的美好图景,在这幅美景中,人们当然看不到血腥、看不到“羊吃人”的悲惨,看不到恩格斯所亲历和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赤贫状况。如果工人能自发地把劳动当作一种天职,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进行“圈地运动”?如果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能够自行筹措到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货币额,地中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何还要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地开辟新航路,进行殖民掠夺?如果工人能够自主地承担超额劳动,为何还有世界著名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和自发地捣毁机器的罢工举动?而这正是我们披露韦伯劳动天职观虚伪性的切入点。
一、入世禁欲主义是一种先验性的宗教教义,劳动天职观理论依据具有虚幻性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介绍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宗教的禁欲主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韦伯的论证逻辑是新教教义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进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真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吗? 显然这是韦伯为资本发展所创设的一个虚假依据。宗教作为一种先验性的世界观,并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不是“创世主”创造的,而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460。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3]701。因而,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2]1,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的生活方式和职业理念,当然也不是宗教创造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立足于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决定生活态度”是颠倒的历史
韦伯通过分析天主教教徒与基督新教教徒的职业倾向,得出天主教教徒具有留守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欲望,而基督新教徒则倾向于流向工厂。前者表现出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后者展现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韦伯指出造成两者不同职业倾向的根源在于两者所信奉的教义不一样,即宗教信仰决定生活态度。天主教强烈的“超尘出世”以及其最高理想所显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导致其信奉者对于此世财货不感兴趣[1]15。而基督新教更倾向于融入世俗的盈利生活,将世俗职业义务的履行作为讨神欢喜的唯一之道。在考察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因信奉的教义不同而导致世俗的职业倾向不一样的基础上,韦伯进一步指出,生活态度的差异,必须从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质当中来寻求,而不单是只求之于一时处在历史——政治情况[1]14。韦伯发现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民族里,几乎找不到“职业”以及相类似的表达字词,这样的字词却存在于所有基督新教占优势的民族里。因此,韦伯断定生活态度的差异是属于何种宗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即属于何种宗派似乎不是经济现象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但很显然韦伯的断定是在刨除天主教教徒与基督新教教徒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基本历史——政治情况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
韦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视为天真的唯物主义,认为职业取向的不同是宗教教义差异的体现和结果。基于对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教徒生活态度的考察,历史给出的结论却是相反的。路德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天主教严重阻碍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天主教会的奢靡、腐败和对钱财的搜刮,严重影响到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尚未宗教祛魅的时代,要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对宗教进行改革,由此路德宗教改革应运而生。基于历史的纬度,宗教教义影响到教徒的生活方式是必然的,但将什么作为宗教教义、宗教改革如何进行等却是依据社会发展需要而定的。宗教改革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教教义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反映。因此,“宗教信仰决定生活态度”是割断人们社会生活因果关系链条,把作为中介的宗教当成终极原因而曲意颠倒历史,以达成用宗教美化和掩饰资本生产现实丑陋的目的。
(二)基于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比较,劳动天职观的道德意义具有人为性
首先,“称义说”到“预定论”的转变,暴露了上帝假说的人为性。加尔文教派是促使路德的天职事业得到具体发展的推动力量。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派一个很大差异在于对上帝恩宠的先验断定上,即“预定论”与“称义说”的差异。路德派认为上帝的恩宠是可能丧失的,并且也能借助悔改谦卑与虔诚信赖神的话语和圣礼来重新获得[1]81,即人是神力的容器,恩宠是通过体验得到的。而加尔文派却信奉上帝“预选说”,即恩宠状态是上帝预定的,是不能改变的,人是神力的工具,一部分永生,另一部分人必然永死,这既不能通过圣礼来改变,也不能通过获得他人或者神的帮助得以改变。那么,确证自己的恩宠状态就成为加尔文派教徒最重要的事情,宗教不安抑或焦虑就是恩宠处于未被确证的状态。与天主教的救赎可以借助个别的慢慢积累而成的善功不同,加尔文教的恩宠状态的确证需要通过系统的自我检视才能形成。事实上这种救赎方式是自己“创造”的,即加尔文教徒自觉自己是神的战斗工具,世俗的职业劳动被视为消解宗教不安的适切手段。然而,“称义说”到“预定论”的转变、恩宠状态由依靠体验式的方式得到向依靠劳动确证得到的转变,都意味着宗教教义是可变的,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历史性创造,是用来印证和解释现实的,而不是规定现实的,以其作为理论依据是不可靠的。首先,既然宗教教义是可变的,那么宗教教义变的依据是什么?是上帝的主观意志,还是人的主观意志?如果是上帝的主观意志,那么上帝关注的应该是世人对待恩宠的态度,而不是以何种方式去确证是否处于恩宠状态,体验式抑或是通过劳动确证,对于上帝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上帝无需费尽心思进行改革。其次,“称义说”是通过主体的内心体验来确证恩宠状态,“拣选说”是通过主体参与俗世的劳动来确证自己的恩宠状态,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恩宠状态的确认都必须经由主体的参与,由主体来完成确证。因此,恩宠状态与否,并不是基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基于人的主观意愿,需要俗世的人来完成。至于采取何种方式来确证恩宠状态,则也必然是依俗世主体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的。
其次,“出世禁欲”到“入世禁欲”职业观的转变,自证了宗教教义的人为性。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新教最大的变化是摒弃了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与“劝告”的做法,转而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依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1]54。由此,也就赋予了俗世的职业生活以道德的意义,这也是路德宗教改革影响最深远的一大成就。虽然天职思想亘古有之,但是将世俗职业里的义务履行作为评价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却是宗教改革开启的。换言之,天职观的俗世道德意义是宗教改革人为赋予的,而不是自古就有的,更不是上帝预先设定的。天主教的“出世禁欲”是服务于教会敛财的需要,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是服务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教义只是现实需要的反映,什么被设定为禁欲的内容则是人为的,而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三)基于“为事不为人”的职业性格假定,资本家敛财与上帝拣选说自相矛盾
首先,“为事不为人”是服务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职业性格。与天主教的禁欲不同,基督新教的禁欲“封起了修道院的大门,转身步入了市井红尘,着手将自己的‘首尾一贯化’的方法论灌注到俗世的日常生活里,企图将之改造成一种在现世里却又不属于俗世也不是为了此世的理性生活”[1]146。这样,上帝拣选说驱动其教徒在俗世生活中形成的在此世遂行天职却不在此世享受的理性生活的观念,就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中“为事不为人”的职业性格的直接理论来源,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入世禁欲主义提供了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为事不为人”的职业性格也刚好契合了资本积累的需要。
其次,“为事不为人”的职业性格只约束工人,不约束资本家。人为事业而活,通过在俗世工作中遂行天职,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享受,这是确证自己被上帝拣选的唯一方式,但是这只是赋予工人的职业性格,是资本对工人和工人的生产劳动所作的异化规定,而非针对占有者——资本家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就越贫穷,他们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就越强大[2]51。马克思进而指出了这个异己的存在物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事不为人”的职业性格在工人这里表现为其本质外化、异化,而在资本家那里则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1]6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的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等的积累[3]290。基于资本主义财富两极分化的事实,资本家自始至终都在敛财,即是在为私为己,而不是为事为社会。资本家不劳动,但却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过着食利者的生活。基于上帝拣选说,确证自己是上帝拣选的子民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劳动当作一种天职。但事实上,工人在劳动之中得到的并不是恩宠的体验,而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者其他强制一停止,他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54。相反,工人的劳动却给资本家带了享受和生活的乐趣,资本家是以不劳动或远离生产劳动而获得了上帝真正的恩宠,成为了上帝的选民。资本家不劳而获的享受状态与工人劳而不获的异化状态都在用事实证明上帝拣选说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二、“资本主义精神”支配“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
韦伯基于宗教先验主义,基于加尔文教上帝拣选说提出了劳动天职观,同时认为生活态度是由宗教信仰决定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占主体的民族会因生活态度的不同而出现不尽相同的经济形式。因此,韦伯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发展,凡是资本主义精神觉醒的地方,就能自行筹措到资本主义运行所需的货币额,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最合适的组织形式等一系列论断。韦伯的精神先决论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现实,而试图将其变为一个以精神为动力或在精神支配下的存在和发展,其目的是否定它的经济事实和掩盖它的现实残酷性。这一论证逻辑是典型的黑格尔式的世界模式论,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统一性,一旦存在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了[4]417。存在成为世界的统一性,就将物质性从世界的统一性中成功地剥离出去了。
(一)以唯灵论来证明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一性,把人的历史变成了神的历史
韦伯论证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精神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劳动天职观与入世禁欲主义都是直接从基督新教教义特别是加尔文教义的上帝预选说中推导出来的,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换言之,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劳动天职观”的正义性提供了宗教信仰的支撑。韦伯不仅仅是从时序性的角度,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借助具体的实例来支撑其观点。其既有正面的例子,如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有反面的例子,如美国南方没有像北方那样废除农奴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南方的资本主义精神远远处于尚未发达的状态等。
既然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源于宗教教义,那么问题是宗教教义又源自何处,宗教教义是什么的产物?是思维本身的产物,是上帝创造的,还是在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韦伯自然会认为是上帝的产物,是先于世界存在就已经久远地存在了。既然是先于世界存在而存在,那么上帝为何要对教义进行改革,上帝又是以何种方式对教义进行改革的?这些都是韦伯无法在现实中予以论证的,因此他就直截了当地把一个叫作上帝的东西硬塞给了自然界[4]415,用一种唯灵论的方式来搪塞一切现实问题,用上帝的光辉来覆盖现实的黑暗,用灵魂的超越来医治肉体的痛苦,从而把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因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粉饰成因蒙受上帝的恩宠而自觉把劳动当作是天职的宠民,最终将资本与资本家合谋创造的工人的异化历史变成了上帝对子民的预先安排。
(二)用唯意识论来证明资本主义精神的扩张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货币,劳动成为精神的奴仆
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运作的手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是马克思指出的积累资本主义发展的货币量,而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问题。凡是资本主义精神觉醒并且能够发挥作用之处,它便能自行筹措到所需的货币额来作为运作的手段,反之则不然[1]43。韦伯认为时间、信用、勤劳和节俭都是美德,而之所以被称为美德,是因为对积累财富有用,即具体有用时才是美德。资本主义精神在扩张的过程中能够通过美德的传播和教育,在革新的过程中赢得客户与劳工的信任;能够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灌注,形成资本主义的秩序;能够使处于这个秩序之中的个人奉行其经济行为的规范,把劳动当作一种天职来奉行;能够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来形成“为事不为人”的职业性格,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财富。这样,资本主义精神通过营造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宇宙,将个人纳入其中,对其进行天职思想的教育,就能为资本主义发展筹措到运行所需的货币额。这一论证的美妙就在于资本积累是一个精神活动过程而不是被剥夺的工人劳动,劳动只是精神的奴仆,是服从精神的结果。抽出物质生产活动的实然状况,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工人成了精神的化身而非剥削的对象。
唯物主义在强调“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的同时也肯定精神的力量,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2]9。但与唯意识论坚持意识是本质和基础不同的是,意识在唯物主义这里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通过物质来起作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所到之处,如果能掌握群众,不排除其有成为一种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的物质的力量的可能,但是历史事实是,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不过是使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成资本的过程,使直接的生产者转化成为雇佣工人的过程[3]291,资本所到之处无不充斥着剥削和掠夺。因此,单纯依靠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是不可能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物质力量。在资本主义精神旗帜之下的是残酷无情的剥削和掠夺,资本所到之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297。韦伯借助于唯意识论神秘化资本主义精神的力量是为了掩饰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但是这种拙劣的论证逻辑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和对现实的考证。
(三)赋予意识完全的自主性,资本主义精神自主找到了最适合的组织形式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扩张一方面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吸纳劳动力,传播天职思想,以自行筹措到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货币额;另一方面则是为自身寻求最合适的组织形式。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利得的心态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里找到了最适合的形式,而资本主义企业则在此心态上找到了最适合的精神动力[1]40。韦伯强调资本主义精神的主动性,其在扩张过程中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这种最适合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组织形式的产生,进而又为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有什么样的精神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态度,进而决定什么形式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
韦伯力证资本主义精神在传播过程中主动寻找适合的组织形式,是为了强调精神的自主性。然而,韦伯赋予资本主义精神自主“寻找”适合的组织形式的同时,也暴露了其理论的自相矛盾。首先,“寻找”的前提是存在。资本主义精神“寻找”适合的组织形式意味着这样的组织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精神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由此,精神先于存在的悖论就不攻自破了。其次,“寻找”意味着是精神“适合”组织形式,而不是相反。资本主义精神需要寻找适合的组织形式,意味着是具体的组织形式决定和支配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只有适合组织形式才能发挥其精神动力的作用。
综上,不管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还是赋予资本主义精神资本原始积累的物质力量,抑或是夸大精神自主寻找组织形式的能动性等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阵地,企图用一种无法验证的先验性的虚无来美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三、劳动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颠倒目的和手段的歪曲的劳动意义论
韦伯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劳动天职观,即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伦理的至善就是赚更多的钱,并且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受,因而劳动是一种天职,是人的目的。劳动是神意的安排,人生在世趁着白日做工是为了确证自己的恩宠状态[1]150。在韦伯看来,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劳动本身包含了人生的意义。然而,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劳动力产生的方式,我们不难看出韦伯的论证只是为掩饰资本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事实,是为了掩饰资本剥削劳动的事实,使得资本剥削合法化。
(一)劳动是对神意的服从,与靠禁欲来防止肉体享受的诱惑自相矛盾
韦伯在论证劳动是对神意的服从时,采取了正反论证方法。首先,韦伯从正面论述劳动是神的旨意,是上帝的安排。韦伯认为上帝毫无例外地为每个人安排好了一个职业,人们必须各司其职、辛勤劳动。人们在劳动中的获利行为首先是为了社会,其次是为了个人,总目标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劳动是神的旨意,是恩宠状态的确证。劳动可以使人在自己的职业里刻苦劳作,通过劳动对财富的追求则不仅是道德上允许的,而且也是神的命令。不劳动则是欠缺恩宠状态的表征。其次,韦伯从劳动是禁欲的有效手段,是一切诱惑的特效预防针[1]153,反面论述不劳动会贬损神的荣光。禁欲是基督教教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是指要睡得安稳,即对此世一切享受欲望的控制,包括财富的积累。而新教的禁欲主义虽然也包括对享乐的控制,但是却鼓励通过劳动进行财富的积累,即只积累财富,禁止对财富的占有。路德教派的禁欲主义比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还要强烈地反对追逐世俗财产,因为占有财产会最终导致懈怠,享受财产会最终导致游手好闲和屈从于肉体享受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劳动是一种天职的观念。劳动能够增耀神的荣光,相反如果不禁欲就会贬损神的荣光。
职业是上帝安排的,从正面论证了劳动是对神意的服从;劳动是禁欲的有效手段,不劳动会屈从于肉体享受的诱惑,从反面论证了劳动才能增耀神的荣光。韦伯正反论证看似合理,实则自相矛盾。首先,上帝为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职业与恩宠状态需要确证自相矛盾。基于韦伯的劳动是确证自己是上帝拣选的子民的唯一尺度的假定,上帝为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职业,意味上帝赋予了每个人劳动的权利,那么每个人都是上帝恩宠的对象。既然上帝为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职业,那么恩宠状态就无需确证。其次,劳动是对神意的服从与禁欲自相矛盾。禁欲的对象是屈从于肉体享受欲望,既然劳动是对神意的服从,那么为什么人还有如此强烈的肉体享受欲望,还必须通过劳动来对这种欲望进行抑制?如果劳动是对神意的服从,是对自己恩宠状态的确证,如果恩宠状态对人如此重要,那么劳动对人的诱惑应该远比肉体享受对人的诱惑大。如果需要靠禁欲来迫使人从事劳动,防止享受,那么劳动对于人来说就不是恩宠,而不是享受,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才需要靠禁欲来维持。
(二)劳动本身就是目的,与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灌输来促发天职观自相矛盾
首先,劳动本身就是目的与劳动自愿性不足自相矛盾。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精神支配之下的劳动已经成为工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为事业而活,而不是相反。韦伯并不是就劳动本身来论证劳动是工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是从促使劳动者自愿进行劳动甚至是超时劳动、把劳动当作一种责任的因素着手来进行论证。韦伯指出低薪资会导致劳动力的萎缩,因而靠低薪资来降低成本的方法,根本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韦伯进而论证了提高论件计酬费率同样不会促发工人劳动的自愿性和责任性。在不断计较怎么样才能最悠闲最不费力又能赚到同样薪水的想法的心态之下,提高论件计酬的费率只会导致工人的懈怠和生产的减少。韦伯对低薪资和高薪资对促发工人劳动自愿性的分析是为了引出资本主义精神在促发工人劳动自愿性上的关键性作用。然而韦伯没有意识到,其对劳动自愿性促发因素探索本身就是对“劳动本身就是目的”的一种否认。如果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工人存在的意义,那么工人就会自愿地进行劳动,把劳动当作是一种责任。而如果需要依靠外在的因素来激发工人的劳动自愿性,则说明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并不具有内在目的性,而是外在的促发性。缺乏外力的促发,劳动则不会发生。劳动的外在促发性与“劳动本身就是目的”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劳动本身就是目的与需要通过教育来促发责任性自相矛盾。韦伯在论述低薪资和高论件计酬费率都不能促发工人劳动自愿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了什么才是促发工人劳动责任性的因素。韦伯指出只有通过教育灌注资本主义精神,才能使得工人将劳动当作一种责任,当作人生的目的。如劳动的自愿性需要外力促发与劳动本身就是目的自相矛盾一样,劳动的责任性需要教育来促发同样与劳动本身就是目的自相矛盾。如果劳动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工人进行劳动就是自带责任的,就不需要通过教育来促发责任性。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被教育者缺乏责任性,教育的目的就是将教育者的理念传授给被教育者,以弥补被教育者的缺乏。因此,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灌输来促发工人将劳动当作一种天职,促发工人劳动的责任性则意味着工人本身缺乏劳动天职观,也缺乏劳动的责任性,并没有把劳动当作是本身的目的。
(三)工人劳动是合理化,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合理化是韦伯分析资本主义和现代化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则。韦伯将合理化分为社会层面的系统化过程和个人层面的个性合理化过程。个人层面的合理化就是个人“从不假思索地接受传统习惯转变为深思熟虑地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去适应周围的环境”[5]30。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是以自由为前提的,但这种自由不是个性的自由,而是内心孤独的状态。当个人进入这种孤独的状态,在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时,他在得不到他人的帮助的情况下,就会作出合理化的选择,而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的选择就是遂行天职,通过劳动来确证自己的恩宠状态。韦伯认为劳动克服了功利主义和超验理想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合理化,而不是异化。首先,恩宠状态是个人在俗世生活中最大的利益,劳动是恩宠状态确证的现世手段,因此,遂行劳动天职就是个人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去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大环境的合理化行为。其次,劳动天职观是对出世禁欲主义的超越。新教的禁欲是纯粹现世内的事,而中世纪的禁欲是超验的理想。加尔文教派认为恩宠状态必须在现世内进行确证,而世俗的职业劳动则具有此等事功。
韦伯对劳动的合理化论证看似符合其对合理化概念的界定,但是这种合理化的论证中充斥着手段与目的的颠倒、理性与自由的分裂。韦伯也承认资本主义合理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手段与目的、理性与自由的分裂,但是他对合理化的评价却采取一种暧昧的态度,有意掩饰这种分裂。首先,个人层面的合理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而劳动天职观是基于宗教教义的角度。因此,劳动天职观不是个人的合理化的经济行为,而是对宗教的非理性服从。其次,合理化的目的是通过自由的选择,实现对终极价值的追求[6]。劳动天职观无论是像其表面上说教的那样服务于神的荣光,还是如其实际上那样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都与工人本身的需求无关。对于工人来说,遂行天职既不是以经济为取向的终极价值选择,因为工人只生产财富,却不能占有财富;也不是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合理化行为,因为劳动本身就是目的,连确证恩宠状态手段功能的意义都已经隐去了,就更不用说以人为导向的目的理性了。
四、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韦伯劳动天职观虚伪性的披露
作为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世界公认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韦伯的理论在欧洲备受欢迎和推崇。这一方面是因为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包罗万象,涉及领域非常之广。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评价的那样:“韦伯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韦伯在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唯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也是由韦伯作为一名忠实的资本主义卫道士的政治立场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世界备受关注是因为马克思要揭露资本剥削工人的秘密,韦伯在资本主义世界备受推崇则是因为韦伯为资本剥削工人的秘密作了精妙的掩护。因此,韦伯的劳动天职观越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受推崇,就越彰显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彰显其为社会的合理化进程和个人合理化进程提供合理化论证的虚伪性。
虽然韦伯也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批判,但是他相信这种“荒谬的”并且“非理性的”的制度有着自己可怕的合理性[7]53-64,因此,韦伯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作为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理论,韦伯的劳动天职观本质上就是一种虚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了掩饰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是为了掩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异化的本质,是为了掩饰人自身的发展而非遂行天职才是人发展的真正目的。
(一)劳动天职观掩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
为了论证其劳动天职观的合理性,掩饰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首先,韦伯赋予了资本扩张精神传教士的合法外衣。资本给所到之处送去了资本主义精神,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形式,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给所到之处送去了文明,促进了未开化、半开化的民族的现代化。其次,韦伯编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韦伯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描述为一个和平的过程,一个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过程,一个自由劳动力自觉产生的过程,一个资本运行所需货币额的自行筹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暴力压迫,也没有武力掠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和教育。由此,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被韦伯粉饰成为一个没有压迫痕迹和暴力罪恶的,传播自由、民主和博爱精神的文明传播过程。
与韦伯先验性、唯灵论的论证方式相反,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同时辩证地评价了资本扩张的历史角色。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前提条件——资本和自由劳动力,都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实现的。而资本原始积累远非韦伯所言是一个文明传播的过程,相反,马克思揭露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的过程。首先,立足于唯物史观,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考察,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两条路径:一是以暴力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即圈地运动;二是通过暴力手段掠夺财富,即殖民掠夺。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货币,又为其提供了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自由劳动力的产生是通过人剥削人、人掠夺人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靠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实现的,也不是靠神的旨意来启明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人造物,不是神造物,更不是精神的直接产物。其次,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科学全面地评价了资本扩张的历史。资本扩张的过程一方面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传播,促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指出,资本扩张使得农村屈服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世界性的文学开始形成等等,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2]404。但马克思对资本扩张历史角色褒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贬抑,是为了揭示资本扩张血腥、暴力的本性,是为了强调资本扩张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是主观意愿,而剥削和掠夺才是主观预设的目的。因此,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297。资本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了极端贫困的无产阶级;资本在瓦解封建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创造了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2]403;在将最野蛮的民族纳入到文明之中的同时,也用坚船利炮塑造了一个殖民掠夺、奴役压迫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综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韦伯不仅主观臆造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而且还片面美化了资本扩张的历史,夸大了资本扩张的积极作用,掩饰了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资本所犯下的一切罪恶。
(二)劳动天职观掩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事实
韦伯虽然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手段和目的的分裂,但是韦伯仍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中蕴藏着可怕的理性。因此,韦伯断定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把劳动当作天职是个人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确证自己是处于恩宠状态的理性行为,因而是符合个人层面上的合理化原则的,是个人合理化的选择。
然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韦伯劳动天职观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并不会像韦伯论述的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恩宠状态而把劳动当作一种天职,当作一种责任去践行,而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者其他一切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54。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指出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自己占有的越少;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53;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54。因此,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有合理化的行为,那绝不是视劳动为天职,而是逃避劳动。这从工人的消极怠工和间歇性的捣毁机器进行罢工的行为,就足以证明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富有责任感的行为。其次,只积累财富而不进行享受是资本积累的需要,不可能成为工人的真实需求。工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也只刚刚能够维持肉体主体的基本延续,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何以谈享受,何以有禁欲的需要,以何来支撑其为社会生产财富的信念?工人并没有为自己生产出一个处于恩宠的状态之中的自我,而是生产出了一个同劳动疏远,但却占有劳动产品的人,即资本家。在工人劳而不获和资本家不劳而获的社会分工关系中,工人并没有感受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是真切地希望摆脱剥削和异化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分工是导致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发生矛盾的根源,因此只要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存在,异化劳动就不会消失[2]162。由此,工人的真实需求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合理化进程得以实现的,只有消灭不合理的、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工人的真实需求才能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由此,韦伯的劳动天职观只是为了掩饰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事实,将工人的异化劳动美化成为一种天职、一种受资本主义精神启发而自觉自愿的劳动,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为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虚伪性的价值观进行掩饰和辩护。
(三)劳动天职观背离了人的自身发展是目的
在劳动意义论上,韦伯主张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劳动是禁欲的最好方式,即“人为事业而活,而不是反过来”。劳动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工人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自己的岗位进行劳动。将目的归于劳动本身,就将劳动主体的需求成功地从劳动这一活动中剥离出去了。但事实上,离开了主体,劳动就不能发生。如果工人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3]243。劳动得以持续的条件是劳动力能够持续发展,既必须要保证劳动主体享受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3]47,否则劳动力就会萎缩,劳动也不能得以持续。由此,剥离劳动主体来谈劳动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劳动的目的必定与劳动主体息息相关。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劳动力以及劳动力商品等概念的基础上,首先马克思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是工人维持作为肉体主体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得到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价格形式,而不是劳动的价值的价格形式。事实上,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格,这也正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所在。因此,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而不是他的劳动。工人出卖劳动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劳动的机会以遂行天职,而是因为工人被剥夺了劳动资料,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因此,工人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劳动的目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劳动主体生命延续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也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人对人的类本质回归的必然途径。马克思以劳动为维度,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自觉的劳动、异化的劳动和劳动复归三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就开始将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了[2]147,即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劳动不仅将人本身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而且还是人摆脱异化状态,实现人对人的类本质回归的必然途径。在私有制社会,在劳动还是统治阶级借以奴役和剥削劳动者手段的社会阶段,劳动对于人来说不可能是一种生活需求,而只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劳动成为一种真正的自觉的劳动的时候,劳动才会成为人的第一生活需要。但是,劳动成为人的第一生活需要并不意味着人为事业而活,劳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本身的发展才是目的。
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主体维持肉体主体存续的手段,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因此,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都不能离开劳动主体而发生,劳动主体的需求才是劳动的目的所指。韦伯之所以大力宣扬“为事不为人”的职业性格,将劳动视为唯一的目的,把人自身的发展排除在目的之外,是为了给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进行合理化的辩护。基于劳动是劳动主体的对象化产物,很显然劳动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被资本强加的外在性的目的,而不是基于主体需要的内在性的目的,因而是一种充满虚伪性的劳动意义论。
五、结 论
韦伯作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从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进行论证也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天职,是对神意的服从,是合理化而不是异化,劳动本身就是目的等观点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论证的,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进行掩饰和辩护的。韦伯之所以提出劳动天职观,究其根源在于韦伯的阶级立场,即韦伯的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意识决定了民族权力而非正义和道德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8]115-136。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韦伯的劳动天职观进行批判,有利于我们透过韦伯思想的深远影响,揭示其虚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有利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正确地认识各种非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有利于我们理智地辨别真伪,合理地对其进行评价,既不盲目地排外,也不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