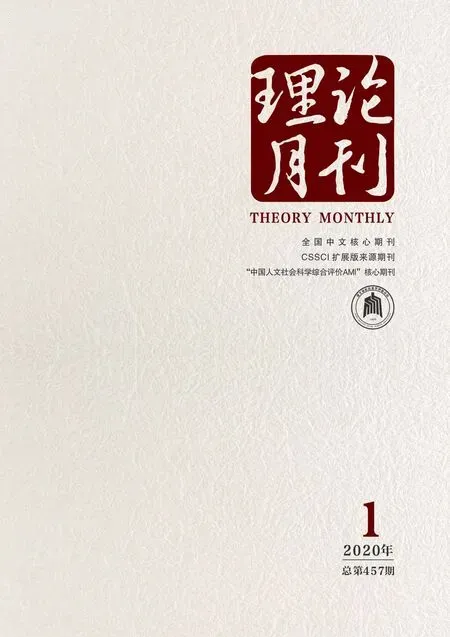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革命话语的认知、实践、信仰功能
□杨 帆
(井冈山大学 井冈山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 343009)
卡尔·曼海姆提出“那些具有革命功能的意愿就是‘乌托邦’”[1](p193),承认可以把“革命功能”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实现手段与具体途径,但是,却隐含了对于“革命功能”作为社会建设蓝图实现手段的批判意味。与之相对,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其革命话语论述之中提出“必定要在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过程当中,方能造成工人政权的真正基础,以进到社会主义革命”[2](p17),由此将抽象的“革命功能”介入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实现其功能化、效用化。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革命话语功能具体体现为:塑造革命认知功能、推进革命实践功能、造就革命信仰功能。这些革命话语体现了毛泽东革命话语从内容本体向外在功能的延伸与拓展,建构了中共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以及权威性,“在毛泽东的革命话语里,多数与少数的对比经常出现,革命的合理与合法性就建立在革命阶级——劳动人民是大多数,而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人数上是极少数”[3](p72)。而其革命话语通过内在逻辑层次性与关系结构性,对话语受众发挥效用,正如野村浩一在《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一文中分析毛泽东曾经使用的“造反”一词,认为“在这种语言和基于这种语言的行动之间,虽然存在着难以形容的深渊,但它们却一直广泛地潜藏在民众之中”[4](p312)。在其看来,“语言”和“语言的行动”是毛泽东革命话语两个方面要素的体现,语言是其话语本体,而语言的行动正是其语言本体的功能实现,体现为“语言字符及语音在特定语境中的交际功能”[5](p226),因此,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革命话语以他者认同的方式完成了自身意图表达并促使意图实现,进而实现了革命话语自身功能,正如有学者阐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功能实现图景时所说,“通过这一系列的话语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面前树立起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干部清廉、军民团结的良好政治形象,进而获得了民众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支持与认同”[6](p110)。
一、革命话语认知功能
陈建华指出,“有关革命的论述不必从使用‘革命’这一词语开始。在大量叙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革命的著作中,被描述的是政治与社会急邃变革的过程,此中包含了我们对革命意义的一般理解”[7](p1)。其论述之中揭示出话语受众对于“革命”理解与认知更多的具有外在输入性,取决于话语主体对于“政治与社会急遽变革过程”话语叙述之话语图景建构,形成话语受众对于“革命意义的一般理解”,进而完成话语主体对于话语受众进行革命认知塑造。正如福柯所言,话语叙述对于客观规律揭示只能是具有相对性,阐释的只能是绝对客观规律的可能性,而并非其自身,“对《圣经》的评论,对古代作者的评论,对旅行者报道的评论,对传说和寓言的评论:人们并不要求自己正要阐释的每一种这样的话语陈述一个真理;所要求的只是谈论这个真理的可能性”[8](p55)。井冈山斗争时期,国共两党围绕革命意象建构向话语受众开展了各自的话语阐述,力图将自身革命认知植入话语受众心理结构与话语表述,记叙国民党革命史的《中国国民革命史》在建构孙中山革命思想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时候,运用设问叙述方式,强化话语受众对于其革命思想正当性的接受与吸收,“问: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起因怎样?答:中山先生因当时政治腐败,海盗横行,民生凋敝,就发生革命思想,后来听人家讲洪杨故事,便决心从事于革命事业。”[9](p6)在话语叙述之中,主要是从“民生”角度阐释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因政治腐败,海盗横行,民生凋敝,就发生革命思想”,从而为话语受众建构了“孙中山革命为人人”的话语形象,确立了其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邵力子口述的《国民会议与国民党》一文中更是通过话语叙述明确强化了国民党的革命形象与革命权力,提出“中国国民党的性质比欧美各国政党与一百多年前法国提倡之天赋人权有不同,天赋人权,至今本已成为疑问,人类在社会应享如何权利,则应尽如何义务。我们是革命之政党,凡革命之人始与以国民之权能,至少也须不反对我们的革命”[10]。
有鉴于此,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其革命话语叙述之中,也非常注重通过革命话语运用塑造话语受众革命认知,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节录)》一文中回忆古城会议情景时谈到:“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迫切任务是要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他具体分析了把井冈山作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11](p30)。在毛泽东革命话语之中,他采用了其惯用固定表达语式,在形势分析之后进行任务布置以及更为微观的具体事项阐述,从而使得话语受众顺畅接受“中共革命信息”的传递,确立关于中共革命的认识与想象。
毛泽东通过话语叙述建构国民党反革命的形象,推翻其统治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12](p181)。经过大革命的宣传,军阀已经成为具有明显负面意义的词汇,“[军阀祸国]这个观念,近几年来,已经深深地印入一般民众的脑海里面了。”[13](p2)通过将“国民党”与“新军阀”这两个词进行并列放置,将“军阀”的负面意义顺利植入“国民党”一词的话语隐义,以不言自明的话语表现方式确立了国民党的负面形象,有效消解了国民党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继而,通过“依然”“对外”“对内”所引导的三个句子在整个句群中的深入阐发作用,也就是对话语主体叙述的核心命题进行具体化阐述与表达,确立了“国民党新军阀”负面形象的具体所指。最后以“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作为整个话语叙述“焦点”,即对话语意思表达最终指向有了定性表述,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黑暗与压迫比旧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依靠“焦点”最后停留加深话语受众话语印象。
毛泽东在消解国民党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后,通过话语叙述积极建构中共革命形象,对话语受众革命认知进行有效引领,“并且边界红旗子之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2](p19)。在其话语叙述中,毛泽东将“边界红旗子”这一具象化实物通过象征修辞手法转化成为表达中共革命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载体,正如话语受众所理解的,“红色在政治上通常象征革命。”[14]中共革命打出来的是“红旗子”,以明喻的方式向话语受众传递了中共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国民党革命象征物“青天白日旗”进行了显著的视觉区分,从而传递给话语受众简单有效的革命价值判断标准:中共革命色调是红色的,即是正当的、合法的、积极的、进步的;国民党革命色调是白色的,代表了腐朽的、落后的、保守的、反动的等等负面象征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如八月边界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军队重回宁冈,大宣传客籍杀死土籍,于是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军队烧屋、搜山”[15](p15)。“白带子”已经脱离了具体物品指陈,具有了反革命的语义,成了反革命的等义词。与之相对,“红带子”成了革命的等义词,“小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贫农委员会只作配角”[16](p14)。
毛泽东还为话语受众叙述了提升革命认知的正确方法,“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15](p29),提出“我们看事决然的是要看他的实质,而把它的形式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而把那做向导的形式抛在一边,这才是科学的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义的分析法”[16](p131)。其为话语受众提供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质认识论,认为“革命行为”的现象是表面的、浅层的,只有透过现象抓住“革命”问题的本质,才能为形成正确革命认知提供可靠的依据,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一文中指出“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17](p237)。毛泽东还论述了有些同志由于错误认识方法对于中共革命以及反革命力量发展所导致的错误认知结论,“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16](p130),以至于“不但红军及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心理,就是中央那时亦不免为那种形式上的客观情况所迷惑,而发出了悲观的论调”[16](p132)。而对于“对客观力量的估量亦然,也决然不可只看它的形式,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只有少数同志在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估量下真正相信湖南省委的话,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话的[十分动摇][恐惶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前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16](p131)。因此,必须采取科学的认知方法,提升话语受众革命认知,“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18](p101)。
二、革命话语实践功能
马克思在《贝尔格区的起义》一文中赞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指出“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街道和房屋都变成了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正从邻近地区——从佐林根、勒姆谢德、格莱弗拉特,从分布在埃奈泊流域的各个地方,——总之,从整个贝尔格区匆忙赶去。起义者并不限于占领爱北斐特和巴门等城市,而要把防御行动扩展到郊区的各个重要据点去”[19](p582)。列宁在《全俄政治罢工》一文中极力赞赏了俄国群众革命实践,提出“全俄政治罢工这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在这个充满压迫和暴力的帝国中,各族无产者正组织成为一支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大军”[20](p2),分析了革命实践对于无产阶级成长的重要性。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1913年11月1日,在《第一师范讲堂录》中以“奋斗”概念阐述了实践的重要性,“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不亡)图存。非奋斗不可”[21](p1)。1926年9月1日,其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一文中进一步关注到了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21](p126)。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继续运用革命话语,引导话语受众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提出“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军中与地方各级党部每日议事程序中重要项目,打仗成了日常生活”[2](p8),也就是革命实践行为已经成为根据地内部群众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也正是其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对群众所宣称的“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22](p52)
根据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井冈山当地革命老人李丁林回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群众参与革命实践的情形:
井冈山斗争时期,我是少年先锋队队员,那年二十二岁,在行州参加训练三个月。这个少年先锋队是遂川县政府的组织,一共有二十多个人,共分两个班。我当时名叫李亚官,少先队的一班班长。黄亚雄(荆竹山人)是二班长。当时少先队集中在县政府搞训练。每天三操两讲,当时由团代表给我们上课,讲的是说要学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搞革命要吃得苦,只有吃苦革命才能成功。操练主要是学立正,稍息,起步走,跑步,行军礼,讲军纪,讲群众纪律,学瞄准,练枪法,当时训练时没有枪,都是梭标,学习好了,就编队,补充到红军中去当兵[23](p24)。
李丁林的回忆只是记述了当年他参加中共军事组织,接受相应的政治与军事训练的情形,而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是要吸引群众参与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以及军事斗争的实践,“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分在分配中。区、乡苏维埃普遍的建立了。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苏维埃,并成立了边界苏维埃。乡村普遍组织了梭标为武器的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组织了快枪的赤卫队”[2](p7)。根据肖克回忆“当时部队分到地方,开展土地革命工作。井冈山时期的土地革命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①《访问肖克同志谈话记录》,资料来源于湘赣革命纪念馆档案室,宗号1,目录号76,案卷号A3,时间:1973年4月25日上午,地点:北京市肖克同志宿舍。永新农民贺云朵②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永新县人。回忆了其参加暴动队的革命实践活动,“那时我在暴动队,做灰色工作。挑扁担贩桐油到吉安,然后办买货物:电池(手电用)、香烟(哈德门和红金牌)、雨鞋、布匹,贩回来日用品,然后秘密交到一个指定地点,再由其他人秘密转交到西北特区。”[24](p1-2)
群众积极参与了井冈山革命实践,在黄洋界保卫战之中,“儿童团、少先队则在王佐任主任的防务委员会和工农政府的领导下,全都动员起来了,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赤卫队则持着各种旧式武器夹杂着少数钢枪,准备配合作战。妇女们则组织成后勤队,为前线服务。”[25](p4)但是,有时少数群众参加革命实践也会存在着假公济私、从中牟利的不当行为,1928年11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十一月十日红军新城、永新之役,宁冈四区赤卫队及一部农友不来前线作战夺取敌人枪械及担任运输、收获、搜山等工作,仍在新城附近农村中专事收搜及其他杂物。”[26](p119)因此,1930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中明令指出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实践,必须注意纪律问题,“凡各部所经过地方须特别严守纪律,尤以不得擅取工农东西,没收东西及焚烧房屋须得有命令方得执行,特别应领导随军群众做到”[22](p162)。
毛泽东直接指出了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革命实践的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就是必须要注意防止与克服部队内部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第二,就是必须要利用好“分兵”,以有组织、有系统地发动群众。据此,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认为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群众力量”[15](p25),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敢于组织起来向旧势力作坚决斗争”[27](p199),1928年10月5日,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指出“此时我们应对同志和群众,详细分析统治阶级与政治上经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动的势力,打破恢复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门依靠军队的等待观点(自然我们不否认军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28](p193)。毛泽东以其自身行动向红四军做出表率,运用适当的话语表达形式,向话语受众传递革命信息,将其动员起来积极参与中共革命实践。遂川县农民郭恩皇回忆了当年毛泽东与其交谈,劝导其参加革命实践的话语内容,“毛委员很和蔼,对穷人很爱护,那次在厅子里,还有些士兵在场。毛委员对我说□□白军就□□□,又对我说:你要赤胆忠心闹革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将来打下了全中国,大家都有好日子。”[29](p2)为了进一步纠正红四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运用话语表述直接将红军打仗的性质界定为非军事的,更多的是政治性的,提出“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完全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2](p25),以使得红四军充分明了动员群众参与革命实践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还认为必须运用好“分兵”的形式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实践,提出“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16](p133)1928年1月25日,“毛委员又把工农革命军集中在李家坪开会,这次会是动员再次下乡发布群众纪律。毛委员讲了话,在讲话中,讲了下去后要遵守群众纪律,损坏群众的东西要赔,借了群众的东西,用完后,要及时还,在群众家里住了,要注意打扫卫生,对群众说话态度要和气。”[30]占领永新县城以后,毛泽东又将部队分散进行革命实践推动工作,当时代表中共湖南省委代表的杨开明回忆道,“永新自攻克后,工作非常紧张,军中同志多出发各乡做事,拟于最短期间造成一党与群众的良好基础。”[31](p97)“分兵”以后,要将群众动员起来参加各种革命实践,“工人都要赶快传组各业工会、联合会,由全县各工会联合会和直属工会组织全县总工会”[32](p13)“各区乡农民赶快组织各区乡农民协会”,还要“解除保安队、保卫团等反动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和赤色游击队以保护工农阶级,肃清反革命派”[32](p14)。
三、革命话语信仰功能
革命信仰功能话语具有方向引领性,“故无论何时代之革命。亦无论革命原因之如何。要非使之印入于民众心理之后。则绝无结果可言。大凡事变之起。各有其特殊之形式。而此等特殊之形式。则又必由其当时民众之心理而生”[33](p3)。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非常强调树立话语受众之革命信仰,提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16](p131),其注重运用革命话语塑造话语受众革命价值观,进而形成革命信仰,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34](p113)。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运用革命话语内化话语受众革命信仰经历了消解——重构过程,因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脑中,一时扫除不净”[2](p14),其需要消除井冈山群众已有的民间信仰,而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植入群众的信仰结构。
有学者提出“中国人普遍认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天人合一是所有中国人信仰的基本原则”[35](p12)。井冈山地区群众的信仰生成主要也是基于神秘力量崇拜,血缘、亲缘、地缘以及社会身份认同等要素,形成了其自然信仰、亲缘信仰及族群信仰,因为不同区域的民间信仰各有其独特表现形式以及形成原因,“所谓的民间信仰,大多是扎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城镇或地方文化区域的,它们的信众主要是当地老百姓,它们的信奉对象、祭祀活动和崇拜行为等,也主要是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社会风俗、民间仪式、特别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36]。井冈山地区群众的自然信仰,实质就是革命时期称之为“封建迷信”的思想,“因为在农村里封建势力很强,宗族观念很重”[27](p33),致使井冈山地区呈现“封建迷信思想较浓厚”[37](p138)现象;其亲缘信仰则表现为浓厚的家族主义,毛泽东提出“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2](p15)他认为这种家族主义不但十分普遍,而且必须要有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得以纠正与改变,“但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形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2](p12);其族群信仰则表现为以土客籍作为社会个体身份归属,从而决定其族群认同与行为实践。正如同属罗霄山脉北部江西万载县所修“《土著志》是万载‘土著’集团的公开宣言:所有万载县人,要么是土著,要么是客籍,非友即敌。”[38](p189)毛泽东提出“在边界还有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2](p15),而在“我们的割据区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2](p15)。
鉴于井冈山地区话语受众的信仰实际,毛泽东注重运用革命话语破除话语受众的封建迷信,奠定其接受中共革命信仰的前提与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向农民讲话时经常讲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菩萨,没有什么‘八字’,要靠自己。那时要破除群众中的封建观念是很重要的启蒙教育”[27](p33)。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么这[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千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39](p43)
从而带动话语受众积极参加革命行动,“同时批判了‘富贵由天’‘生死由命’的天命论,破除迷信等等,于是农民又纷纷起来分田地”[40](p164)。莲花县“高洲区群众信迷信和继续封建习俗特别浓厚,区乡苏维埃及区文化部须加紧做破除迷信与封建习俗的宣传鼓动工作,造成群众自动起来反封建迷信运动。严格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和尚、道士及一切封建残余的猛力打击,现在还做和尚道士不改变其职业的人实行不分土地。”[41](p136)
毛泽东还非常注重科学理论的传播,促进话语受众接受中共革命信仰。运用话语叙述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现在我们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42](p27)。提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43](p76),因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43](p80)。同时,毛泽东还很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强调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指出“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43](p81)。即使是共产党的会场,也非常强调其无产阶级特色,提出要“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15](p33)。
毛泽东还认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党员教育,以促进话语受众革命信仰之形成,提出“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15](p33-34),包括“(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以及“(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15](p34)。据此,向中共中央请求购置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用于开展党员政治理论教育,“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44](p84)从而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以科学的标准发展组织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权威性,提出要对“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而吸收新分子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考察其对于中共革命信仰的态度,“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15](p31)。
四、结语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井冈山斗争时期起,就注重以“形势、建设及功能实现”等要素建构革命话语内容,“似乎同时隐藏着某种[中国革命]的特殊逻辑。”[45]这种话语逻辑性暗合了其思维逻辑性,始终坚持自我对于“革命形势分析、革命建设展开以及功能实现促进”的话语分析,正如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中强调指出“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46](p109)也表现在其话语表现形式与群众话语需求之间的耦合性,正如其在批评某些文艺工作者时所说,“什么是不懂?言语不懂,你们是知识分子的言语,他们是人民大众的言语。我曾经说过,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39](p972)。究其实质而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革命话语是以工具性外在载体展现了中共革命思想,“成为划分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成为划分知识的唯心唯物、反动和革命、资产阶级路线和无产阶级路线的最高依据”[47](p187)。在毛泽东革命话语的训诫与规训之下,其革命话语建构了话语受众的话语想象,进入了其话语结构,影响了其话语范式,最终将中共革命理念导入话语受众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