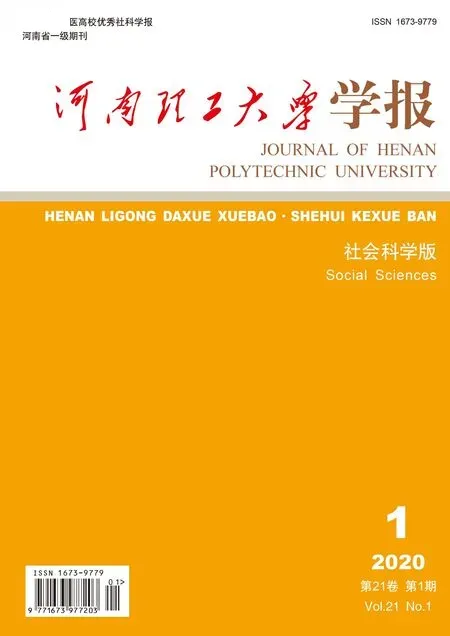明清督抚制度的嬗变及其评鉴
孙 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89)
督抚制度是总督制度与巡抚制度的合称,是明清时期中央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以派遣京秩出监地方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总督、巡抚逐渐向地方官嬗变,并最终成为省一级最高行政长官,成为监察官向地方官转化的典型案例。因此,探究督抚制度形成与嬗变的历史轨迹,分析其兴衰得失,可以察古鉴今。
一、督抚制度的形成与嬗变
明朝建立之初,在地方管理上沿用了元朝的行中书省制度。但行中书省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1]175。行中书省权力大而集中的特点,使新生政权存在严重的威胁,所以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废行中书省,将行省权力一分为三,设立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用以分管省一级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同时,明初又仿效汉代刺史制度,以省为单位,划分监察区,由都察院派遣监察御史进行监察,使三司无法与中央抗衡,确保了明初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三司自身也存在着无法忽视的不足,三司各自独立,权力过于分化,往往导致地方事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中央集权。因此,为弥补这一不足,进一步监察地方,明朝开始创立督抚制度。
巡抚制度起始于建文,定制于宣德。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遣“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2]1768,“问民瘼,课吏治,皆得便宜行之”[3]796。明朝设立的采访使,既承袭唐初设采访使巡按诸道的制度,又开启了永乐以后巡抚制度的逐渐成型。之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2]1768,巡抚之名由此而来。但此时的巡抚“均因事因时而设,旋设旋撤”[4]212,只是为了特定任务而出巡地方。而使巡抚开始有固定的建置,进而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则是在明宣宗宣德时期。明宣宗洪熙元年(1425年),胡概巡抚南畿长达五年。宣德五年(1430年),接替南畿巡抚的周忱更是任职22年之久。这使巡抚由短期出巡改为常驻久任,可以说是明代巡抚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之上,巡抚常设开始普遍化,“宣德五年九月丙午,擢监察御史于谦、越府长史周忱等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处。各省专设巡抚自此始”[5]849,这标志着明代巡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确立。
总督制度则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起始于正统,定制于景泰、成化。在此之前,明代也设有总督一职,但其职能只限于督催税粮,并非监察军政,这与我们所说的总督制度有本质区别。正统年间民变多发,为了解决巡抚及三司无法应对的接连不断的地方起义,朝廷始创总督军务之制,“正统初,靖远伯王骥以兵部尚书督师征麓川,始以总督军务入衔”[6]849。但此时,总督也属临事派遣,而形成固定制度则应在景泰至成化年间。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以王来担任湖广总督平叛贵州,事毕,“诏留(王)来、(梁)瑶镇抚。寻命来巡抚贵州”[2]4581。此时,总督辖区逐渐固定,开创了总督兼任巡抚的先例。景泰三年(1452年),为解决两广苗患,朝廷又以左都御史王翱为总督总管两广军务。在之后的天顺四年(1460年),由于石亨擅权干政,明英宗遂罢停督抚。至成化四年(1468年),两广盗贼多起,韩雍两度被任命为总督,“开府梧州,遂为定制”,“三司皆长跪白事”[5]1213。这一变化标志着总督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同时表明总督出现了向节制三司、总领一方的地方大员转化的趋势。
之后,自成化至嘉靖,督抚制度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巡抚一省一设、总督跨省而设的格局以及巡抚重民政、总督重军政的局面。万历中期以后,由于内外矛盾激化,明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为挽救政权,督抚不断增设,建置愈加混乱,一直到清代统一以后,督抚制度才得以恢复常态。
清初承袭明制,地方政治体制仍基本沿用三司制度,并在三司之上设立督抚,用以监察地方和军务。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几次改制,以诏谕敕令、各类会典事例的形式,进一步规范了督抚制度,使督抚成为地方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此时,出于强化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督抚设立往往职权轻,任期短。
直到道光、咸丰年间,为了应对接连不断的内外矛盾,督抚职权逐渐加重,任期也越来越长,这大大加速了督抚向地方官嬗变的进程,督抚最终嬗变为封疆大吏应该说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过程中确立的[7]118。为了镇压起义军,道光帝允许督抚在地方操办团练和训练新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曾国藩组织的湘军和李鸿章组织的淮军。这些往往成为督抚的私人武装,也成为督抚发展自己势力和扩张权力的借口与资本。咸丰年间,为开展洋务运动和应对内外战争矛盾,原本职权扩张的督抚势力更为膨胀,如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达24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18年,成为总领一方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在督抚任上做大的袁世凯更是权倾朝野。与汉朝的刺史、唐朝的节度使相似,督抚由监察官嬗变为封疆大吏,尽管没有像前两者完全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但还是从体制内部加速了政权的灭亡,没有摆脱“历史周期率”。
二、督抚制度的建构
经过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规范,督抚制度不断完善,在督抚的建置、职权、任命、考核、保障、监督制约等方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第一,督抚的建置。督抚设立采用兼衔制。一方面,保持中央派遣官身份,督抚均列于都察院,这样一来,既明确了督抚中央监察官的定位,也保证了督抚在地方的权威;另一方面,突出督抚地方官的地位。乾隆三十年明确规定:“督抚为国家封疆大臣……嗣后三品以下奉差外省,非特旨有钦差字样者,概不准在督抚前列名。”[8]10由此也可看出,督抚的地位已经定位为省级最高长官了。同时,经过明清几次重大改制,督抚制度形成了巡抚一省一设、总督两省一设、部分巡抚由总督兼任的基础格局。直至宣统二年,最终形成直隶、四川、甘肃、福建、湖北、广东、云南、奉天巡抚由总督兼任,其余每省各设巡抚的格局[9]17。
第二,督抚的职权。督抚制度职权逐步突破省级政权分权化而走向“事权归一”,“督抚之设,统制文武,董理庶职,纠察考核,其专任也”[10]7。其中,总督与巡抚的职权也有所区别,如雍正帝谕令:“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号民绥辑,乃为称职。”“国家任官守土,绥辑兆民,封疆之责,惟抚臣为……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于巡抚。”[11]5这就充分说明了巡抚重民政、总督重军政的职权区别。此外,随着内外矛盾的日益增加,督抚的职权又不断扩张,几乎涵盖了所有地方事务,如监督任用官吏权、节制绿营军队权、监督财政权、司法审判监督权、对外交涉权等[9]28。
第三,督抚的选拔与考核。明朝至清初,督抚的选拔采取廷臣会推的方法,至康熙十年谕令停止会推推升之法[12]35,改由吏部(后为军机处)开列具题请旨,再由皇帝最终确定人选。督抚的考核方式一为“京察”,三年一次,督抚遵例自陈,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具奏请旨处置;二为“咨部”,督抚需定时向六部报告工作情况,六部则有权针对相关工作进行核准,向督抚提出驳议,对督抚进行弹劾。而不管哪种考核方式,最终都由皇帝对督抚进行奖惩去留的决定。
第四,督抚的保障机制。一是开府建牙。随着督抚常设常任,巡抚衙门、总督衙门相继建立。二是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及各道员成为督抚属官。乾隆十三年明确规定:“督抚总制百官,布按二司皆其属吏。”[8]14同时,原本作为布、按二司属官的道员,也逐渐成为替督抚传布政令的官员。三是督抚驻留地方,可以携带家眷。
第五,督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督抚进行监督和制约,主要通过两个维度:一是“大小相制”,“大”指通过君主和朝廷监督震慑,“小”指通过布、按二司等衙门分权制约;二是“内外相维”,“内”指由各部院对其行事进行查核监督,“外”指由督抚之间进行相互制约,以达到“设官置吏,中外相维,是以万里之遥,若臂指之相使”[13]5569的效果。
由此可以看到,督抚制度的完善过程实际上就是督抚制度的嬗变过程,督抚制度在完善过程中又走进了“历史周期率”。
三、督抚制度的作用与缺陷
纵观明清两代,督抚制度都曾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稳定政权。明清之初,三司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其鼎足而立,凡遇大事,各系统难以协调,拖延不决。特别是遇到地方“民变”或者动乱,三司调动军队还须向朝廷申报,易使地方形成失控的被动局面[14]368。督抚的设立恰恰成为三司的“中枢”机构,能够快速的决定、处理事务,直接处理对外战争、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征收赋税徭役等,起到了快速稳定政权、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二是察吏安民,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督抚以京秩出监地方,其监察权远远大于一般的巡按御史,对地方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凸显了“镇”与“抚”的监察效用;督抚以近臣外任封疆,“带风宪之衔,不独地方利弊可言,即朝廷大政无不可入告”[15]1042。可见,不管国家大政还是地方事务,督抚都被要求与中央保持密切交流,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然而,看似能够完全弥补地方政治体制不足的督抚制度,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正是这些内生性缺陷,决定了督抚制度的嬗变,进而不断侵蚀政权机体。
首先,督抚设立的逻辑起点存在缺陷。君主通过监察官的“外化”来达到对国家权力的“内化”,以强化皇权对国家的“内控”[7]119,这是督抚设立的逻辑起点和监察官地方官化的根本动力。我国古代长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专制君主为保持自身在政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都力求“事事躬亲”“乾纲独断”,但面对辽阔的疆域和纷繁的事务,又不得不以一套官僚政治制度来维系政权的正常运转,这就必然导致皇权的分割以及皇权与相权的对立。而督抚等监察官“由内及外”的嬗变,正是皇权与相权博弈的结果与体现。一方面,督抚以京秩出监地方,本就深受君主信赖;另一方面,督抚代表了皇权与中央的权威,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往往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更使君主对督抚产生依赖,这必然使督抚可以得到更多授权,更好地统领地方。照此路径,我们可以推出,当监察官完全嬗变为地方官后,其本身又会造成对皇权新的分割,对此,专制君主将势必再派“近官”对其进行制衡。新的制衡若有效,则会重蹈监察官向地方官嬗变的覆辙;若无效,则往往造成地方割据或分裂。这一路径依赖,使督抚自设立之始便注定了向地方官嬗变的“命运”。
其次,督抚制度的运行机制存在不足。督抚制度实质上是以服膺皇权为最高原则,为维护皇权而监察地方,为此,确立了以君主为中心的选拔机制、考核机制、保障机制等,以保证其能有效运行,服务皇权。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各项机制缺乏独立性,导致督抚监察效果大减,权势不易控制,加速了督抚向地方官的嬗变。一是选拔机制不独立。总督一般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开列,由各部侍郎、各省巡抚升任或由总督互调[16]1;巡抚一般由内阁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顺天府府尹、各省布政使升任,或由巡抚互调。由此可见,督抚选派并非完全出自监察系统,他们或由地方官升任,或由中央行政官外派,在监察过程中难免摆脱不了行政化或地方化思维,更难以保证监察主体的独立性。二是考核机制不独立。以“京察”“咨部”为主的督抚考核,往往需要都察院、吏部及其他各部院的配合,所以为了自身前途,督抚在处理问题时就不得不考虑相关方的利益,难以保证监察过程的独立性。三是保障机制不独立。尽管督抚被允许开府建牙,但在人、财、物等方面还是需要地方官的支持和帮助,工作开展也主要依靠三司及其属官,难以保证监察工作的独立性。因此可以说,督抚制度运行机制上的不独立,导致了其监察效力的不可持续性,也使督抚常驻地方后快速融入了地方官僚队伍之中,加速了自身向地方官嬗变的进程。
最后,对督抚的监督制约存在漏洞。为避免前朝“强枝弱干”的局面,明清两代从“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两个维度、四个方面对督抚进行监督和制约。而这本质上属于政权体系内部的自我监督和约束,无法根本规范督抚用权、保证督抚廉洁。一方面,督抚作为皇权的“代表”,地方官吏对其“趋奉积习,恐督抚见疑……竟有不得不就之势”[17]176,中央各部院“办事预存一私意,计较某省督抚正在褒奖,其事宜准,某省督抚方得不是,其事宜驳,不论事之当否,而专以逢合为心”[18]28。三司听命、六部逢合,这使“大小相制”“内外相维”根本无法发挥实效。另一方面,遇到非常之事时,皇帝与内廷往往通过督抚的密折奏陈了解下情,督抚也借此机会请旨获得办事权,主动寻求权力的扩张。长此以往,督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央的权力,不断从内部侵蚀政权,直至国家灭亡。如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权力不断扩张,最终尾大不掉,逼迫清廷逊位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四、督抚制度嬗变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现如今,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政治改革重要一环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以史为鉴,回顾明清督抚制度的形成与嬗变过程,总结其利弊得失,对当今我国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要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国家政权架构相适应。明清创立督抚制度以弥补地方不足,并取得了明显效果。然而好景不长,督抚制度很快异化和变质,缺陷暴露无遗,很大原因是没能正确把握制度建设中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因此,当前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要将其放在国家政权的总体框架之中来考量和推进,既要注重监察体制本身的改革,又要注重此项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协调、相适应;既要注重监察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又要注重将此项改革做深做细、做规范做完备;既要注重改革对当前反腐压倒性态势的巩固,又要着眼于夺取反腐败斗争全面胜利的延续性、复杂性。
其次,要确保国家监察权自上而下的独立性。只有保障独立性,才能凸显权威性。督抚制度的嬗变、督抚监察的乏力,很大原因在于难保自身的独立性,这在督抚的选拔任用、权力行使、考核奖惩、后勤保障等方面均有体现。所以,要想顺利推进此次改革,就应当高度重视监察权的独立行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体制和以上级监委的领导为主;明确要实行监察官制度,依法确定监察官的等级设置、任免、考评和晋升等制度。但当前具体的法律法规多在酝酿之中。今后应当重点研究,广泛借鉴先进成果,系统设计各项具体制度,保障监察权的合理配置,确保权力自上而下行使的独立性。
再次,要确保国家监察权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的独断性、随意性、多变性是封建社会人治的显著特征。督抚权力完全来源于专制君主,君主往往根据自身需要而授权督抚,致使其权势不断扩张,结果难以掌控。因此,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整合相关权力以达到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目标的同时,更要注意依法监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对监察权行使的主客体、范围界限、方式方法、审批程序、时限要求等做出了严格规定。今后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当对审查调查、巡视巡察、派驻监督、信访举报等具体工作做出更为深化、细化的规定,确保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把监察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最后,要注重对国家监察权的多元监督和制约。对督抚制度的监督制约之所以失效,就是因为只存在政权体系内部的监督和制约,而忽视了外部作用。因此,在目前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除了强调国家监察工作人员应忠诚干净担当,设置内部监督机构以加强自我监督之外,还要重视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各自优势;加强检察权、审判权与监察权的相互制约;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监督制约方式,依法对监察机关进行监督和制约。
五、结 语
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充分汲取我国传承千年监察制度的合理内核,克服监察制度嬗变的弊端,以免重蹈监察失灵、腐败泛滥的覆辙。同时,还要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不断改革创新国家监察法律法规、工作规程,完善国家监察制度,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