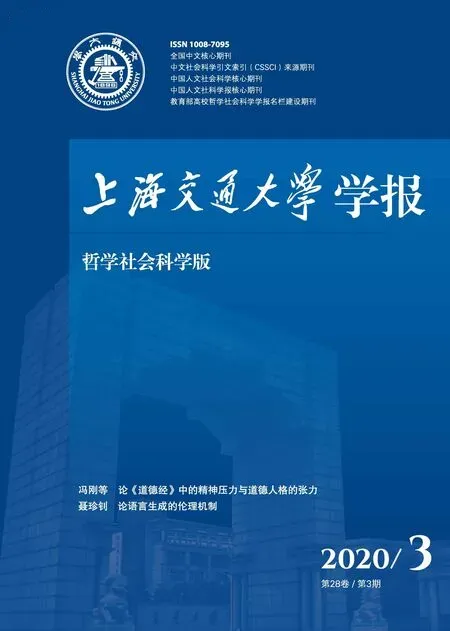身体·主体·社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经典科幻电影的“赛博格”想象
潘 汝
(浙江传媒学院,杭州 310018)
赛博格(Cyborg),由cybernetics和organism这两个词构成,cybernetics意为控制论,organism意为有机生物体,合二为一则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的混合”(1)[美]唐娜·哈维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314.,乃“半人”或“非人”之意。“赛博格”生发于20世纪40年代控制论的土壤。1948年诺伯特·维纳的划时代著作《控制论》(Cybernetics)的问世,也伴随着“赛博”一词的诞生。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苏军备竞赛的狂潮中,“以技术手段干预人体使之适应极端生存环境”的需求,进一步激发了对控制论的探究热潮。1958年利克莱德提出了“人机共生”的概念,将“控制论”隐含的主体性削弱,因而“赛博文化”(cyberculture)的概念在1963年被首次提出时,词根的变化完全消解了主体控制的意味,所以这一概念很难再被翻译成“控制论文化”。此后,“赛博格”一词应运而生,并逐步从科技领域走向大众文化。库布里克根据克拉克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便是大众文化痴迷于“赛博格”的一个印证。20世纪70年代之后,“赛博格”在科学层面上的意义渐次淡化乃至消亡,但“‘赛博格’作为一个强大的神话与隐喻重生了”(2)[德]托马斯·瑞德.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M].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132.,唐娜·哈维拉在1985年发表的著名的《赛博格宣言》,模糊了身体与机器、人与非人、意识与模拟、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界限,描绘了某种理想场景,这也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各种乌托邦式意识形态的源头与内在本质,从而催生了“赛博格”科幻电影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网络矩阵等成了这一时期科幻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
在此,笔者试图从三个维度——身体、主体自我、赛博空间——探讨近三十年来欧美经典“赛博格”科幻电影如何以影像的方式批判因身体差异而导致的伦理秩序的失衡,传达主体自我在数据时代被解构所带来的迷惘情绪,揭示被控制论所定义的赛博空间的“专制”特征;进而对“身体”的进化与虚化、跨越差异性的新主体自我的重构、“民主”式乌托邦赛博空间展开想象,突破了人与非人、意识与模拟等二元对立的藩篱,表达了对新技术条件下人类生存状态的忧思与展望。
一、 赛博格:“非人”的身体
关于“非人”身体的叙事,伴随着科幻片创作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20年代被誉为“科幻电影的第一座丰碑”的《大都会》(1927),到二战前的《隐形人》(1933)等,再到冷战时期的《2001太空漫游》(1968)《变蝇人》(1958)等,都在“赛博格”与“本真人类”的身体差异中呈现矛盾冲突,展开故事情节。而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美“赛博格”科幻电影对“非人”身体的思考日益凸显。
(一) 歧视与迫害:“非人”身体
自文艺复兴以来,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及同时期画家们的相关作品表现了人的身体的完美尺度。这些画作以“视觉上实现具音乐和谐感的数字比例”(3)[法]乔治·维加埃罗.身体的历史: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M].张竝、赵济鸿,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22.而成为通行的人体审美标准。然而,随着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兴起,这个作为人体标尺的普遍具象暴露出其价值与审美定位的偏颇与狭隘: 以年轻强壮的欧洲白人男性的形象代表全人类的理想身体美学,依据这样的标准,女性、有色人种、非欧洲裔、病弱衰老等身体形象都被视为“他者”,“被评估、管理和分配到一个指定的社会位置”(4)[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36.,于是,隔离、歧视乃至迫害都变得顺理成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美“赛博格”科幻电影,对“非人”因身体差异而被践踏、被蹂躏、被清除的“不公”,表达了显而易见的批判意识,换句话说,也就是将人类平等的意识延伸到了“赛博格”的领域。如果说80年代的《银翼杀手》(1982)还通过亚文化的包装对外星来的“赛博格人”有所鄙视的话,那么之后的《人工智能》(2001)、《机械公敌》(2004)、《别让我走》(2010)、《双子杀手》(2019)等则将他们视同“常人”,提升了伦理叙事的境界。
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2001)描述了安装了情感运算程序的人工智能男孩大卫,被养母遗弃之后,踏上寻找童话中的蓝仙女之路,以期变身真人,重返养母怀抱,却被送入“机器人屠宰场”,目睹人类残暴的杀戮。
影片一开场,哈比教授就对故事中的人工智能做了这样的设定:“一个有心智与情感的机器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潜意识及充满暗喻、直觉及自主推理能力的内心世界。”随后出场的机器男孩大卫不仅有持续的爱的能力,还有追求梦想、主动探索的能力,拥有与人类完全相同的精神世界与自我意识,唯一不同的是身体构造。正因为其身体的“他性”,致使他及他的同类被当做低贱的玩物,归于病态的异类,从规范性中被驱逐出去,沦落为不端、变态、耻辱的代名词。
在影片中,“机器人屠宰场”弥漫着对这种“不公”的隐喻式批判。喧嚣的机器人屠宰场是政治权力意志的实现空间,被人类视为以身体为核心来完成“生命庆典”的场域。“身体中没有晶片的”纯正人类,围成一个巨大的环形观看圈,而那些被人类遗弃的机器人被置于观看的中心,被处以各种酷刑,或被塞入炮筒烧射成炮灰,或被利剑施以腰斩,或被滚烫的硫磺液体熔毁……“他者”被销毁的场景,成了一场身体消费的疯狂宴会。在这里,观看者因其合乎规范的身体而被视觉政体赋予了合法权力,代表着公正与秩序,正如屠宰场的主持人约翰逊傲慢地宣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鲜活的生命,我们要为人类创造真正的未来”;而被观看者,则因身体差异而成为“他者”与异类,被剥夺、被迫害成为“理所当然”的秩序要求。
如果说《人工智能》(2001)、《机械公敌》(2004)等系列科幻片中的“他者”身体因其机械构件而区别于所谓的纯正人类的话,那么,《别让我走》(2010)与《双子杀手》(2019)中的克隆人,身体的内外构造均无异于“人类”,仅因其脱离了两性生殖而被视为异类,承受命运的不公: 前者成为人类“本尊”的器官的捐献者,后者沦为剧中反派的一枚棋子。但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非人”身体,都在失衡的伦理秩序中遭受磨难。
(二) 进化与虚化: 对“身体”的开放性思考
在批判“歧视‘非人’身体”的语境中,对“身体”的开放性思考成为必然。在新科技的狂飙中,基因工程、机械连接、电子植入、远程传输等方式都可造就区别于自然人的“非人”。在这样的情境下,“‘非人’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肯定性的概念元素,通过它,我们可以思考人的移置”。(5)[法]阿兰·巴迪欧,[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当下的哲学[M].蓝江、吴冠军,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56.于是,“人”的内涵与外延被大大拓展,正如甘克尔所认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人’这一词已经开放,也包括动物和法人,而且随着我们开始授予非人类代理权,将机器纳入人的范畴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6)Gunkel D. The Machine Question-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I, Robots, And Ethic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2.
吕克·贝松的《超体》(2014)是思考身体的开放与移置之可能性的最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品。影片讲述了一个身处异乡的卑微人物Lucy小姐,误入国际贩毒组织,被迫以人体藏毒的方式运送高科技“毒品”——CPH4,岂料体内的CPH4渗漏,于是在短短几十个小时内,Lucy迅速进化为脑容量开发利用率达100%的神奇的“赛博格”。
影片中,吕克·贝松运用理性蒙太奇的手法,将Lucy的奇幻身体进化,放在人类进化的总体框架中予以演绎,其寓意颇为明显: 借Lucy的身体流变,探讨“后人类”身体进阶的程序及最终可能——从完美的自我身体控制,到控制他人身体与意志,直至物质性的身体消失,最终成为无处不在的虚拟符号表征。
在哈维拉看来,自我与他者、心灵与身体、物质与非物质、有机体与机械物之间尽管存在区分,但“高科技文化以各种有趣的方式挑战这些二元论”(7)[美]唐娜·哈维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377.。剧中,Lucy的身体“跨越了通常意义的肉身、性别、身份的局限”(8)张进,王垚.技术的嵌入性、杂合性、药性与物质文化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1): 20-26.,以其“在不同的情境中不断编码和信息转换的多元合成体”(9)张进,王垚.技术的嵌入性、杂合性、药性与物质文化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1): 20-26.,彻底抹煞了“人”与“他者”的界线;而作为Lucy身体演变的终极形态——非物质形态的“虚拟躯体”,将人们对身体的开放性想象推向极致。
片末的那视觉上归于“无”、以数据流的方式存在的躯体,并非吕克·贝松“向壁虚构”的产物。早在1986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应德国齐根大学之邀所作的《无躯体能否思维》一文,就提出了“非人”身体的终极形态——虚化。在利奥塔看来,人体是一种技术装置,只要充分了解这个装置,就有可能制造出可供思维运行的平台。倘能如此,45亿年之后的“后太阳”时代,地球灭亡,一切物质实体消亡,人类思维仍有可能借助非物质实体的平台得以幸存。利奥塔说:“所谓无躯体,准确地说,就是‘无’被命名为人体这复杂的地球动物的躯体。”(10)[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M].罗国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14.换句话说,就是培育一种虚拟的身体,使之在非地球的环境中仍然能够为人类的思维软件提供运行的可能。在地球毁灭之后,这个虚拟身体承载着人工智能与天然智能合二为一的思维软件,逃逸到远方,如此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才不至于因最终的灭亡而失去所有的意义。利奥塔指出,如果我们“相信一切的合目的性”,坚守所谓的物质“本质”,即“物质与思维的契合性”,那么,我们“将是这个宇宙角落中稳定秩序关系的牺牲品”。(11)[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M].罗国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11.
对这种虚拟化身的探究,还仅仅是艺术家与哲学家的冥想,是否具有科学的依据,尚在不确定的争论之中,如同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具有意向性思维的争论一样,但是对于科幻电影来说,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之“实在”地予以表现,因为类型电影的奇观形式需要无止境的创新。
二、 主体自我: 消弭与重构
“赛博格”身体的建构必然会导致主体自我的重新定位,在开放的环境里、流变的过程中推演着“生物算法”,并“以技术为中介,在一个自然-文化连续统一体中发挥作用”(12)[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88.,因此传统主体自我有可能遭到质疑,“外部算法理论上有可能比我更了解自己。如果能用某个算法检测组成身体和大脑的每个子系统,就能清楚掌握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13)[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296.
(一) 主体自我意识的崩塌
1990年,菲利普·迪克的小说WeCanRememberItforYouWholesale被保罗·范霍文以《全面记忆》(1990)(又译《宇宙威龙》)为片名搬上大银幕。时隔22年,伦·怀斯曼重拍《全面记忆》(2012),除了故事的发生地有所改变,核心内容与旧版大致相同,讲述了主人公奎德在智能程序操控下追寻“自我”的故事: 在一系列生化作用下,机器人工厂工人奎德变身孝生——一个打入反抗组织内部的“英联邦”密探,与“殖民地”反抗组织首领麦费思的女儿梅琳娜相爱并携手粉碎了英联邦元首高克根入侵“殖民地”的阴谋,成为救世英雄,但在胜利收官之时,奎德突然发现此时的自我并不真实。
在传统好莱坞类型片的框架下,影片反复渲染“自我”在科技的作用下逐渐消弭的事实。奎德到力高公司订制记忆,打造新我时,试图追问输入记忆之后的“自我”的真实性,力高公司的记忆定制操盘手确定无疑地告诉他:“生活只是大脑对所见事物的化学认知,是你的大脑对你的眼睛所见产生的化学反应,我们只是删除了中间媒介,直接产生化学反应。”这也就意味着,奎德定制的“自我”不需要现实中介,直接通过大脑神经元的化学反应获得完全真实的存在感,也就是哲学家所谓的“缸中之脑”,因而奎德不断发出“我是谁?”的惊恐质问。反抗组织领袖麦费思回答了奎德关于“自我”的追问:“每个人都想找到真正的自己,但答案是,(真正的自己)在当下而不是过去……过去的事构成了人的思想,令我们盲目,蒙蔽我们,但人的内心是想活在当下。”奎德接受了麦费思的理念,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我不知道自己以前是谁,但我知道自己现在是谁。”从而完全认同了大脑神经元所提供的“当下”。于是,影片末了,奎德发现手臂上的记忆植入标志消失不见——这个标志相当于后来《盗梦空间》(2010)骰子陀螺之类的物件,用于分辨幻境与现实——这就意味着他此刻所拥有的并非所谓现实中的自我,但是,奎德不再追问真实自我,而是将梅琳娜拥入怀中,活在此时此刻脑神经的电化作用所创设的虚拟现实中。
其实,关于记忆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早在80年代的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1982)中就有了雏形,复制者接受人为的“记忆”,获得“真实”人类的错觉,虚拟记忆成为他们自我的核心。在其后的科幻电影中,关于“涣散的主体、飘忽的自我”的主题,变得愈发复杂与吊诡。《异次元骇客》(1999年)表现了虚拟主体反客为主,占据其创造者之身心的奇思妙想,这种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互换主体的设定,与同时期的《黑客帝国》(1999)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启示了其后《盗梦空间》(2010)等经典影片的创作。正如这些电影所暗示的,无论用来建构自我的记忆材料是来自真实的生活经验还是虚构的贩卖,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都用它们来为自己构建现实,并创设未来,而正是在技术提供的亦真亦幻中,传统意义上的主体自我崩解并溃散。
(二) 主体自我的重构
2000年,年轻的诺兰凭借《记忆碎片》(2000)一鸣惊人,从此关于记忆、梦境与自我的探寻成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在长期对碎片化自我的质疑与思考之后,诺兰先知先觉地意欲在资讯时代寻找主体自我的重构之路,尽管这种探索并不流畅与顺利。由他制片的《超验骇客》(2014)的前半部分让观众误以为在走“技术恐惧”的老路,至后半部分才渐次显露其真正的创作意图——重构人类的主体自我。
影片的主人公是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威尔与伊芙琳夫妇。威尔因其致力于情感与智慧兼具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制而招致反科技极端分子的谋杀。在威尔将死之际,伊芙琳成功地将威尔的意识上传到电脑并联网。在自由的网络世界,威尔通过自我学习极速扩张,建立数据中心,将群体意识贯注到每一个接受其治愈手术的活生生的人体中,还运用纳米技术修复生态。然而,对未知的恐惧使得包括伊芙琳在内的一干人等决定消灭威尔,伊芙琳在体内注入病毒,以诱杀威尔,而威尔早已洞察一切,他选择主动感染病毒,与心爱的伊芙琳共赴死亡之约。这部影片超越了以往科幻电影的“新哥特式恐惧”,塑造了威尔这么一个跨越差异性、构建群体性、充满生态责任感的主体自我的典范。
关于建构跨差异性主体的设想,威尔在影片开场不久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出:“有感知能力的机器一旦联网,将迅速克服生物局限……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存在: 同时拥有人类情感,甚至自我意识的‘超验者’。”上传意识之后的威尔,成为跨越各种差异的AI超验者。
人与机器的区分不仅在物质本体,更在于意识与情感。威尔的意识上传电脑并联网之后,突破了人类作为生物体的诸多限制,完成了人类智慧与机器及网络的强强联手。更重要的是,威尔的主体自我并没有认同冰冷僵化的机械律条,而是饱含着人类的自我意识与深情的爱,他用全知全能的技术手段检测伊芙琳体内的激素变化,关心她每一丝情绪的波动。以自己的超能之力,实现着伊芙琳改变世界的美好梦想。最后,为了解救好友麦克斯,主动选择与感染了病毒的伊芙琳一起赴死。从某种意义上,上传之后的威尔的主体意识是否真的存在是一直被质疑的,只有当他表现出人类情感与意志的时候,才实现了真正的人机一体,“无躯体”的意识找到了更好的操作平台,而原本无情感无意识的机器与网络获得了爱的灵魂——即主体自我的核心。
这个人机一体的新主体自我,在跨越差异性的基础上建构其群体性特征。在科技时代,“人类不再认为自己是自主的个体,不再依据自己的期望度日,而是习惯把人类整体看做一种生化电算机制的集合体,由电子算法网络实时监测和指挥”(14)[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296.,于是,个人主义崩溃,权威也从个体化的自我意识转向算法所构成的集成网络。剧中,某些散居个体纷纷汇聚到威尔所构建的布莱希特伍德小镇的数据中心,救治伤痛、强壮身体,并通过联网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体。威尔所打造的社团型主体,不同于极权政体,他让人们通过联网的方式,确定个体的定位,各尽所能,协作共进。正如剧中威尔所介绍的那样:“他们保持自己的个性,但他们也同时行动,作为群体意识的一部分。”
而这些兼具个性与群体性的超验者还是生态责任的积极践行者。威尔在濒死时刻描绘了自己正在实现中的属于伊芙琳的梦想:“我们正在拯救生态系统而不是伤害它,(纳米)微粒随着气流传播,或以原有的污染物为中介自我复制,推进着生态的自我修复,森林可以再生,水纯净到任何一条河流都可以直接饮用。”虽然这个充满责任感、践行生态哲学的完美主体威尔被那些因未知而恐惧的人们所杀,但其具有超越性的主体价值永存。
三、 赛博空间: 西方科幻视域下的社会系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美“赛博格”科幻电影,在探析身体与主体自我的同时所展开的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基本上不脱离“专制”与“民主”的刻板冷战思维。
(一) “专制”式反乌托邦梦幻空间
正如英国学者乔治·弗兰克尔所说的那样,“人类渴望理解、支配和控制他的环境,并最终创造环境。”(15)[英]乔治·弗兰克尔.文明: 乌托邦与悲剧[M].褚振飞,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144.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运用生化手段与数字技术对大脑这个由上百亿个神经元构成的复杂网络进行干预,以创设虚拟图景的方式操控人类社会,是90年代以来欧美“赛博格”科幻电影常有的情境。最具代表性的有《黑客帝国》(1999)与《盗梦空间》(2010)。
《黑客帝国》(1999)上映于1999年,充满了世纪末的怅惘与焦灼。这部影片引人深思的不仅仅是人与“非人”的地位翻转: 人类的身体被封锁在一个小小的玻璃柜似的生产单位里,生命活动所产生的电能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人工智能,就像人类曾对“非人”所实施的暴虐褫夺。更让人震惊的则是在这场翻转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工智能所实施的精细化虚拟化操控: 他们将人类的精神投射到矩阵空间,在自由的幻象中,进行专制的统治与奴役。以至于尼奥在初知真相时疯狂抗拒,试图回到矩阵“母体”,而业已摆脱“母体”控制的雷根,则无法面对沉重的真实,宁可让身体回到活体发电厂,让灵魂重入矩阵,在电脑操控的梦幻世界里了此一生。可见,人工智能专制统治的触须已深入人类的每一根神经。
如果说《黑客帝国》(1999)中的人类,在人工智能操控的矩阵中成为囚徒,那么,到了2010年的《盗梦空间》(2010),则是人类在自己构建的梦幻空间里困守愁城。道姆是一个老到的盗梦者,善于潜入他人的潜意识盗取商业机密。然而,在一次次对未知梦境的无尽探索中,妻子梅尔因为被他植入“此处非现实”的意念而在返还现实世界后自杀身亡,道姆被视为杀妻嫌犯而亡命天涯。商业大亨斋藤以让道姆回家为交换条件,让道姆在斋藤对手(一位垄断型能源帝国的主宰者)的儿子费舍的潜意识中植入“解散公司”的意念。道姆组建盗梦团队,在逐层递进、纵横交错的梦空间里,终于成功植入意念,如愿以偿回到家中。然而,团聚时刻,道姆眼见永不停歇的旋转陀螺,惊觉此处仍是梦境。
这似乎是一个人类意志无处不在的梦空间。有筑梦师阿德里安负责空间布局与建筑的设计,有前哨者亚瑟负责前期的资料搜集与侦查工作,有提供强力安眠的药剂师佑沭确保梦境的稳定,当然还有道姆作为总设计师的全面布局,细致安排,临危应变,生成一个多层梦境逐级递进、多人共梦互动影响的立体控制模型。即使如此,这个由多重信息回路组成的资讯系统,依然运行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制法则,在影片中,这些法则以隐喻的方式呈现:
资讯系统还凭借严密的把守机制确保其专制构型。《黑客帝国》(1999)里的特工程序,无时无刻地逡巡矩阵空间,将不符合程序要求的“异类”清除殆尽,而《盗梦空间》(2010)里针对费舍的植入行动是要破坏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式能源帝国的存续,因此,《盗梦空间》(2010)里的道姆与《黑客帝国》(1999)中的尼奥一样都是在对抗某种形式的专制社会。尽管为了博取观众的认同,故事中的主人公道姆也被赋予正义性,然而费舍的潜意识里有许多把守者,当盗梦者入侵,这个把守机制立即开始工作,阻挠盗梦者的行为,潜入意识越深,则把守愈加严密,从暴雨如注的追车枪战,到冰封世界中的重兵把守,无不体现矩阵空间的专制构型之严整。
资讯系统凭借传播机制推行其专制意志。《黑客帝国》(1999)中主人公是在与自己外部的“母体”进行对抗,“母体”掌控一切,甚至要在人体中植入窃听装置,只有进行暴烈的对抗才能将其摧毁。而《盗梦空间》(2010)中的主人公却是利用意识观念生成的唯一性,也就是专制性,来达到目的,但是意识观念的传播机制并不像工具一样可以随意放下,影片主人公看似取得了胜利,但资讯生成的专制性依然可以将其隔离于现实而不自知。
不论是《黑客帝国》(1999)中的“母体”,还是《盗梦空间》(2010)中的“把守”抑或“植入”,都是影片作者批评的对象。不论哪种目的、哪种形态的专制,都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内部世界生成的专制观念与外部世界生成的专制社会一样可怕,都会把人逼到生不如死的痛苦之中。由此可以引申出: 人类社会也是由信息控制论建构的赛博空间,资讯作为此间的根本力量,主导了各种利益取向,掌控了一切能量规则,将人类破碎飘摇的主体玩弄于控制论所定义的场域之中。
(二) “民主”式乌托邦想象空间
通过反乌托邦式梦幻空间的立体景观,科幻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人类社会在现代科技的操控中陷于专制的渊薮。“现代技术体系自诞生以来就展现出推动整个世界前进、促进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变革、创造新的人的生存境况的巨大力量,整个世界日益被技术支配和裹挟。”(16)陈飞.技术与人的存在——阿伦特技术哲学探微[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02): 108-114.然而,为了“避免坠入人类危机的修辞窠臼之中”(17)[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53.,在刻板冷战思维的引导下,另一些试图构建“民主”式乌托邦想象空间的欧美“赛博格”科幻电影,也同时呈现在近三十年的银幕上。
《阿凡达》(2009)是其中试图探寻“革命性的社会与崭新的未来时代”(18)林建光,李育霖,Hayles N.K.等.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M].台中: 国立中兴大学华艺艺术出版社,2013: 19.的超越之作,探讨了在高科技发展的情境中构建“民主”式乌托邦空间的新的可能。剧中,杰克是下肢瘫痪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作为人类的间谍,操纵着“阿凡达”身体,进入潘多拉星球的纳威部族,却爱上了纳威公主,并被万物和谐沟通的纳威世界深深吸引,背叛了自己的同类。当杰克率纳威战士竭力反抗,仍无法应对人类军队的利炮之时,纳威的神祇伊娃发挥其“万物互联”的优势,协助杰克打败了人类军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爱上对手的好莱坞爱情故事。然而,如此解读并未触及影片的精髓。实质上,本片真正要传达的是: 运行于天然“万物互联网”之中的未来人类社会在与仍处于信息互联网时代的当下人类社会的对决中,虽历尽艰险,终获胜利。
影片不遗余力地把潘多拉星球构建为一个天然而迅捷的“万物互联网”。先是让女科学家格瑞斯做详尽的介绍:“(潘多拉星球的万物)存在着某种电化学信号的交流,像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一样,每棵树与相邻的树之间的连接点有‘十的四次方’之多,而潘多拉星球上,树的数量是‘十的十二次方’,因而,所有树之间的连接点比人类大脑的突触还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系统,纳威人就是一个个站点,可以随时上传与下载信息,包括(储存在网络系统中的先人的)记忆。”而潘多拉星球引得地球人垂涎的Unobtanium矿——一种常温超导体,则在物质环境上支持了“万物互联网”的运行。
随后,借夸奇上校之口说明纳威人的身体特质:“纳威人身体的骨骼中含有纯天然的碳纤维。”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纳威人的身体成为“万物互联网”中的可移动站点。因为,这种由碳元素组成的特种纤维,能导电、导热,能够让每一位纳威人具备随时接通“物联网”、即时上传下载信息的功能,同时让所有的纳威人与潘多拉星球的一切生物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互联”共同体。正如剧中科学家马克斯·帕特尔博士所说的那样:“伊娃(纳威人之神)是由所有生命体组成的。”这个被命名为“伊娃”的圣母,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物联能量网”,将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连为一体,并精确计算能量的分配,使之均衡流动。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影片描述了这种天然“万物互联”的方式: 如纳威人征服坐骑伊卡兰(ikran)时,两者必须通过“神经鞭”来互相沟通,确认协同关系;纳威人时时刻刻与潘多拉星球无处不在的网络相连,影片十分形象地采用纳威人脚下绽开的光电之花,表明他们的联网状态。
揭开神秘主义的面纱,本片深藏的是网络时代的数据主义。这个名副其实的“万物互联网”所具有的超时空链接、极速上传下载的传输特性,让潘多拉星球成为导演所构想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有机、全球信息网络”(19)Magerstädt, S. Body, Soul and Cyberspace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Cinema: Virtual Worlds and Ethical Problem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2.。
因此,这并非一场潘多拉星球的纳威始族部落人对当代地球智人的战争,而是已进阶至有机“万物互联网”的纳威社会,在信息传输极度自由的乌托邦空间里,战胜了信息处理能力相对滞后的地球人社会。如果说,“民主和专制在本质上是两套关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对立机制”(20)[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338.的话,《阿凡达》(2009)中纳威社会打破电子算法与生化算法的隔阂,即时收集并处理信息的机制,则是“民主”式乌托邦社会愿景的极致表达。
上述经典“赛博格”科幻巨制,触及了技术和社会构型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曾提出:“技术能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特定形式?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21)[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5.
结语
一直以来,科幻电影不仅张扬技术发展之风尚,更是开启人文理念之先河,“艺术经常捕捉新出现的科学进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科学发现的启蒙和灵感的来源。但最重要的是,艺术的表现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自己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的途径。科幻电影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它们试图通过表现未来的镜头来把握今天令人费解的东西”。(22)Gerdes, A.IT-ethical issues in sci-fi film within the timeline of the Ethicomp conference series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2015,13(3/4): 314-325.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经典“赛博格”科幻电影讨论灵与肉的关系,讨论主体的消弭与重建,“并非赞成人、人性、身体的消弭,而是要在后人类时代重新定义‘人’,重新找回‘人’的意义”(23)Hayles, N.K.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M].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9: 24.。最终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不是我们的生物或技术设施,而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同情感、同理心、希望和爱。这些“赛博格”科幻巨制在消解并质疑人之身体、人之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主体的意义,探寻崭新的社会构型,不啻为一场“数字化文艺复兴运动”(24)[美]托马斯·A·奥汉年,[美]迈克尔·E·菲利普斯.数字化电影制片[M].施正宁,译.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 2.詹姆斯·卡梅隆为该书所撰写的前言中,提出了关于“数字化文艺复兴”的观点。。在当下人工智能的热潮中,“赛博格”科幻电影所呈现的迷人旅程与思维盛宴,对探寻电影在“审美娱乐之外探讨严肃社会问题”及深刻哲思的可能性,“拓展电影艺术文化广袤的发展空间”(25)潘汝.艺术之美与灵魂之思: 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研究[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5.,深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