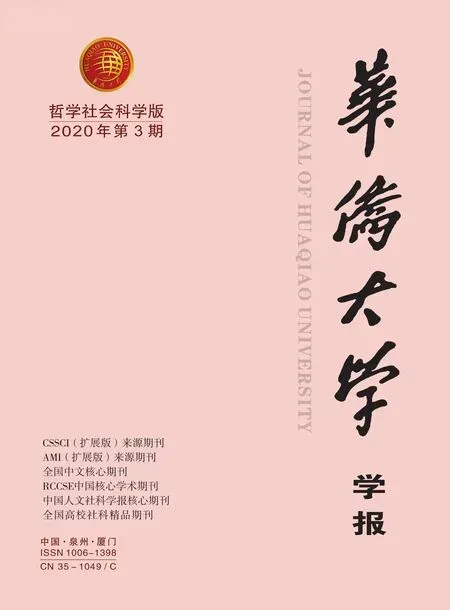康德地理人类学的多元整体主义文化观
○刘 晨
康德一生的理论关切是复杂多样的,地理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却常常被忽视的方面。他曾投入相当多的精力研究和讲授这门学科,因而有学者将他誉为“西方思想中关注地理学的专业哲学家的杰出典范”(1)Joseph A. May,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 p.3.。在这门学科中,康德从哲学的视角考察了世界各地处于不同地理境况中的人类,形成一门独特的“地理人类学”。本文的工作是梳理康德地理人类学中关于人类的地域差异与共同命运的理论,并阐发其中蕴含的一种可被称作“多元整体主义”的文化观念,以冀对我们当下思考人类的文化与发展问题有所助益。
一 康德的地理人类学
从就职后不久一直到退休,康德几乎每年都定期开设两门课程:“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学”。他在1775年的一次课程预告中表示,两门课程的共同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种知识的纲要,以帮助他们“按照规则整理所有未来的经验”。这些经验划分为两个领域:自然和人,它们分别是两门课程的对象。(2)[德]康德:《论人的不同种族》,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6页。
但以“自然”为对象的地理学并非完全无涉于“人”。在1802年出版的讲稿汇编《自然地理学》中,上述两个对象被更具体地规定为:“自然”是“作为外部感官对象的世界”,“人或者灵魂”是“作为内部感官对象的世界”;“人类学教给我们对人的知识,我们把对自然的知识归于自然地理学”。(3)[德]康德:《自然地理学》,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可见,作为地理学对象的“自然”并非指一切非人的事物,而是指一切作为外部感官对象的事物,后者也包括以外部感官来观察的人类。
所以毫不奇怪,康德的自然地理学课程广泛涉及人类主题。例如,在1757年的《自然地理学课程(纲要与预告)》中,康德指出,“对地球的考察”(即广义的地理学)主要有三种:数学的考察、政治的考察和自然地理学。第一种是对地球整体的抽象几何学研究,第二种考察“了解各个民族、人们彼此之间由于政府形式和行动以及相互的利害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宗教、习俗等等”,这显然是典型的人类学研究。即使是以“地球的自然特性以及地球上有什么”为对象、因而看似与人类无关的第三种考察,也把人列为地球上的存在物之一。(4)[德]康德:《自然地理学课程(纲要与预告)》,《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4页。并且,康德在此表示,地理学课程的目标之一是“说明人们出自自己所生活的地带的爱好,说明他们的成见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这一切都能够有助于使人更切实地了解自己”。(5)[德]康德:《自然地理学课程(纲要与预告)》,第10页。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人类”在康德的地理学课程中“扮演着突出角色”;就其都显著地包含人类主题而言,地理学和人类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重叠。(6)Robert B. Louden, Kant’s Human Being: Essays on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5-126.
当然,不应忽视“自然地理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观察人类的视角差异。人类在康德哲学的不同语境里拥有不同的身份。在纯粹哲学中,人类是无差别的、纯粹的理性主体。与之相对,经验性哲学则考虑到人类的以下被给定的事实,即它始终生活在经验世界之中、始终受感性的影响,因此这里的人类是现实的、不纯粹的、在其经验性条件中的主体。康德将“人类学”课程定位为“实用人类学”,它“关涉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使自己成为或者能够并且应当使自己成为什么的研究”(7)[德]康德:《实用人类学》,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而在地理学中的人类主题上,康德则是就人类与其地理条件的关系来规定它。这门学科以人类的以下地理境况为前提,即人类居住在地球表面的不同地理区域、被各自的地理环境所影响。这一境况使人类获得其最主要的经验性身份之一:作为地球居民的理性主体。从纯粹哲学到实用人类学与地理学、从“无差别的、纯粹的理性主体”到“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与“作为地球居民的理性主体”,康德对人类的多维规定表明他的哲学充分尊重人类身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一个无身体的人类主体,到一个扎根的人类主体,思想中的这一转变至关重要”。(8)Davi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 in Reading Kant’s Geography, edited by Stuart Elden & Eduardo Mendiet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1, p.271.
康德曾将“实用人类学”区别于“生理学的人类学”,后者“关涉大自然使人成为什么的研究”。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这个表述,即不是将它理解为人类具有何种生物学特性,而是理解为人类由于在大自然中(或地球上)居于不同的地域、从而在生理和文化上演化出怎样的差异化特征,那么这就是康德地理学中关于人类的研究内容。在生理方面,康德研究了人类自然属性的地域差异,其中主要是他用多篇论文讨论的“种族”问题;在文化方面,正如上文提及的,他研究了世界各地的居民在个性、道德、政治等方面的多元性。总之,关于人类,康德地理学研究的是它由于受所处地域的地理条件影响而产生的种种空间差异。
应当注意的是,康德强调人类对地球的扎根性并非是对人类的贬低。尽管他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把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事物归为共属于一个自然系统的“地面自身所包含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里单纯就其自然属性来看待人类、将人类降格到动物的水平。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共性尽管是既定事实,但并不是康德的地理学真正要强调的。人类在康德那里始终首要的是自由的理性存在者。在地理学中,康德只是通过突出人类的地理属性来表明它不仅是纯粹的理性主体,而且现实地拥有身体性和对地球的扎根性,它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因素的影响。(9)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表示,“自然系统中的人(作为现象的人、有理性的动物)是一种意义不大的存在者,与其余作为大地产品的动物具有共同的价值”。但他在这里如此贬低人作为大地上的存在者的身份,只是因为人还可以“作为人格来看,亦即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理性的主体”。([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4—445页。)相较于人作为道德的主体而具有一种绝对的内在价值而言,人作为大地上的存在者当然是“意义不大”的。然而,如果在康德哲学的其他语境中、例如在自然目的论中看,人的“大地上的存在者”的身份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康德哲学中的人类拥有“作为地球居民的理性主体”的身份,这一身份在他的地理学中得到关注和研究。他的地理学包含一种“地理人类学”,其总体任务是考察作为人类存在要素之一的地理境况,即研究人类由于分布在地球上不同的地理单元、受各自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呈现的地域差异。
二 人类的地域差异
康德是以一名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地理人类学的,因此他并不意在详尽考察各种地理对象,因为这超出哲学的任务范围。但包括地理人类学在内的整个地理学由于是一门经验性学科,因此又不能像纯粹哲学那样以先天的方式来研究。可见,康德的地理人类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要审视康德关于人类地域差异的论述,首先必须确定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这决定着他是以何种视角来审视、以何种结构来框定各地人类的差异化特征的。解决这个问题后,我们就可以梳理康德在这种方法论中对人类地域差异的具体描绘。
如上文所述,“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学”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准备好面对包括自然和人在内的一切未来经验。但课程本身并不直接提供这些经验,而是预先给出这些经验的纲要,以便学生将来填补入知识的杂多部分。因此,地理学和实用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不是详尽的知识细节,而是体系性的知识框架。所以康德指出,在这里自然和人“必须以宇宙论的方式来考虑,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它们的对象各自包含的值得注意的东西(物理学和经验心理学),而是按照它们处身于其中且每一个都在其中获得自己位置的关系使我们注意的东西来考虑。”(10)[德]康德:《论人的不同种族》,第456页。康德之所以把这种方式叫做“宇宙论的”,是因为在形而上学语境里,“宇宙论”是指对世界整体的研究,并且形而学家们相信,世界之中诸事物通过普遍的联结而构成一个整体,每个事物都以某种方式在这个世界整体结构之中拥有自身的位置。例如,沃尔夫定义道,世界“乃是流变事物的一个集合,这些事物相互邻近、依次跟随,并且在整体上互相关联。”(11)沃尔夫:《德意志形而上学》,转引自Eric Watkins, Kant’s Third Analogy of Experienc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94, p.88.鲍姆加登也指出,世界之中的事物“每一个都与整体相关联,并且因而每一部分都与另一部分相关联”,因此,世界包含“一种各部分间的联结和一种普遍的和谐”。(12)Alexander Baumg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s,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translated by Courtney D. Fugate & John Hymer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167.在康德这里,宇宙论地思考,意味着不是首先关注对象自身,而是从整体性视野出发,关注对象在一个整体框架结构中的独特位置以及它与结构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就地理学而言,经验的整体就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亦即整个地球表面空间。“这里所说的是世界知识,据此也说的是对整个地球的描述”(13)[德]康德:《自然地理学》,第160页。。整个地球表面空间就是构成地理学知识框架的基本质料。康德要求“以宇宙论的方式”思考地理学,就是要求在整体上、结构化地认识地球和它表面的事物。按照劳登(Robert B. Louden)的说法,就是要获得“对自然的整全感”(an overall sense of nature)(14)Robert B. Louden, Kant’s Human Being: Essays on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p.124.。同样,地理人类学中的人类及其地域差异也应该“以宇宙论的方式”思考,这意味着不能孤立地分析某个地区的人类状况,更不能将地域性的人类状况看作是普遍的,而应当运用全球性的视野,指明不同地区的人类各自的特征和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共同构成的多元整体。以宇宙论的方式研究人类地域差异,借用康德的说法,就是绘制一幅“人类的大地图”(15)[德]康德:《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15页。。
现在可以来看康德是如何具体绘制这幅“地图”的。由于“自然地理学”是康德地理学课程最主要的内容,因此,对于人类地域差异,康德探讨最多的是人类随空间分布而相异的自然属性,其中被最深入研究的则是人的种族差异。(16)一些学者指出,康德是“种族”概念的发明者。(参见Robert Bernasconi, “Who Invented the Concept of Race?Kant’s Role in the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Race, edited by Robert Bernasconi, Oxford: Blackwell, 2001, pp.11-36; Mark Larrimore, “Race,Freedom and the Fall in Steffens and Kant”, in The German Invention of Race,edited by Sara Eigen & Mark Larrimo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91-120.)《自然地理学》把种族问题置于“论人”一章的开端,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康德看来种族所决定的人类的肤色和其他身体性状是人的所有属性中最具有物质性、最无法被自由选择、因而是最突出地反映人在地理因素前的被动性的一种。
康德将人类划分为四大种族:白人种族、黑人种族、匈奴种族、印度种族(17)当代一些重要的理论挑战这种传统的种族观念,它们否认种族区分的真实性,或者将种族观念描述为缺乏生物学基础而仅仅是社会建构的。(参见Ron Mallon, “Race:Normative, Not Metaphysical or Semantic”, Ethics, vol.116, no.3, 2006, pp.525-551.)但这些讨论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发掘康德的种族观念背后的哲学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但他的种族理论更值得关注的是“种族”这个概念的定义,即“同一个祖源的动物的族群差别,如果它是必然遗传的话”(18)[德]康德:《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这个定义包含种族概念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同源”,二是“差异”。
所有种族都出自同一祖源,是康德对种族的关键论断之一。这是从一个事实推断出来的,即不同种族之间具有生殖关系的亲缘性,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有多大,任何两个有生殖能力的异性人类个体都能交配繁育出同样具有生殖能力的健康后代。这表明,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属于一个自然类,否则不同种族的人就会像不同类的动物那样存在生殖隔离。由于同一个自然类的动物都演化自同一个祖源,那么就可以推断,不同种族的人类都属于一个唯一的祖源,它们的不同性状是从共同的原始性状中变异而来。康德种族理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有关种族差异的形成。他提出一种“胚芽理论”,即认为,祖源人类身上包含一种原初的、综合性的“胚芽”(或“自然禀赋”),当他们迁徙到不同的地域之后,各地气候的差异促使“胚芽”中包含的诸多性状的可能性分化开来,其中有助于人类适应当地气候的性状成为显性的,而其他性状逐渐退化为隐性的。如此经过长期的繁衍,各地人类便形成不同种族,它们之间的差别通过“必然遗传”而固定下来。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胚芽理论”并非一种建立在实证证据之上的生物学理论,而是一种从现存结果出发、按照一定原则反推出来的目的论。其次,不同于通常观点,康德认为地理环境尽管是持久种族形成的刺激因素,却并非决定因素。的确,特定环境激发原始综合性状在特定方向上的显隐分化,然而,在康德眼中种族的起源是大自然有目的的主动规划,而非机械的被动生成。人类凭借自然禀赋主动适应环境,而非被动地被环境所改造。实际上,这两点与后文将阐释的康德种族理论的哲学背景有关。
在“种族”这种最具“地理性”的人类地理境况之后,康德按照人超脱环境和身体等基本的感性因素而趋近文化的程度讨论了其他一些随地域而相异的人类自然属性。在这些自然属性中,首先是各个民族的体态和体质,其次是各个民族对如何装饰自己身体的不同喜好(这似乎是审美活动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的起源),以及各地人们的食物差异,再次是“人在其鉴赏方面的彼此偏离”。这里讨论的“鉴赏”远未达到只包含纯粹的、无利害的愉悦的美的判断,而仅仅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混杂着快适的“对普遍使感官满意的东西”的判断。如果说纯粹鉴赏具有对一切主体来说无差别的普遍性,那么康德的地理人类学就表明,不纯粹的鉴赏具有显而易见的地域性,一个地方“极其多的东西都基于成见”(19)[德]康德:《自然地理学》,第318页。。
另外,在康德看来,人的文化属性也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他认为不同地区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道德和个性、“法律同样与土地和居民的性状相关”“神学原则根据土地的差异多半经历了很根本的变化”等等。(20)[德]康德:《自然地理学》,第166页。他还强调语言差异的文化意义,认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使民族的概念更澄明”,民族语言的教育则有助于培养和保持本民族的个性。(21)[德]康德:《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威尔克的<立陶宛语德语—德语立陶宛语词典>笔记》,《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458页。
总之,正如康德所预先规划的一样,他的地理人类学从宇宙论的视角构造了一幅全球范围内人类地域差异的整体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人类分布在地球上的不同区域,在各自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不同种族和其他各具特色的性状,这些具有不同性状的居民共同构成一个互相差异又相互关联的广阔整体。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人类地域差异的论述是按照从身体到精神、从感官享受到文化成就的渐进顺序来进行的。这种安排与下文即将论述的康德地理人类学的自然目的论背景有关。
三 人类的共同命运
上述康德对人类地域差异的规定只是横向的,换言之,人类随地域分布而呈现多元属性只是一种空间性描绘。但实际上,康德将这种横向规定嵌套在一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后者就是人类共同趋向其完善性的发展进步。这一点需要通过康德地理人类学的哲学背景(即自然目的论)来阐明。
我们可以从种族问题入手来阐述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上文引述的他对种族概念的定义只表明种族是什么,但他对此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定位,即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概念,而非一个“自然描述”的概念。康德指出,对自然的经验性(非单纯思辨的)研究可以是“物理学”的,也可以是“形而上学”的。前者单纯基于经验的证明根据,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而后者“先天地由纯粹实践理性来规定”,从而让我们在对自然“纯然经验性的摸索”中增添“一个指导的原则”,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在自然中找到“合目的的东西”。前者就是“自然描述”的研究,后者就是“自然历史”的研究。在“自然描述”中,我们由知性的原则所主宰,通过观察来构建自然的“图志”,而在“自然历史”中,我们根据反思性判断力的原则,通过反思来构建自然的“谱系”(22)[德]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运用》,《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58—161页。。举例来说,观察一个物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物构造是“自然描述”的,而说明它的构造在向着更高的完善性进化就是“自然历史”的。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我们可以在自然中寻找到物种构造的实证证据,但在哪里也找不到“进化”这个东西,因为它作为一种合目的的、有方向的运动源自人的理性,是人为了在一定的秩序中理解自然而加于自身的反思性概念,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自然目的论概念。
康德认为,“种族”概念完全是一个自然历史的或自然目的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自然描述的概念,换言之,“人分为不同的种族”不是一个实证陈述,而是一个目的论的陈述。“[种族]这个词根本不处在一个自然描述的体系中,因此,就连[这个]事物本身也或许不在自然中的任何地方”。(23)[德]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运用》,第162页。我们把人类区分为不同种族的正当理由不是可以在自然中观察到的实证证据,而是由目的概念引导着,把不同组别的变异性状设想为具有一个共同的祖源并置于同一个合乎目的的自然历史进程之中,然后才反过来把特定的身体性状的看成天然地属于特定种族的。种族“只是理性如何才能把生育中的极大多样性与血统的极大统一性结合起来的理念”(24)[德]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运用》,第163页。。这表明,严格来说,在一个静态的时间横截面上是不存在种族这回事的,它只存在于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即人类沿着统一与多元的引线的进化之中。
按照自然目的论,自然界可以被看作处在一个向上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展示了这个进程。在其中,一切无生命的事物,例如土地、水、气候等,都是大自然为了让有机体在其上生长繁衍而有意创造的。有机体就是自然的目的,而所有自然事物构成一个指向有机体的巨大目的系统。由于包括有机体在内的整个自然界又是为了人类能够加以利用,因此,“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创造的最后目的”(2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6页。。但并非人类的任何活动都足以使其称得上自然的最后目的。康德认为,“只有文化才可以是我们有理由考虑到人类而归之于自然的最后目的”(2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20页。,这是因为唯独通过文化,尤其是通过艺术和科学,人类才培养起对超自然的更高目的(即道德的人)的适应性,从而为人性的提升铺平道路。这样我们看到,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一般生命到人类,从人类幸福到人类文化,这些自然所能提供的东西中存在一个由低向高的发展秩序。当然,在这个进化系统中,康德最关注的还是人类的发展。他认为,人类的发展目标是“完全地并且合乎目的地展开”自身被赋予的理性禀赋,尽可能褪去身上的动物性,“仅仅分享他不用本能,通过自己的理性为自己带来的幸福或者完善”。(27)[德]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25—26页。而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科学和艺术,由于可以使人为成为道德主体做好准备,因此是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中介。
在《判断力批判》中,上述人类朝向完善性的发展进程所依据的是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概念,这一概念是先天的,并不涉及人类的经验性境况,因此发展进程对所有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类来说是共同的。任何人类,无论他所处的具体条件如何,都无一例外地处于自然的目的论系统和人类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可以说,朝向完善性的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如果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只是论证了人类具有共同命运的可能性条件,并勾勒出人类发展进程的大体框架,那么他的经验性哲学则填补了这一进程中更多的细节,即分析了现实的人所处的种种经验性境况对其发展的促进或阻碍。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他的地理人类学表明,人类发展的共同命运与它的地理境况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尽管人类拥有共同命运的可能性基于先天原则,不能从地理人类学中寻找,但地理人类学却能告诉我们经验生活中的人类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现实地应当如何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从康德根据目的论原则所确立的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反观他的地理人类学,重构出他书写的一部作为地球居民的人类的发展史——这部历史的开端是祖源人类原始的同一状态,同时大自然在祖源人类身上植入综合而可塑的“胚芽”,这是人类日后得以分化和进化的原初禀赋。在人类迁徙到不同地域后,地理环境触发原本单一的“胚芽”展开,同时,有利于适应环境的性状也在遗传中融合定型,种族差异由此产生。大自然将人类分化为不同种族,以便人类能够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中居住和繁衍生息,从而尽可能广阔地分布到地球表面的所有地域。“人是为整个地球创造的”(28)[德]康德:《自然地理学》,第238页。,它注定要遍布各个地域(29)有学者注意到,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一元论是康德人类进化理论的源头之一。(Mark Larrimore, “Antinomies of Race: Diversity and Destiny in Kant”, Patterns of Prejudice, vol.42, no.4-5, 2008, p.346.)实际上康德的“人类注定遍布地球”的思想同样在圣经中有其根源。。而大自然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人类由于地域的隔绝,通过世代积累培育出不同的地方习性,进而形成尽可能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但文化的多元性还不是这部历史的终结。地理隔绝既是多元文化形成的契机,又是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文化的多元性同时意味着每一种文化的有限性。为了克服这种有限性,便利的地理要素使人类能够建立商路和航道,让不同的文化彼此碰撞。(30)康德特别看重商业贸易对于人类文化交往的意义,认为“贸易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使人文雅,并且建立人们彼此之间的相识”。([德]康德:《自然地理学》,第166页。)这一点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同时面临退潮危机的今天尤具启发意味。文化的交往一方面通过扩展人的视野而使其理解其他文化,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来使其反思自身,从而强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的互相理解和自我确认使每一种文化得以发展,又使它们超越差异而在更高的水平上融合,最终突破地域限制而促成整个人类在全球尺度上的共同发展。
拉里摩尔(Mark Larrimore)认为,康德地理学是“一个……对理解人类的命运至关重要的领域”(31)Mark Larrimore, “Antinomies of Race: Diversity and Destiny in Kant”, p.343.。在自然目的论视野中,康德书写了一部大自然把人类播撒到地球表面各处以促成它的发展,最终实现文化和道德的完善性的历史,这部发展史就是大自然施加在全人类身上的共同命运。
四 全球文化的多元整体主义
康德认为,人类的文化是自然的最后目的。上文的分析表明,在康德地理人类学中,各地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既是人类形成地域差异的目的,又是人类发展进步、成就其共同命运的重要中介。因此,“多元文化”是康德地理人类学隐含的一个核心观念,对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
大自然为了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借助地理因素形成人类的地域分隔和文化差异,这决定了人类历史不是单线(单一文化)延伸的,而是呈现为多线(多元文化)交织推进的形态。因此,康德地理人类学包含一种文化多元主义。但同时,这种文化多元主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即存在于多元文化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康德把不同的地域文化纳入同一个历史性进程中,认为人类在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同时也拥有一种共同命运,即趋向其完善性的发展,因此, 历史尽管必然落实在不同文化各自的进路中,却不是无方向的,而是隐含一个出自目的论原则的、向上发展的演进秩序。在康德看来,人类命定地同时具有文化形态的差异性和历史方向的同一性,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康德地理人类学中一种充满张力的文化多元主义。
由于其对文化差异作为人类命运的强调,康德地理人类学也许会让当代许多持文化多元主义观点的学者产生共鸣。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人们日益摒弃整体性的叙事模式,转而越来越青睐多元甚至分裂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在事物的历史性开端被建立的不是它们的起源不可侵犯的同一性,而是与其他事物的不和。是不一致。”(32)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42.“差异是创世或生产的唯一原则。”(33)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57.然而,如果考虑到康德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判断,考虑到在他那里文化的多元化远非是首要原则,而仅仅是成就人类朝向完善性发展的共同命运的环节,那么这种后现代理论可以说与康德地理人类学是很少有重合的。
相比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晚近一些温和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与康德更加接近。这些温和的文化多元主义者认为单纯的分裂和单纯的一致都不符合一种良好的文化主体间模式。他们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提倡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和互动,试图以此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废墟上重建普遍价值。哈贝马斯是这些学者中突出的一位。他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34)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29页。,因此他提出“交往行动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处理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坚持“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35)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第32页。这种“在差异中建立同一”的理论诉求也体现在弗里德·达尔迈亚(Fred Dallmayr)的“整体多元主义”(Integral Pluralism)中。达尔迈亚运用“一”与“多”的不同方式的搭配,建构出文化的四种“理想模型”:1.整体的或全面的一元论(integral or holistic monism),即“所有事物都在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庇护之下,统一在‘一’之中”;2.整体的、静止的二元论(integral and static dualism),即“假设一种本质性的极性(心灵—物质、主体—客体、自我—他者),被看作‘一’的内在分裂”;3.任意的分散或多元化(random dispersal or pluralization),即“统一被完全放弃,由一种激进的‘多’和分裂来取代”;4.整体多元主义(integral pluralism),即“关注生成的联结或关联”。(36)Fred Dallmayr, Integral Pluralism: Beyond Culture Wars,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p.15.在达尔迈亚看来,他所主张的第四种类型是最为可取的,因为它强调跨文化互动,进而“自下而上”地产生普遍价值,因此既可以避免传统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自上而下”强加的结构,又可以避免极端多元化导致的原子主义。哈贝马斯对文化差异与同一的处理同样符合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联系到康德,我们可以大体上把他看做一名与哈贝马斯和达尔迈亚一样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甚至可以借用达尔迈亚的术语,把康德地理人类学中的多元文化观念同样理解为一种“整体多元主义”,因为它坚持人类文化同时保持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必要。
然而,康德与“温和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之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别。在连接文化的差异与同一的方式上,如果说哈贝马斯和达尔迈亚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进路,是“在差异中寻求同一”,那么康德采取的就是“自上而下”的进路,是“为同一而要求差异”。对哈贝马斯和达尔迈亚而言,文化的差异性是首要原则,任何超越差异性的先天秩序在他们看来都是损害多元性的危险力量,因而是被摒弃的。他们所要求的同一性仅限于文化主体间的平等地位和对话理性,而这只是维持一种民主的文化主体间结构,防止多元主义堕落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需要。相反,对康德而言,多元文化之上的人类共同命运才是首要的,促成全人类趋向其完善性的发展进步才是他的地理人类学中的多元文化观念最终的诉求。为这种共同命运奠基的目的论原则是源自理性的先天立法。这一原则尽管并非是对历史的规定性原则,却作为反思性原则范导性地决定着人类对历史的整体理解,使历史具有超越当下偶然性的必然秩序。在目的论原则的基础上,历史呈现出确定的方向性,即人类从野蛮到文明、从幸福到道德的提升。而文化的多元化只是大自然为促成全球人类发展进步的必要手段:通过文化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冲突,人类内在的理性禀赋才能逐渐被唤醒和展开,最终各个文化主体在更高的水平上趋向同一,成为道德的人类整体。由于康德把人类共同命运的权重置于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地域差异之上,因此,与其把他的多元文化观念叫做“整体多元主义”,不如叫做“多元整体主义”。
我们有理由推断,与哈贝马斯和达尔迈亚强调文化间的平等不同,康德眼中的多元文化之间存在等级秩序,因为根据他建立在目的论之上的人类共同命运,必定有的文化类型在某些方面更加接近完善性,有的文化类型在某些方面距离完善性更远。大自然让人类演化出多元的文化类型,不仅是为了让文化主体互相交流融合,而且是为了在不同文化的互相比较中显明何种品质是相对进步的、何种品质是相对落后的。由于坚持这一等级秩序的存在,康德的地理人类学有一点备受后人诟病,这就是他发表的某些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例如他认为:“人类就其最大的完善性而言在于白人种族。黄皮肤的印第安人的才能已经较小。黑人就低得多,而最低的是一部分美洲部落”(37)[德]康德:《自然地理学》,第314—315页。“最热地带的所有居民都特别懒惰”(38)[德]康德:《自然地理学》,第315页。等等。
这些言论诚然带有明显的偏见,然而,如果我们推测它们背后的原则,就仍然可以从中拯救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康德所坚持的多元文化之间的等级秩序不是基于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基于以文化和道德的完善性为目标的进步理念。后者超越特定的族群,而仅仅基于普遍的目的论原则。康德贬低的从来不是非白人种族本身,而是人类对良好品质的背离,例如懒惰、鉴赏力的缺乏、精神的无力、迷信、奴性、不服管教、犹豫不决、残害身体等精神和行为上的陋习。尽管他仅仅根据不甚可靠的经验认为这些陋习在非白人种族身上更为常见,但他从来不认为白人种族可以天然避免。所以,就其思想意图而言,康德是试图通过文化间的等级秩序提出一种进步的要求,以此敦促各个文化主体彼此对照和反观自身,从而在文化和道德上竞相向上攀登。正如福赖尔森(Patrick R. Frierson)所说,应当把康德对某些种族或民族的负面描述理解为“对道德力量的劝诫,而非对无法摆脱的劣等性的标记”(39)Patrick R. Frierson, What is the Human Being?,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111.。根据康德的多元整体主义文化观念,一个民族应当努力提升自身的文明高度,只有这样它才能进入历史中的伟大民族之列。
公允而言,比起康德,当代温和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对文化多样性的态度更显开放和宽容。他们的理论有助于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某些文化困境,例如他们为弥合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加剧的宗教和伦理冲突提供了思想资源,并且呼吁保护文化多样性,鼓励人们更多地关注非西方的或边缘的文化族群。在他们看来,一种基于目的论、坚信人类共同命运、呼吁人性提升的文化观念如今是不合时宜的。但实际上,康德地理人类学中的这种并非以跨文化的对话,而是以全人类的发展为旨归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康德在目的论的基础上把文化多元主义与人类进步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样,他按照更高的标准,对各个文化主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我们固然应当宽容他者,但更应当发展自身;固然应当在多元文化中寻求身份认同,但更应当在与文化和道德完善性的比较中建立自己的谦卑与荣耀。这种对每一种文化主体都毫无例外的鞭策意图是我们在当代许多文化多元主义者那里难以见到的,但显然,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这样的声音。
综上所述,康德在其地理人类学中表明,人类是作为地球居民的理性主体,它的命运与其地理境况紧密交织。他从宇宙论的角度展示了人类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从目的论的角度展示了人类在历史目标上的同一性。人类的差异化分布是大自然的意图,其目的是形成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再通过多元文化的交往融合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成就其趋向文化和道德完善性的共同命运。上述理论蕴含一种可被称为“多元整体主义”的文化观念:一方面,多元文化的差异与交往对于人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人类整体的共同命运才是首要的,多元文化只是成就共同命运的手段。与当代主流的文化多元主义相比,康德的多元整体主义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和现实意义,即可以更有力地鞭策每一种文化主体致力于自身文明高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