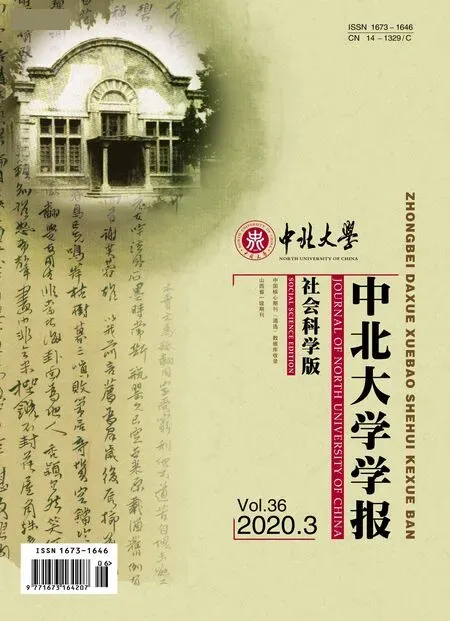近代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探析
郭进萍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江苏 苏州 215131)
红十字标志是红十字文化的物化载体,时人对此有生动的描述:“每当佩着红十字标帜的朋友显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生动地难以忘记地记起法西斯魔手的罪恶,争取‘人性’斗争的胜利也越发鼓舞着我!”[1]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是透视红十字文化传播成效的一扇窗口。大体而言,近代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排拒到接纳继而滥用的过程。
1 排拒:因形似基督教标志
红十字标志是集体约定俗成的结果,本无宗教上之意义,“只因第一次会议开于瑞士,特以表敬意于瑞士,且瑞士为永久中立国,乃与红十字条约目的相合之国,故用瑞士之国旗而反其色,易红地白十字为白地红十字,成为红十字会之标记。”然而因为红十字标志与基督教的红十字架标志形似,一些伊斯兰国家难以接受,认为此标记是对穆斯林的亵渎,故而用红新月标志代之。日本则称红十字会为赤十字社,且“曩昔之日人,以其十字之标记,多误会红十字事业为基督教之事业”[2]。
不独伊斯兰国家和日本如此,中国亦然。当红十字会登陆中国后,“一般不明根底的人们,每一看见红十字,即联想到它的象征意义,耶稣钉十字架而死”[3]。据此,民众往往将红十字标志与以红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教相联系。
1918年,荆襄战起。为救护战场伤病兵和受战火波及的民众,沙市天主堂的传教士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号称天主堂红十字会,其经费由长沙市绅董捐集。该会征得入会会员百余人,“制有徽章旗帜,书明天主堂红十字会字样,或佩身上,或悬门前,以期保护”[4]。天主堂红十字会成立后,即收容医治南军受伤兵士百余名。然而该会却遭到社会人士的非议,有自称沙市红十字会会员名萧英者表示反对,并在《大公报》刊登《教堂设会敛财之黑幕》一文,诬捏四条登之报章,称:
该堂组织斯会之初,既不曰万国缔盟红十字会,更不曰万国红十字分会,而独标曰天主堂红十字会。天主堂红十字之木牌遍钉街衢,于法律上不合者一也;匿藏溃兵武器,靳不交出,欲交出又索相当之代价,于条约上破坏者二也;当战事正盛之时,引渡灾民,辄索重金,否则掉头不顾,于条约上破坏者三也;出发队员每藉十字名义,诈欺取财,该堂主教充耳不闻,于条约上破坏者四也。[5]
该文一经登载即引发轩然大波。荆州总司铎马修德闻悉后,当即照会沙市商会,针对萧英的说辞一一反驳,声称天主堂发起红十字会,“乃体上主爱人之德,念基督救世之心,原非专为名誉起见,但任意诬蔑,将以阻后来办理慈善之心”,并请求沙市商会查明“沙市红十字会设于何地,成于何时,创于何人,其会员确有萧英与否”,以便天主堂与萧英交涉,“为赔偿名誉之举,是为至要”[6]。其后,沙市商会查明“沙市红十字会尚未成立,亦无会员萧英名目,其为冒名捏诬情形显然”。于是,沙市商会致函《大公报》,将沙市天主堂红十字会成立的来龙去脉悉数道来,并对萧英所诬蔑的几条再次予以批驳和澄清,强调该会“其款项公任之,其用途公定之,其账目亦公同监督之,并未募化会外人捐款,亦未由天主堂三司铎经手。”[7]此外,沙市商会还通函各报馆登载更正,恢复天主堂红十字会名誉。至此,该事件水落石出。萧英对沙市天主堂红十字会的指摘,纯系捏造污蔑,这既有损红会声誉,也折射出红十字会与基督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时人对基督教的排拒心理。
直至20、30年代,国人将红十字标志与基督教相联系的看法依然层见叠出。1920年,孟司铎在四川省武胜县红十字会的成立仪式上宣讲道,红十字会始于欧西,“其旗帜上书一大红十字者,系记耶稣昔日曾藉十字圣架,舍身救人,倾流圣血也”[8]。不单宗教界人士如此认知,一般民众也持类似看法。1921年,时人在谈到红十字会的命名原因时直言,“红十字者,西方救主耶稣丁(钉)于十字架上救世流血之一大纪念也。故西国凡有义举,一以红十字为标识”[9]。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红十字会系统中竟也有人将红十字标志与基督教相联系。1922年,红十字会常议员金邦平在演说中称“红十字会根据耶稣舍己爱人,流血十字架而发生,凡红会职员,当思耶稣杀人成仁之宗旨”[10]。
这样的认知对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不无窒碍。华侨联合会委员林有壬就曾撰文呼吁取消中国红十字会。在他看来:
我国除最少数人外,均与耶稣风马牛不相及,即无取“十”字以名我国中最大慈善团体之理由。若强名之,是贬吾国为基督教征服国,强吾国最大多数同胞崇拜其所不愿拜之“十”字;反基督教之爱国青年,或且因反对“十”字而波及红会;其不知“十”字历史者,将视十字旗章为毫无意义,无以启其景仰赞助之忱;于红会发展前途,不无妨碍。[11]
“各国红十字会之宗旨,在乎维持人道。”[11]为此,他建议改用白底“人”字旗,提议政府将红十字会易名为“中国人道会”,并洋洋洒洒地述说了易名的种种益处:
以“人”字之简明,外人见之,亦易辨认;于国际战争时之救护,绝无困难。近顷宗教势力日衰,人道主义将起而代之,易“十”字为“人”字,非特可以表现吾族爱护人类之决心,亦可警醒世界沉迷宗教之痼疾。国内外同胞热心慈善事业者,不感“被征服于异族异教”之苦,其捐输必更踊跃。[11]
林有壬对红十字标志的排拒潜藏着他对宗教侵略以及“被征服于异族异教”的忧虑。这种忧虑情绪普遍弥漫在近代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
近代中国,伴随基督教的大规模涌入,中国人的反教、排教情绪一浪高过一浪,教案频发即是明证。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国人的反教情状作了这样一番概述:大抵“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兵藉端攘夺,无故肇衅”[12]591。传教士明恩溥对此也颇有同感,直言“湖南省的排外文字如洪水泛滥,其中充满各种恶意的诽谤,试图以此引起一场动乱,好把洋鬼子逐出天朝”,并分析了这种攻击出现的原因“部分是出于误解,部分是出于一种民族仇恨”[13]97。
在近代国人反教、排教的历史语境下,红十字文化走近中国。而红十字标志与基督教十字架之间的形似则直接导致它被国人排拒的境遇。尤其是在被视为晚清教案高潮的庚子义和团事件中,红十字会更是受到排拒乃至危害,诚如史料所载:“中国无知愚氓,昧此主义,曾于庚子之变,联军入京之际,义和团匪时有炮击红十字会之事。”[14]
2 接纳:基于护身符效应
红十字标志具有保护和标明作用。战火纷飞时代,伴随着红十字文化传播实践的开展,红十字标志逐渐被国人所接纳。
对普通民众而言,能在动荡的时局中保全身家性命是他们最渴望也最迫切的需求。而加入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即可为身家性命提供一个“保护伞”。1911年,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在征集会员广告中即以红十字标志的护身符作用吸引民众入会,强调会员佩戴红十字徽章“不特赞襄义举,抑且保卫己身,一举而两善备焉”[15]。红十字刊物也大力宣扬:世道乱离变迁之时,惟红十字会“乃能引之出险而保护其身体之健康,惟入红十字会之人乃能自保其身家,勿见疑于军士,勿见俘于敌人”[16]。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红十字的护身符效应对普通民众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为保身家平安,许多民众选择缴纳会费,成为红十字会的一员。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频发,政府威信陵替。当时军队风纪败坏,估拉佚役,强占民房,成为普遍现象。宜宾红十字分会曾炳文以理事长身份,商得驻军长官同意,凡是会员住宅贴有红十字分会标记的,一律不住军队;戴有红十字分会符号的,一律不拉佚役。风声所播,数月之间,自愿捐资25元取得会员资格者,达200余人。还有部分人捐资1 000元成为荣誉会员,捐资200元为特别会员者。[17]76震泽红十字会于1924年的一度发展也是因为“一时风传,入会者可保一身一家”,故“纷纷入会者达百余人”[18]。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息县。息县红十字分会成立后,发展会员有300人左右。这些民众入会的动机也同样是基于“一人入会,全家平安”的诉求:
当时入会的会员,均发有红十字会会旗(布质)一面,每日早晨插在大门口的左上边;还发有红十字会会章(当时叫金针银牌)一枚,可佩带在自己的左胸前外衣上;另外,还发有红十字会袖章(系布质的),白底红十字,带在自己的外衣左臂上。以后还印发有红十字会会员门牌,是一大张厚纸印制的。中间直行写的大字是:万国联盟中国红十字会会员门牌,直行字的两边还印有“博爱恤兵”四个大横字(一边两字),下面还有说明的几行小字。这个门牌都贴在特制的木板上,挂在住宅的大门左上边,与会旗上下映照。
在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官兵,来往行军,多住在居民的住宅内。凡门前挂有红十字会会旗和红十字会会员门牌的住户,国军官兵不去住。官兵也能自觉地遵守红十字会有关章程的规定。[19]81-82
抗战时期,红十字标志的护身符效应被进一步放大。据时人的认知:在当时,只要扛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就有人身安全。“即使残暴成性的日军,瞪着充满怀疑的目光看着它也奈何不得。”[20]152只要会员门口或分会机构门口插有红十字会的会旗,那么“就连日本人也不得进入”[21]48。在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人们认为,只要钉上红十字会门牌,就可能避免战争的灾难”[22]88。
这种将红十字标志视为护身符的心理是近代处于战火连绵境况下的广大民众的普遍心理。民众接纳红十字标志继而入会,除“保身家平安”的诉求外,还有不少是出于免征壮丁、享受医药优惠等方面的动机。
尽管在开展各种业务活动时,红十字会员所付出的劳务,都是无代价、无工资的义务工作。但红十字会员也享有一些权利,比如“凡加入红十字会的会员,可免征壮丁”[23]48。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曾发文通知全国,凡在红十字会工作的青年人,可免于抽壮丁,这样红十字会便成了“壮丁保护伞”。麻城红十字会成立后,宋埠、铁门、中驿、白果、城关等地区的青年都纷纷参加该会。闵集乡有一个红十字会会员被抓去当壮丁,县红会急电报告南京总会,很快得到南京复电,指定麻城县政府予以释放。这样,入会的人就更多了。[24]155-156另外,入会会员还可享受一定的福利。息县分会曾规定,凡入会的会员,凭证件均可到息县红十字会医院或外地红十字会医院就诊,可享受免费待遇或减收医疗费用。故入会的人员,也就逐渐增多。[25]82
总体而言,接纳红十字标志进而加入红十字会的民众,“与其说是认同作为舶来品的人道主义,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乱世求安的考虑”[26]85。
3 滥用:基于光环效应
由于红十字标志特有的光环效应,与民众对此标志接纳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各界对这一标志的普遍滥用。大体而言,“满足安全需要,谋求认同、标明身份,获取经济利益是国人使用红十字标识的主要动机”[26]28。
3.1 假冒红十字会名义骗募捐款
红十字作为救护团体应有的识别标志,本身具有神圣性。近代红十字会在民众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其尊重人道、博爱恤兵的宗旨,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但它也极易被不法之徒或有心之人利用来谋取私利。
比如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甚嚣尘上,叠见报端。据资料显示,社会人士曹桂卿以九龙镇红十字会分局医生王正平的名义在社会上骗捐,“佯称善于治病,骗去洋卅元”[27]。社会人士沙淦用红十字名义募捐,又有新闸浜北共和路协兴衚衕(胡同)会内诸某假冒红十字会名义募捐。[28]在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不法行为中,甚至出现了“夫妻档”骗捐的现象。社会人士曹鼎钟和周召南系夫妻,二人打着南京红十字会筹办高等医学校的名义在爪哇泗水和芜湖等地分别骗捐,极大地危害了红十字会的名誉。为此,中国红十字会咨请内政部“严饬周召南等取销红十字会名称,以惩撞骗而杜影射”[29]。
伴随抗日战争的烽烟,社会上盗用滥用红十字会名义以募捐渔利的行为愈发猖獗,红十字会冀察绥区办事处即是一例。该会打着“营救战线伤亡”的旗号,派会员边子和等持函前往劝募。事后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查核证实“本会并无冀察绥区办事处之组织,显系有人假冒名义意图渔利”[30],函请政府严加取缔。又如安徽人卞宏钧,“专假童子军及红十字会名义,在四处募捐自肥”,先后以伤兵和红十字会第二难民医院代表的身份到处骗捐,后被拘获,以诈欺提起公诉。[31]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不仅妨碍红会信誉,而且害及难胞。
3.2 滥用红十字标志谋求身份认同
辛亥革命时期,据统计红十字会先后成立分会65处,“大彰于武汉之师”,然据会长吕海寰的观察:“辛亥以后,风会所趋,各立门户,假慈善之名称,开权利之渊薮,既不听总会之节制,遂致轶救济之范围。”[32]可见时人成立分会之动机鱼龙混杂。更有甚者,“有树红十字旗帜从事疗伤,将其伤愈之兵,居然备文送回队伍,以结好于营官,或有树红十字旗帜,收容少数伤人,以为自身免遭兵祸之保障者,凡此不但破坏公约,其离红十字会救护主义亦甚远矣”[33]。
民国成立后,发生数起社会团体滥用红十字标志的事件。影响较大者有上海法界大马路救护团假冒红十字会的名义募捐,南京一女子救护团未经授权使用红十字标志请求军队保护,汉口人道总会滥用红十字标志触发救护等事件。对此,红十字会以有悖于红十字条约,妨害国际信誉为由,呈请政府一律取缔。[34]江浙战争期间,各种十字组织纷纷涌现,如红十字会、赤十字会、白十字会、蓝十字会等等,“大有遍地慈善之象”,遗憾的是,“队员良莠不齐,以慈善为名而行偷窃者有之,假公济私用以自保者有之,沽名钓誉藉以扩展势力者有之,利用十字图谋不德,增十字旗帜无量之秽点,可恨孰甚”[35]。
值得一提的是卫生机构和医药界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据资料显示,“国内各地卫生机构开业医师及药房等,普遍应用白底红十字符号已有数十年之历史,揆其动机,似袭本会博爱服务之旨,未可厚非,然对条约信守,实属大悖”。红十字会曾多次呈请政府取缔,政府亦三令五申饬禁有案,“惟医药各界习用红十字已久,严予取消,实难澈底”。有鉴于此,红十字会不得不函请经济部商标局禁止用红十字为货品之商标或标记,并以世界各国的潮流为例,建议“医师以绿十字,药房以蓝十字为符号”[36],获得了一些响应。
3.3 冒用红十字标志非法从事军事活动
红十字标志具有保护性作用,“惟红十字人员得有往来各处及深入战地之殊权”。因之,在近代军队冒用红十字标志的行为数见不鲜。辛亥革命时期,张竹君的见闻即印证了这一点,“闻十字会中有为敌军间谍者,有冒名诓骗者,诸如此类,不可胜计”。此外,她还亲眼所见“有四人冒十字会名义为汉奸者”[37]。
1913年癸丑之役爆发后,军队中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甚嚣尘上。据报道,张勋之兵入城后,“城内满悬红十字旗号”[38]。有军队私造红十字旗、红十字袖章作侦探之事[39],“有某国人十三四名混用红十字会名义及旗号运送子弹约五万粒”[4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诚如资料所载:“红十字徽章,于战争时,往往有假之以侦查军事者,亦有非战斗员利用之以谋身体之安全者,其他种种之滥用,殆难悉数。”[41]
3.4 盗用红十字标志谋取商业利益
“红十字标志系为全世界红十字会所公有,其他个人或协会等,不得使用,更不得假冒此项红十字之符号及名称为商业或其他目的之用途。”[36]。尽管如此,商业机关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依然数见不鲜,永泰油行即是一例。
1929年,上海市四马路永泰油行公然发售红十字油,“各界无不乐用,每年运销国内外,数达万万”[42]。红十字会以永泰油行“违背日来佛红十字条约,以红十字为制造标”[43],危害中国红会国际声誉为由,致函内政部和工商部请求取缔,不准发卖,获得批准。尽管如此,永泰油行以曾在国民政府注册为辞,“仍以红十字为商标,抗不遵行”。红十字会无奈之余,延请律师函令取销。后由部饬商标局查复此项商标,“系前广东实业厅注册,不仅为商标法第二条第二款所不许,更有违犯日来佛红十字条约第八章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前广东实业厅贸然核准,殊属不合,除由部咨行广东省政府转饬建设厅,将该公司红十字油商标,尅日撤销,并通令各省市一律取缔”[44]。最终永泰油行将“樽颈绘有之红色十字删去,惟名称则一仍其旧,照常出售”[45]。这起纠纷反映了很多问题,永泰油行滥用红十字标志是国人红十字意识淡薄的体现,广东实业厅贸然核准红十字为商标却折射了政府对红十字标志保护意识的淡漠。
此外,还有假借红十字会名义谋取其他私利的。如1924年,社会人士曹人杰冒充红十字会会员贩运烟土,打着红十字会的名义“公然携带烟土,藉免沿途搜检”[46],影响十分恶劣。1929年,曾为红十字会名誉会员的马士伟,“以红十字会为护符,另组团体,名为一心堂”[47],旨在实现其政治野心。
这些负面现象严重损害了红十字会的声誉。江浙战争期间,浏河方面居民“每有谓红会人员扰及民间之说”[48]。非但如此,滥用现象还严重窒碍了红会工作的开展。庞京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因为社会上一般人的不知尊重红会,往往把红会旗帜,作不正当的用途,所以特区当局对伤兵的出入,时时发生很大的周折”[49]。这些现象折射出时人对红十字标志保护意识的淡薄。
应该说,对于滥用红十字标志的各种现象,中国红十字会是高度重视的,也力所能及地予以保护,然而各类滥用事件仍然屡禁不止。这与政府的漠视不无干系。对此,有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红十字标记之所以多年以来屡遭仿冒、滥用,主要是因为缺乏法律确实的保障。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根本不曾注意保护红十字标记的问题,国民政府时期虽然三令五申,以行政命令禁止滥用红十字标记,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由于缺乏罚则,以至于禁者自禁,民间仿冒、滥用者仍然不绝如缕……这不能不说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代表当时中国并未忠实履行日内瓦公约的规定。”[50]299
4 国人基于多元视角对红十字标志的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并非沿着排拒—接纳—滥用的轨迹线性发展,而是一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逐步深化,并打上了鲜明的本土化色彩。除了将红十字标志与基督教之十字架相联系的观感外,时人对红十字标志还有着其他多元的解读。
一是从传统文化中找寻与红十字标志榫接的资源。如《红十字月刊》在解读红十字标志时即称:“红是代表仁爱的象征,十字是具有牺牲救人的精神。不论红十字的定义是否如此解说,在一般人的心理上确是如此的反映。”[36]
二是从中西词源学的角度对红十字标志的含义进行解读。1921年,时人借亭从十字“一横一竖,东西南北皆备”的古文含义出发,指出红十字的精神即“以救主爱人如己之精神,贯澈(彻)于东西南北,即以东西南北之人互相团结其精神,而维持于不敝者也”[9],勉励全国民众积极赞助红会。与之相较,鹿门则从十字英文含义出发,指出:十字在西文里为cross,表示四通八达和普遍广大的意思,红色是表示热烈而博爱的意思。“十字而用红色,就表示用热烈的博爱的情感施于普遍广大的领域,是一种仁慈救济的意义。”[51]所以凡属于救济性质的团体或是个人,常用红十字做标记。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国人对红十字标志存在普遍的误读和滥用,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符号的多歧性。
三是从服务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解读红十字标志,这在抗战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如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政治部主任王洽民的眼里,红十字标识是“革命事业与革命人生观”的代表:红的颜色表示勇敢与热烈,这是革命事业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十字一纵一横,横是代表全体人类,纵是代表宇宙无穷,指示“救护工作必须自上至下自左至右,无所不至”。他呼吁佩戴红十字徽章的广大救护人员抱定革命人生观,“以最勇敢最热烈的革命精神,来从事于增进全体人类之生活、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的工作”[52]。这种看法在红会系统颇有代表性。
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多样解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十字标志的初始含义大相径庭,但却在无形中融化了异质文化间的坚冰,有助于国人的接纳。在战争年代,红十字标志带给了民众力量和希望,诚如时人所观察到的:
人类在演出相互厮杀的悲剧,使人感觉凄惨与冷酷,但在另一方面,在机声轧轧之下,在枪声隆隆之中,从血肉的深渊里,隐隐的望见几个红“十”字,挺起肩仔,与恶魔奋斗……这是如何伟大的事![53]
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深有同感:“红十字的标记,是人人所爱敬的,因为红十字会不是为自己谋什么,是为人群服务的,在目前一片纷扰的世界中,红十字的标记,确给我们唯一的一种希望。”[54]
5 结 论
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过程是透视红十字文化传播成效的一扇窗口。大体而言,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排拒到接纳继而滥用的过程。因形似基督教标志,在近代排教反教甚嚣尘上的时代背景中,红十字标志遭到了国人的排拒。因特有的护身符效应,在战火纷飞的岁月,红十字标志逐渐被国人接纳,以保身家平安。与之相伴,红十字标志特有的光环效应,又引发了国人的普遍滥用,或假冒红十字名义骗募捐款,或滥用红十字标志谋求身份认同,或冒用红十字标志非法从事军事活动,又抑或盗用红十字标志谋取商业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逐步深化,并作了多元解读。
符号与意义是相对分离的,诚如威尔伯·施拉姆等人所说:“符号不是完美无缺的工具。它们必须是从个人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因而“符号的含义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同”[55]72。近代国人对红十字标志的反馈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上文可知,红十字标志既使国人联想起西方基督教的侵略意味,也使国人看到近代西方的“文明”观念,同时还使国人意识到它的“护身符”功效以及光环效应。更有甚者,政治家还看到了红十字标志与革命精神的关联性。显然,红十字标志所引起的个人反应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个体长期积累的经验。因之,尽管传播者有意让红十字标志传递“人道保护”的讯息,希望接受者按照传播者的意向作出回应,但结果往往可能不尽人意。在这个意义上说,红十字标志问题恰如一面镜子,如实映射出了近代西方在中国的两重性(既是“先进文明的导师”,也是“霸权侵略的化身”[56]194)以及国人的复杂心态,也折射出中国红十字会事业的多元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