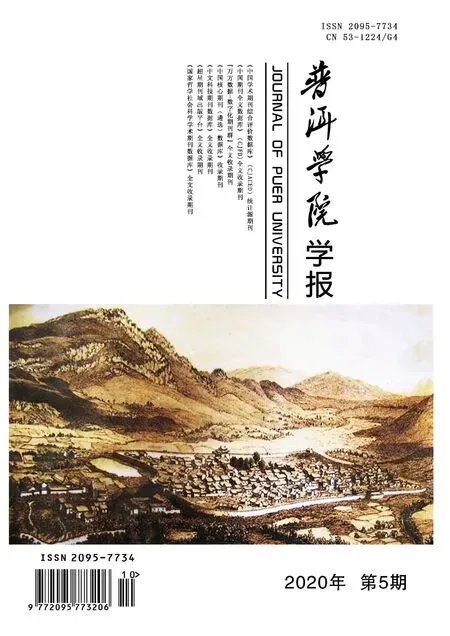《聊斋志异》的诗性叙事研究
伋 静,钱 敏
1.中共和县县委党校,安徽 和县238200;2.安庆师范大学,安徽 安庆246000
鲁迅先生在《小说史略》中指出,《聊斋志异》虽然写鬼写狐,讲魑魅魍魉之事,表人世离别怅惘之情,抒书生壮怀之意,然而叙次井然、描写委婉,用传奇法,言古今情,能将封建社会的人文、习俗及风尚,有机地融入到故事创作中,使故事在“志怪”的同时拥有抒情与批判的功能。胡适曾在相关文献中指出《聊斋志异》看似虚幻缥缈,却包含着蒲松龄对社会黑暗的愤怒、怨恨及对“风清气正”、“大同盛世”的期盼和向往。在很多短小精悍的故事及篇章中,我们能够发现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和“鬼魅”并非封建迷信的产物,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本土化的、平民化的、理想化的“精神”,譬如聂小倩的反叛精神、胡四娘的不屈精神及“鸦头”的孝廉精神等。这种物化的精神和思想能够在委婉动人和铿锵有力的叙事节奏中形成鲜明的主题意蕴,使《聊斋志异》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有效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蒲松龄常以“喜人谈鬼”、“雅爱搜鬼”自居,但他却反复感叹“知己者,常在黑塞青林之间”。所以《聊斋志异》的创作初衷是对作者人生理性和“孤愤”之情的寄托,虽然写鬼写妖,以鬼狐暗讽社会,然而在“剔骨挖讽”之间,又流露出书生特有的执着感和愤世情。
一、《聊斋志异》的情节化结构
小说叙事的本质是情节架构和人物编制,是通过构建特殊的“情境”,使读者感受到作者蕴含在情节中的思想及理念。亚里士多德曾在戏剧创作中指出,故事和情节并非相同的概念,两者间存在着鲜明的从属关系,即故事是记录事件发生顺序和演进历程的载体,而在事件记录的过程中却添加了一定的因果关系,形成了情节[1]。《聊斋志异》在开篇卷中通常以简短的叙事来记录“古怪”而“神秘”的事件,譬如《尸变》《考城隍》《耳中人》《山魈》《捉狐》等篇章,都是稀奇而古怪、神秘而莫测的志怪故事。胡适也曾说过《聊斋志异》的开篇作品的确为“志怪”之作,然而在情节建构与人物刻画中,却相对细腻、委婉。尤其在人物描写中,逐渐突破了传统志怪小说的窠臼,将人与物、事与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在《耳中人》一篇中,蒲松龄虽然没有交代事件的缘由,然而却将角色的情态、感知、思想生动地表达出来。如“小人闻之,意张皇,绕屋而转,如鼠失窟”这处,语句虽简短,几个动作却将角色的慌张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现代文学创作层面,情节化结构注重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注重角色情感和作者思想的融合与流露。这种创作理念和思想,我们能够在《聊斋志异》中窥见一二。譬如在《小二》中,角色的情感和思想是通过角色的肢体动作和所见所感表现出来的,如“女始着裤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该段文字详细地阐述了事件的发生过程,虽然简短,三个动词却给人以清晰的画面感,在情感表达上,“始着裤”生动地刻画出角色危急关头不忘自身形象的情感和性格。而在“孤愤”情感上,《聊斋志异》在情节架构上,可以表现出鲜明的片段化特征,能够凸显叙事情节的“应然”特质,表现出对“抒情传统”的发扬和“体认”。譬如以乐事、赏心、美景、良辰的行乐图卷,充分表达出作者的“乌托邦理想”[2]。部分学者曾从题材和内容的角度出发,将《聊斋志异》的故事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作了结合,将其界定为作者思想流露与发泄的载体,有对仕途的抱怨与迷惘,也有对自由、理想的畅想。在这个过程中,蒲松龄将自己的情感有机地融入到故事中,使其成为文章的主体,并借角色之口,将两种外化的情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鲜明的主体意蕴。通常来讲,诗化的叙事在于情感的抒发,是《聊斋志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关键。然而在志怪小说创作层面上,情感的表达与呈现,则需要情节作为载体和媒介,使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更有递进性和层次性。诗化叙事过程拥有明显的“片段化”特征,饱满而完整的情感,能够为《聊斋志异》的诗化叙事奠定了基础。
二、《聊斋志异》个人化叙事视角
《聊斋志异》的主观叙事和个人化视角主要表现在对乡间寒士的刻画上,将个人的偏好和好恶融入到情节编织和叙事的层面上,借此抒发个人的憎恨、愤懑及欲望。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和“伦理观点”,蒲松龄在处理个人情感及叙事思想的过程中,主要以两个角度出发。首先是对社会现实的传闻化、轶事化处理。蒲松龄在撰写《聊斋志异》的过程中,所涉及的题材较为宽广,不仅涉及贞妇、孝子、烈士、忠臣,更涉及兵政权谋、志怪传说,还涉及民间趣事和乡俗传说。《罗刹海事》便是包含了浓厚的异国风情的小品,而《山鬼》则从民间故事出发,将小人物、小事迹进行传闻化处理。在整体层面上,《聊斋志异》能够将明末清初的民变、灾害、饥荒、战争等社会政变和历史史实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也能够将个人志趣和理想抱负,有机地整合到文章的创作中。其中,《白莲教》便以个人志趣为出发点,或概述、或展示白莲教的兴起与沉浮,神秘与怪诞,使《白莲教》拥有了浓浓的神秘学色彩。其次在题材改写上,作者能够将主观情绪充分地宣泄出来,实现借文抒情的目的。根据相关研究调查显示,《聊斋志异》中约有25%的篇章是作者根据诗人笔记或前人杂著撰写成的,所以《聊斋志异》的诗化叙事又有“借鉴”的特征[3]。与原始故事相比较《聊斋志异》的叙述语言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化特质,譬如《续黄粱》便是以《枕中记》作为故事原型撰写而成,根据《唐国史补》能够发现《枕中记》中的黄粱梦拥有较强的“寓言特征”,能够表达作者的悲悯情怀和人生感悟。而《续黄粱》则将《枕中记》的主题变换为对贪官污吏的报应和惩处,用浓重笔墨描绘冥报场景,以此彰显作者的激愤情感及深思静观的理性精神。
个人化视角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首先情节叙事的主观性,在小说创作中,主要有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等常规视角,还有介入式第一人称视角。其中介入式视角主要指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描写角色的心理、动作及情感,使小说叙事更加多样化、多元化、层次化、立体化。我国古代的志怪小说和言情小说,主要以第三人称为主要叙事视角,通过角色塑造和情节叙事,充分地将小说角色的情感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在《聊斋志异》中,人们却能够发现明显的介入式第三人称视角痕迹。作者虽然以客观的角度来概括并描写角色和事件,然而在细节描写中却能够将角色思想情感有机地表现出来,使个人的主张和思想融入到角色刻画的过程中。譬如写贪官污吏的昏庸无道、写普通百姓的封建麻木等,这些都是在细节刻画的过程中将作者的主观情感呈现出来的。其次在题材的处理上,根据上文叙述,《聊斋志异》涉猎题材宽泛,能够将诗人的思想进行转换,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故事题材的处理上,更体现在作者凝练思想和观点等层面上。如在《花姑子》一篇中,蒲松龄将造成安幼舆和花姑子的悲剧,归因为封建礼教,归因为社会迂腐的思想及理念,然而在结局处理上,作者却以“伪圆满”结局点睛,提出文章的本质,并借此讽刺人性中的贪婪和迂腐。这种处理手法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能看到,然而这种借他人之口达自己之意,却充分契合了蒲松龄的处世观和价值观,是作者思想内化的现实表征。
三、《聊斋志异》的诗意化和虚幻
通常来讲,文学空间是虚构的物理空间,拥有较强的审美性、象征性和隐喻性特征,能够有效地表达和流露出创作者的所思所感,能够将客观现实以主观化的形式融入到小说叙事的过程中。在《聊斋志异》的叙事空间中,文化隐喻的叙事功能较为明显,能够将虚幻空间和拟实空间排除在外,注重“过滤现实要素”后的单纯性的、纯粹性的叙事载体。在这种叙事空间中,蒲松龄能够将角色进行“激情的演出”,使小说叙事成为诗性演绎的载体和映射。其中拟实空间主要指对社会现实的描绘和渗透,虚幻空间则指对事件的编织和罗列,过滤掉现实的纯粹性叙事空间,则指角色主观化的思想和现实。这种虚幻空间,能够使现实景物表露出较强的诗性特征,表现出作者的诗化思想。“山雨欲来风满楼”便是将山雨到来前的情景进行了拟人化处理,能够给人以别样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却是构建在主观化叙事的基础上的,是通过视角的感官化,将诗情画意完整地展现出来的。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出发,这种虚幻空间主要指创作者的“借物喻人”和“借景抒情”手法,使创作者的情感充分地映射在诗歌的创作与撰写过程中的[4]。
在《聊斋志异》中,虚幻空间主要体现在对周遭环境的描写上,这种描写突破了拟实空间和虚幻空间的限制,使人物情感和客观事物得到了充分的融合。简而言之,读者通过蒲松龄笔下的环境描写、景观描写,可以深入地了解角色所特有的思想和情感。部分学者和专家曾将这种包裹在景观描写下的“思想”或“情绪”称为隐喻,然而笔者却认为《聊斋志异》中的隐喻主要表现在虚拟空间中,表现在“洞府”“仙乡”“梦境”“地府”等层面上。这种境界的设置与构筑,铸就了《聊斋志异》的诗情隐喻。其中洞府、仙乡、梦境是角色渴望征服、逃脱时间流逝的诗情世界,因此在情节架构上,蒲松龄着重表现了现实世界和“仙乡洞府”的反差,通过仙界时光的流转映衬出“此生易逝”的情感,进而构建出氛围浓郁的“意境”。在这里“洞府”和“仙境”是“世外桃源”的象征,是逃脱世俗枷锁的表征,同时也是承载作者思想和情感的载体,能够有效地将作者的理想“物化”地表现出来。而这也是《聊斋志异》诗意化的重要体现,能够将小说叙事的情景转化为情感抒发的“意境”,而这种意境的表达与融合,又将成为读者获得“诗情画意”的载体,进而在隐喻和象征的过程中,使《聊斋志异》的人文性更加明显,更加鲜明[5]。仙乡偶遇题材是蒲松龄结合男女的柔情、自然的风光及人际的温馨,所流露出的文化气息,描绘的是喜闻乐见的普世愿望,浓缩了作者对人世间的感慨与苍茫。虽然在虚幻仙乡的过程中,蒲松龄能够通过想象和虚构的故事,体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逃避,然而在诗意景观的描写上,却将人生如梦的情感和思想,表达得酣畅淋漓,使仙乡场景更具有诗情、诗景和诗意。最后在语言层面上,《聊斋志异》的诗意化主要体现在句式和修辞上。纵览全文可发现,很多篇章多以三字、四字、七字为主,无论在情节叙事还是在语言描写上,都有较强的节奏感,部分篇章则以对仗、对偶、押韵等方式,使句式层次清晰,节奏强烈。尤其在场景叙事和语言描写等方面,这种简短的语言,能够极大地增强小说的意境感,使志怪小说拥有较强的诗歌性。艺术的精髓在于情感,无论是文学、绘画、建筑,还是音乐,都注重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而诗意性则指作者将情感进行放大,以语言和意境的形式将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其对隐含其中的思想进行更直观的体验。譬如观赏者只有在深入地观赏和体验作品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情感的共鸣,获得丰厚的审美体验。而《聊斋志异》的诗意叙事,则具体体现在意境构建、情感表达、画面呈现、思想抒发等层面,以此使读者在感受和体验虚拟世界、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的过程中,更好地感受到小说的审美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四、结语
《聊斋志异》拥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人文性及文学性,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负。在叙事结构和空间层面上,架构出艺术化的诗意空间,使小说的表层与深层有机地融合起来,演化成时空、视角、结构相结合的诗性特质,使蒲松龄的大同思想、人文关怀及道德理念更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