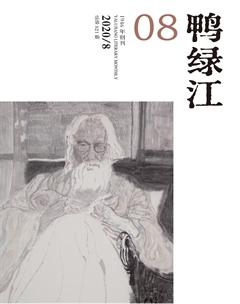那些小说中的人是些什么人(对谈)
陈培浩 王威廉 林为攀
1
陈培浩:本期我们先从林为攀的新作《方寸》说起。《方寸》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呈现了一个80后女作家工作中与90后同事的格格不入、家庭中对丈夫儿子的咄咄逼人。当然,小说中主人公对自己的行为也开始有所反省。我好奇的是,作为一个90后的男性作家,怎么会想到用80后女作家的视角来写作呢?创作这篇小说的缘起是什么?
林为攀:女性视角我一直很感兴趣,这些年也在小说中多有尝试,比如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梧桐栖龙》,便是以一个小女孩视角书写的儿童文学。我没有专门思考过女性视角的用意,也许与我的个人偏见有关。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假如能从女性视角出发,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看法。当然,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离不开复杂的人性,两者同样值得深究。创作这篇小说的缘起与其说跟女性视角有关,不如说是为我接下来创作一部都市长篇所做的前期工作。我很少写有关都市题材的小说,不管是短篇还是长篇。2020年以来,我觉得是时候迈出自己的舒适圈了——我自认为比较擅长乡土文学,尤其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我真正有时间静下来思考都市与人的关系。因此,我便先写了这个短篇,权当一种实验。
陈培浩:就写法而言,《方寸》前后很不一致。前面很长部分几乎是没有情节的,用的是一种概述的方式来描述主人公——一个化身公司前台的80后女作家眼中的90后女同事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描述只有情节的碎片,而没有真正的情节性。情节的实质是前因后果,是叙事的链条和动力,这些在前面的部分是完全没有的。一般来说,小说家不会在概述上花太多时间,因为这将影响故事的展开。常规叙事是在一定概述之后,叙事人就隐身了,让故事获得某种裸呈的效果。甚至有的小说家就追求自始至终那种电影化的呈现。《方寸》显然有着另一种尝试的冲动,我一开始还以为,《方寸》会是一篇完全由概述构成的小说。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后面写到主人公的家事时为什么又融入了一定的情节元素?
林为攀:陈老师关于小说概述与情节的看法很专业,的确如您所言,在小说中情节一般要大于概述,这甚至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看法。《方寸》的割裂性,就在于概述和情节几乎各占一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意为之,因为我写作一般要写完才能窥见全貌。写完重看时,我为这种割裂性找到了合法的外衣:后半部分的情节是为了补充前者的视线盲区,或者说前者是为了论证后者,两者的关系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有内在较为牢固的联系。如果要往更深处说,估计与我这些年形成的审美旨趣有关:喜欢把两种毫无关系的元素混搭起来,以此形成一种抓人眼球的陌生感与新奇感。
陈培浩:威廉,你对这个小说有什么样的观察?
王威廉:林为攀是一个出道颇早的90后作家,他这次的小说也很有意思,他竟然以一个80后女作家的视角来写小说。一个是80后,一个是女性,一个是作家,这三个要素实际上涵盖了这篇小说的某种趣味性。为攀出生于1990年,某种意义上,还是延续了80后的某些时代与生命元素,而女性则是他着力于转换视角想要发现新的叙事动力的一种尝试,那么作家则是他自身的职业。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搭配当中,既有陌生的领域,又有熟悉的领域,可能在写起来的时候,那种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平衡,那种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互相补充,也许会更加和谐一些,更加有把握一些。这个短篇小说本身是希望讲一个好故事的。相较而言,他对故事密度的这种重视,是这个短篇小说当中的亮点。能在“方寸”之地展开绵密的叙事,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两种不同的叙事模式,像是“方寸之内”与“方寸之外”的对话。
陈培浩:很多作家都提到这样一种感觉,创作短篇小说时,一下笔,语调感觉对了,小说就对了,往往一气呵成。我认为所谓语调对了,是指小说找到自身的语言。这涉及小说语言的发生学问题。有一类作家,其语言是高度风格化和个人化的,无论写什么样的小说,他/她都使用打上自身烙印的语言写作;另有一类作家,他/她的语言要更丰富,或者说随物赋形,这类作家的语言并不是凝固的,总是随着小说的主题、思想和风格而发生或大或小的调整。有的作家还没有意识到文学语言内在的复杂性,无论写什么都是那一套公共语言,这是等而下之的一種,可能连门都没进;另一种呢,语言具有高度的个性,他/她有能力让内容去适应其语言,所以也不用考虑语言调适的问题。大部分优秀作家,都会注意到小说内容不但在召唤它的形式,也在召唤它的语言。当这种语言没有找到时,写下的自然就语调不对。扯这么远,我想问为攀的是,《方寸》前后使用了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这中间你是如何进行调适的?你是否担心过它们之间的协调性问题?
林为攀:最近我跟朋友交流时,也讨论过类似问题,即小说的语言是否完全或有必要大于其他元素。众所周知,每个作家最显眼的武器首先就是语言,其次才是其他,因此打磨语言几乎要花费大部分时间。我跟朋友的交流虽然最后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我仍旧保留自己的看法:一个作家在写作初期可以在语言上多下功夫,但写到最后,绝不能再唯语言论,而是要让语言沉下去,让思想浮起来,倘若两者能形成一致,也就是语言没了雕琢感,我觉得才是臻于化境的表现。现在许多作家恨不得把语言玩出花来,一句话同时出现好几个眼花缭乱的比喻——这被外国学者斥为繁复的巴洛克风格。当然我也深知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几乎无法写作,他们需要在故纸堆里为自己搬出若干大师,进入到对方的语境中才能书写自己的故事。说起来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前辈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摆脱他们的影响,大部分作家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大师的阴影之下,充当一个廉价且不自知的文学中介。我在《方寸》中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说好听点,就是希望摆脱固有的文风——实不相瞒,我之前的诸多作品,深受马尔克斯的“荼毒”;说不好听点,是强迫自己转型,所以肯定会经历难熬的阵痛期,当然也担心它们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但我始终认为,与其借助大师的拐杖走路,莫不如自己学会行走,哪怕刚开始会顺拐。
陈培浩:威廉,你怎么看小说的语言发生学问题?
王威廉:语言是文学最基本的元素,作家在一起最常谈论的话题就是谁谁的语言特别好。在这里,我比较一下诗歌和小说的语言,我们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诗歌对于语言的要求,是在每一个很短的句子单位当中都要推陈出新,都要追求意义的密度;但是小说的语言,表面上要无限贴近日常生活,但需要突然从日常生活中飞起来,飞翔到一个很高超的地方。所以呢,小说叙事对于语言的要求在整体上是更大的,至少是更加全面的,而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小说家的语言普遍要弱于诗人的语言。因为语言并不仅仅是句子,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语言是一个整套的话语系统,对应着另外一个平行于世界的艺术空间,甚至艺术世界。那么,语言所承载的就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还要承载更多的它所关联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还有想象中的一切,以及要把这两者弥合在一起的那种焊接式的努力。但最终,所谓作家,是要创造出自己的这一整套语言体系。为攀有这样的语言自觉性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陈培浩:《方寸》的题目我是挺喜欢的,现代人就是被迫囚禁于方寸之地的人。比如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人,作为一个公司前台,就是一个被典型地规定了活动空间的人,每个人都是有限视角的人,但有的职业尤其如此。她的复杂性在于她同时还是一个作家,作家拥有观察的能力和书写的权利,所以我们通常相信作家是自由的。但《方寸》有意味之处在于,小说中那个作家身份的叙事人其实是被质疑的,由此它提示着:警惕心灵和视角的方寸化,对于拥有书写权利者同样如此。因此,“方寸”在小说中是有思想意味的。不过我好像不太喜欢小说后面的和解和温情化的东西。关于小说的结尾,为攀你是怎么考虑的?威廉你又怎么评价这篇小说的思想表达?
林为攀:“方寸”最开始的用意是疫情期间的足不出户、每个人都被迫关在家里,借助电子产品了解外界,虽然身处方寸之地,但视野跟疫情之前没有区别。我觉得作家并没有高人一等的观察能力和书写权利,很多时候,只是在抢夺热点的残羹剩饭,作家已无力书写这个复杂的社会,同样也无法挖掘复杂的人性,所以许多人转而继续在历史的土里“刨食”,哪怕书写历史的人可以塞满一个沙丁鱼罐头。关于小说的结尾,我恰好与陈老师持不同的看法,我很清楚结尾的温情可能会削弱小说的锐利,但正是因为温情,才有可能让前面的尖锐和反省站稳脚跟,否则这篇小说就不成立了。从叙事角度上说,这还能形成一种反差,或者是一种逆向反差,常见的反差是前面好、后面坏,这里剛好反过来,是前面的尖锐直接导致了后面的温情。
王威廉:我欣赏为攀将这种感受性的东西给具象化的写作。“方寸”这个汉语名词,它既是一个抽象的数量词,但同时又是具体的,涉及某种具体的场域,比如说,他设置的这个公司前台,就特别意味深长。尤其是置身在新冠疫情当中,每个人都被迫龟缩在自己的方寸之地,如果写作没有突破这种方寸的狭窄与局促,获得某种更宏大的视野,那么这样的写作是不是无效的?我想,为攀是有这种作为作家的焦虑。我对此也感同身受。因为在今天文学的存在已经饱受质疑,那么文学的写作必须超越人的身体所处的方寸之地,必须超越人的思想所在的方寸之地,一定要走到更加开阔的空间里面去理解此在的“方寸”。但这无疑是有难度的。正是对这种难度的体谅,让他在后面表现出了极大的温情。这让我突然心中有所动,此种温情不正是人与人之间超越了“方寸”的美好事物吗?都说有时作家要狠一点,但我想,作家终归是狠不起来的,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疫情时期。
2
陈培浩:为攀,说起来,在青年作家中,你也算成果颇丰的一位。谈谈你的写作历程吧。
林为攀:我19岁立志写作,迄今已有11年,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哪怕有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困顿,依旧矢志不移。现在想来也是很奇妙,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一个少年的执着?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或许跟我身无长物、无法从事其他行业有关。写作这十余年来——现在远不到盖棺定论之时,但不防趁机做一个小结——头三四年是真正的学徒期,“师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塞万提斯等西语文学大师,后来为了摆脱他们的影响,又把目光放到鲁迅、沈从文、老舍等中国作家身上,直到2016年写出一篇《御风》,我才算在某种意义上摆脱稚嫩的学徒期,当然,后面还是写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但至少有好几篇现在重看,仍拿得出手。这些年,我几乎交错创作中短篇和长篇,短篇是写长篇之前的休息,而长篇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力活儿,需要养精蓄锐才能开始。每当听人说写短篇和写长篇同等困难时,我都会忍不住发笑,因为我知道说这话的人肯定没写过长篇。我觉得写长篇是文学创作中最劳神的一项工程,它需要你同时具备专注、体力和坚持,而惰性始终都是它们最凶悍的敌人。
陈培浩:我知道你现在也参与编剧,还担任一本杂志的执行主编。这些工作跟小说写作构成了怎样的张力?
林为攀:这些工作目前跟小说写作既有关,又无关。之前编剧工作也曾影响过小说创作,直观表现为我在小说中也注重塑造人物和叙事,后来我就强行中断了这种影响,因为这两者看似都跟文字有关,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工种。我也是写剧本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作家跨行写剧本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比如福克纳,他为好莱坞写剧本,只是为了赚点快钱,以此反哺他的小说创作,至于写的剧本质量如何,好像没什么人提起,可见质量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也把写剧本当成一种谋生工具,除了受福克纳影响,也深知剧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合作的结果,需要你完全与市场看齐,这对一个有表达欲的作家来说,实在很难接受。好在经过几次所谓的磨合,我也找到了其中的窍门,即不管谁提的意见都全盘接受。果不其然,剧本写作便顺利多了,不管制片还是导演,都会夸你进步神速。每次开剧本会,无疑都是一场众生相,每个有话语权的人都争相提意见,哪怕意见狗屎不如。我为此感到很纳闷,编剧在影视圈的地位如此低下,为何又人人争做编剧?只要你以局外人角度出席此类会议,便会收获许多意外之喜,起码人性的角力你可以亲身体验到。因此,我每次写剧本都抱着这个目的,让自己一方面深陷局中,一方面又旁观者清。这个做法在今年给了我灵感,这也是我打算创作一本都市题材小说的契机,我决定以这些年的观察和亲历为蓝本,创作一本属于21世纪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对一个作家而言,任何经历都是宝贵的素材,就看你能否调动你的感官,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至于担任执行主编,情况就复杂多了,一方面我本身是一个写作者,深知写作的艰苦与不易,也知道每个作家都对自己的作品视如珍宝,不管写得怎么样,我都会站在一个编辑的角度给来稿者提出温和的建议,虽然这样有时会增加工作量,不过我认为也是值得的,毕竟每个大师都有学徒期,很少有人一上来便技惊四座,作家的生长期跟他将来有可能取得的成就同样珍贵。另一方面,看到眼前一亮的作品,则会非常有成就感,甚至有时比自己写出好作品还开心。作家写出一篇好作品是非常困难的,几乎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因为条件如此苛刻,所以注定无法量产,这也是海明威、福克纳等大师哪怕写了上百篇短篇小说,也仅有寥寥几篇流传后世的原因。我抱着对坏稿子多鼓励、对好稿子则不吝赞美的心态在干这份很有意义的工作,相信将来真如主编所言,“打造出一本中国版《纽约客》”。有时看到好稿子,出于一个创作者的尊严,也会激发“一比高低”的斗志。我认为这是一种良性竞争,是孤独的写作必不可少的强心针。
陈培浩:每一期我们都会请青年作家谈谈对他们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借此了解当年青年作家写作资源上的新变。也请谈谈你的写作资源。
林为攀:这里的写作资源准确地说应该是师承,我的师承除了刚才提过的,还有一个则是伍尔夫。就跟马尔克斯看到《达洛卫夫人》中的一段话让他后来“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我则在这本小说中学到了书写长篇的时间概念,即哪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人物里,也能写出万千气象——跟《方寸》这个题目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段震撼马尔克斯的话是这样的:“但是,毫无疑问,(车子)里面坐着的是个大人物:大人物遮掩着经过邦德街,凡夫俗子们伸手可及,他们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君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等到伦敦沦为一条杂草丛生的道路,这个星期三上午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人们全都变成了白骨,几枚婚戒散落其中,还有无数腐烂的牙齿里的黄金填塞物,好奇的文物学家翻检时间的废墟,才能弄清车里的人是谁。”
陈培浩:我们的栏目叫“新青年·新城市”,你如何理解写作的城市性呢?哪些城市文学作品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为攀:写作的城市性是书写城市还是在城市里书写?假如是前者,我尚在学习之中;如果是后者,我这些年都在城市里写作。《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用大卫雕像的小鸡鸡安慰菲茨杰拉德这一幕让我印象深刻。
3
陈培浩:《方寸》一开始重点是90后的办公室女性群像,后面重点则在第一人称叙事人——一个80后青年女作家。《方寸》不是一部以故事为中心的作品,但它与以往小说在写人的方法上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想不如就借此机会探讨小说与人物这个话题。无疑,塑造人物被视为小说写作中极其重要的元素,但韦勒克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俄国的批评家更集中注意主人公的问题,包括消极和积极的主人公。”南帆由是指出:“这种表述或许表明,更多的西方批评家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兴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至少,人物塑造不是文学唯一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批评家没有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示出足够的理论关注。他们的叙事学遗产多半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哲学与草蛇灰线、背面铺粉、横云断山、伏脉千里乃至无巧不成书等谋篇布局。很大程度上,这些概念论述的是情节的巧妙设置。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小说、戏曲评点多有涉及人物性格,然而,他们的赞叹仅此而已:这些人物的刻画性情各异、声口毕肖。”应该说,人物作为小说叙事核心要素这一判断具有特定的时空限制。比如说,中国古典小说中篇幅精短的笔记和传奇就无法支撑起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到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人物众多,长篇的体量也为人物命运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某种意义上说,以典型为核心的小说人物论是18世纪以来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物。中国古典小说的意义生发方式很多样,所以在人物这一范畴上寄寓的更多是形象化、感染力等审美诉求,而不是西方小说通过典型论建构起社会分析和批判的思想诉求。中国古典小说善于寥寥数笔勾勒人物的鲜明个性,因此夸张和对照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常用的手法。为使人物个性获得鲜明的辨析度,人物往往属于福斯特的“扁平型人物”,《三国演义》由此导致的夸张失真还被鲁迅讥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的此番讥评意味着他秉持的是18世纪以来西方叙事传统的评价尺度,一种将写实仿真作为小说重要追求的叙事传统。
西方小说以严密的叙事链条和架构为基础,西方小说这种“严密性”从观察方法上接近于使用透视法建立起来的素描,与严密的架构互为表里的是一种写实仿真的审美诉求。应该说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土壤而做出“圆型人物”和“扁平人物”的区分。鲁迅正是内化了这种写实仿真的叙事尺度,才会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提出非议。事实上,从中国民间对诸葛亮、刘备的熟悉来看,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极其成功的,只是这种“成功”逸出了西方小说人物论的评价坐标。以诸葛亮这个形象而言,这个神机妙算、未卜先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神奇人物极受民间欢迎,既因为诸葛亮身上所投射的忠诚、勤勉等儒家人臣的伦理价值在民间具有极深的文化土壤,更因为这个人物的神奇性与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审美一脉相承。诸葛亮作为一个奇人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人们追捧他是因为他具有万人莫及、万众敬仰的英雄性和唯一性,这种形象被塑造出来,既是为了读者惊叹,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崇拜心理。这是一种跟“现代性”格格不入的阅读心理,它在五四文化转型之际被鲁迅、胡适这样的新文化立场秉持者所唾弃是再自然不过了。
王威廉:中国古典艺术有着极强的“写意性”,也就是中国人在自己文化语境中的“意会”,从客观效果上论,也近似西方文论所说的象征表现。因此,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集中承载,所以新文化运动之际,当时的作家们把诸葛亮视为“妖怪”就不出奇了,这是文化语境被置换之后的误读。鲁迅一代人,开创了中国的现实主义,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人必须破除固有的文化语境来认清自己。但历史到了今天,又有了很多变化。在今天这样的处境中,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非模仿现实不可,“他”是谁有时甚至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为现代小说的真正主角。现代小说的主角都行动在一片黑暗当中,他自然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和一株绿色的榕树,但他的世界是雾霭遮蔽的毫无能见度的空间,他所谓的“看见”应该只是内心深处由意念凝结而成的道具。因为世界的整体性变得不那么容易一目了然地把握了,对于现实的模拟,反而会更加失真。
陈培浩:由此我们就发现了西方18世纪以来写实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差异处,中国小说人物尚奇,主角是最独一无二的个例;而18世纪以来的西方写实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它要的是从一个形象去靠近许许多多的平凡人,这正是典型论的来源。巴尔扎克说作为“典型”的人物,其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别林斯基认为“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西方18世纪以来的写实小说的“典型”意在解决一个个体与群体、特殊与一般的问题。不难发现,他们的立足点不在个体和特殊,而在群体和一般,甚至于,不能通向群体的个体、不能通向一般性的特殊性就会视为大大贬值。这里包含着一种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崛起、平民创造历史的史观转换和文学视点从英雄向普通人下移等诸多背景。鲁迅受这种典型观的影响,也便倡导“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人物塑造法:“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王威廉:中国古典文学是精英文学,所以书写的大多是才子佳人,里边的主角都属于普通人当中的优秀角色。而西方文学受到戏剧的影响,是让作为观众的普通人(不需要识字)来观赏周围这由一些普通人构成的世界,而精英们创造了这一切却隐居幕后,犹如他们信仰的上帝。这种差异性在今天依然值得关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包含着多种历史冲动,在文化语境置换之后,我们所要消灭的,或者说要压缩的,就是古典文学当中的神秘性、古典文学中的贵族性。而“拼凑”,则对应于普通人,或者说,对应于我们常说的“小人物”。有一点值得思考,用现实中不同的人作为元素,拼凑出一个形象,实际上它背后的逻辑已经远离了现实,是指向了虚构,因为这种拼凑还是要求虚构空间里面的逻辑自洽性。没有这种逻辑自洽,拼凑就失去了意义。我还想在此基础上说说今天文学的变化。我想起了电影《阿凡达》。人类为了殖民新的星球,他们将人类的DNA和Na'vi人的DNA结合在了一起,制造了克隆Na'vi人,这个克隆Na'vi人可以让人类的意识进驻其中,成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替身”。当然,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操控这个克隆Na'vi人,只有他的母体,也就是与其身上的人类DNA一致的人才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关系听起来很复杂,仔细想来却是很有趣味与深意的,那么能用来隐喻小说家和“面目模糊的他”(即他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吗?他是拥有小说家DNA的替身吗?他代替小说家在文本的星球上探索并受苦受难吗?好像有时候是,有时候又不是,他似乎不仅拥有小说家的DNA,而且还会将自己那部分独特的DNA“传染”到小说家身上。他们相互控制,相互拥有,相互渗入,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最终的结果是,他们都不再是自身,而变成了更为复杂的存在。
陈培浩:到了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塑造时典型论就失效了,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和《城堡》里的K都是非常著名的文学人物,但这两个人物塑造显然都不是以典型论为方法。现代主义小说的人物并不追求现实主义人物那种对现实的高仿效果,所以其优点不是血肉饱满,而是这个符号化人物身上某种特征被作家象征化了,所以它所使用的不是典型化的思维,而是象征化的思维。典型化处理的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象征化处理的却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通过象征,某个现象性的东西被引申而获得了对更丰富对象的代表性。我们会发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小说人物具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人物依然是小说非常值得勘探的领域。我们看到,《方寸》里面写人物,前半部分写的是群像,它没有将这些群像杂取化合为一个人物;后面部分写那个80后女作家,其意也不在典型,但是它也不是想通过这个人物来隐喻什么,而更像是使用一种转喻的思维,由这个人物转喻出与“方寸”相关的议题,我不知道这种写法算不算成功,且当作一种尝试吧。
王威廉:典型意味着秩序,而秩序在溃败,或者是在重构。因此,从卡夫卡开始,溃败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注定结局,小说家的努力只能体现在溃败的程度上,以及溃败的方式与最终的救赎上。神奇的是,溃败的发生并不是源自敌人的强大,而是敌人的隐蔽与不可知,就像卡夫卡的城堡,世界的荒凉本身就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吸引着你来挑战,然而并不与你过招,只是与你虚与委蛇。你没有见过对手的样子,更无法概括对手的性质,最终,挫败的发生完全体现在心理的崩裂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最为欣赏鲁迅先生提出的语汇:无物之阵。这四个简练的汉字所传达出的绝望与反绝望意识没有其他任何汉语语汇可以代替,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意识的小说并不能理解我们时代的处境。那么,在今天写作,必须迎着“无物之阵”去“顶硬上”,人物像与不像是一回事,但人物必须传达出置身于“无物之阵”中的状态与信息;如果提出高标准,那就是加上思想、情感与理解。为攀给我们呈现的“方寸”中的人物,可以肯定的是,还是传达出了那种“无物之阵”中的状态与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说,“方寸”也是“无物之阵”中的一种。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陈培浩,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特支人才计划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广东省作协签约评论家。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 《中国文学研究》《中国作家》《作家》《文艺报》《江汉学术》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论文多次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已出版《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互文与魔镜》《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岭东的叙事与抒情》等著作。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广东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
王威廉,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倒立生活》等,作品被翻译为英、韩、日、俄等文字。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語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广东鲁迅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