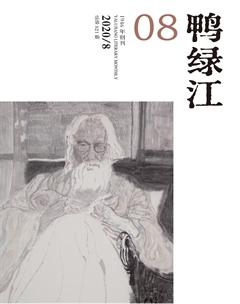与树终老
我看见了那些树。城市如水,不可避免地沉下去。涟漪渐消。水落树出,突兀于荒漠之中,散发着神性的光辉。
披着国际大都市的外衣,深圳的内核其实是城中村。深南大道、北环大道、滨海大道、宝安大道……蓝色的高楼大厦后面,城中村连接成片。有点前店后厂的意思。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对外整洁严谨,对内节俭鲜活。经过几十年的颠簸,大拆大建模式逐渐沉寂下来。低矮的城中村和光鲜的写字楼、综合体、商业小区各安其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对峙。
都有点累了。
处于劣势的城中村终于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喘息。它们如海上漂泊的小船,起起伏伏,时隐时现,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好在每条小舟上都有一只锚,重达千斤,可令其随时停下来。
此处的锚,就是榕树。
几乎每一个城中村里,都有一棵被崇拜的“神树”。说每一个,也许并不严谨。没人专门统计深圳有多少棵“神树”,但确实很多,时不时就会遇到。它们像一颗颗钉子,把这个繁忙的、随时要飞起来的都市紧紧地钉在大地上。
不同品种的榕树,大叶榕、小叶榕、橡皮榕、雀榕等,大同小异,都是阔大的阴凉。阳光七绕八绕要跳下地来,叶子摆阵阻挡,拉住它的腰带,使其悬于半空。
树干上拴着几条红布。四周围一圈低矮的栏杆,或木制,或钢制,栏杆内摆放着神像。一尺多高,彩塑。有的单供一菩萨,有的单供一关公。有的供着渡海的八仙,有的供财神爷。多数是放几个神像,菩萨、关公、财神爷坐一起,各收各的香火和祭品。更奇者,树下摆四五个关公像,或坐或站,或持刀,或捋髯,或呆萌,仿佛若干片段的拼接,一个人的一生集合于此。
原住民的崇拜是开放的,绝不偏执。凡是你能想到的神灵,天上的,地下的,海上的,河里的,钦定的,民间的,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神仙太多,各管一摊,都比凡人力量大,都能影响凡人的生活。随手一指,土坷垃就变成黄金。即使一时求不着,将来没准儿用得上。即使一辈子用不上,也不能得罪。虽帮不了你,但因为神通广大,分分钟置你于死地,伤害力有甚于“有求必应”,所以见神就拜准没错。
如此,也不需什么完备的教义。崇拜嘛,归结为一个词,即敬畏。烧香拜神,心中多存非分之想。这一部分,神仙能否满足,自古见仁见智。有所求的另一面是有怕。世俗中人,有个怕头,挺好。天不怕地不怕,也许才是最可怕的。
农耕社会,拜神乃百姓日常,如油盐酱醋,如吃喝拉撒。神在每个人的身边,深度介入具体生活,掌管各种生活禁忌:不能踩门槛,容易受穷;不能说瞎话,会烂嘴角子;不要说丧气话,容易成真;不孝顺父母,天打雷劈……举头三尺有神明,神在高处打量着众生,默默给出评价,一个都不落下。
如今,人们的生活被金钱牵引着,沿另一个方向疾速行进。地铁、创业、抖音、房产,成为另一种生活方式。神纷纷离去。背影萧瑟。他们掌控的那个世界渐趋崩塌。怎么办?
也许没这么悲观。摆放在树下的、数不多的塑像,每个晚上都会复活,检视人间。他们可以被打碎、被挪走,但有这棵大榕树在,他们随时可以回来。身负众神的责任和寄托,他们以一当十。
越来越少的崇拜者,则因危机感而更紧地抓住神的衣襟。岂止是信仰,还有乡情、亲情和时代的痕迹。城市发展得太快,他们一路跑着追,一手护着兜里的糖。如果吃掉,不过就是一块糖。你要从他手里抢走,那就是他的尊严和全部牵绊。他用这一块糖来维护自身所有的过去和未来。
所以,神树越被挤压,就会被擦得越亮。
城中村的主人是原住民。蜂拥而来的外来人口渐渐稀释了他们。他们有的老去,有的挣够了钱,到更舒适的地方定居。而客居城中村的人,故乡已经回不去了。此处彼处,他们已然用脚步投票,对此地有了归属感。耳濡目染,也被这朴素的信仰所净化和同化,有了恭敬之心。当年我们一行人去内蒙古玩了几天,获知牧民喜唱歌,酒桌上,大巴车上,随时高歌一曲。在此地生活了几代的汉族人,不知不觉也都爱上歌唱。他们承接了这个地方的风情。一块土地自有一块土地的神性。土地的气息和传承,似乎要大过人类自身的努力与抗争。
我所居住的小区附近就有个城中村。我经常从那棵神树下面走过。“神树”一词不知是否准确,我图方便才如此简称。为何要拜树?本地人提供了一种说法:古人相信大树底下好乘凉。茂盛古老的大榕树附近,都是风水极佳的地方,把观音菩萨安放于此,是对神灵的照顾。菩萨住得舒服,自然回报信众。另外,一些宗祠、庙宇旁边也都种有榕树,意義相同。广府人一般每月农历初一、十五要去上香。做生意的潮州人则习惯在每月农历初二、十六上香祭拜。如果心有所求、事有不顺,祭拜的时间可随机。
明明是拜神,拜来拜去,成了拜树。其实想想,塑像亦非神的真身,用以寄托而已。久而久之,树可代塑像,塑像可代树。无论拜谁,只要虔诚即可。信则灵。应验了,是神灵保佑。没有应验,是神灵力有不逮。以同情心深爱神灵,而非斤斤计较。诚心诚意地信奉点什么,一辈子过得都踏实。
神树的树干上挂着“某某街道名木古树”的铁牌,小字为“保护等级:三级;树龄:150年;责任单位:某某居委会”。这个牌子是它的身份证和保护伞,它不是因为“神”而被保留下来,是现代生活中的考古、环保等要素留住了它。但在居民心中,这棵树葆有灵气,聚天地之精华。他们像祖辈一样崇拜它,在那里烧香许愿。现代和传统就以这样自然的方式结合了。
神树大多在城中村的广场中央,庄严肃穆,居高临下。叶子因高远而显得渺小,树冠因为庞大而遮下一片阴凉。但那阴凉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只可远观而不可近享。走近了,胆怯、自责之情便油然而生。
另有一种,像邻居一样坐在人群中间,成为休闲之地。旁边有违停的汽车、垃圾桶和驮着煤气罐的三轮车。一只散养的鸡跑来跑去,两岁的娃娃在树根旁边蹒跚学步,年轻的母亲坐在石凳上刷手机……天地祥和,榕树造就了这一切,又仿佛一切与它无关。
所有重大社区活动——文化演出、厂家直销、一早一晚的广场舞、饭后闲聊等,都在这棵树下或者附近举行。哪怕它实际位于城中村的门口或东北角,但它始终是人们心理上的中心,是众人心之所倚。有了这棵树,这个村子就散不开了,始终是一个坚固的整体。
有必要说一说城中村。千百年来,它们原本是一个个独立的村庄,懒散地躺在岭南湛蓝的天空下。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之间,大片的稻田自由自在。转眼之间,厂房拔起来了,新的规则建起来了,打工的人纷纷赶来。村民们匆匆忙忙在自家宅基地上盖上楼房,楼和楼紧贴在一起,俗称“握手楼”。流水线工人、保安员、清洁工、快递小哥、机关里的临时工在这里可以租到便宜的房子,买到廉价的生活用品。这些城中村成为城市的湿地。城市靠它呼吸。原住民坐收渔利,有时候又不满足于此。一帮画家朋友住在一个城中村。他们有个庞大的计划,用手中彩笔给脏兮兮的墙面涂抹上一幅幅画作,所谓城市涂鸦。有些居民听说后,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画得这么漂亮,万一成为管理部门邀功的定点社区与旅游景点,将来就不好拆迁了。
他们的想法已经改变,对凌乱的城中村也不再留恋。
但对神树的崇敬一直坚守着。
南方科技大学校园里有三棵“神树”。我见识过其中的一棵。
这一年春天,天气暖得特别早。本应三月份盛开的木棉花,提前到了二月。天空一片红。南科大位于长岭陂水库旁边,一直禁止开发。建校时,附近三个村庄搬迁。村民提出的要求之一便是不要砍伐这三棵树,给他们留个念想。搅拌机轰鸣,挖掘机穿梭,一所清新脱俗的大学很快矗立起来。新栽种的各类树木,列队打量对面这棵孤独的四百多岁的古树。高大如彼,也被空旷的蓝衬托得不再高大。一朵朵白云从头上飘过。老树临风而立,沉稳老练,不卑不亢。
每年固定的某些日子,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祭拜神树。
问,具体哪一天来?答曰,不清楚。
旁观者仅仅知道他们有这个信仰。为何?如何?都不重要。每个人都沉浸于自己的生活,能转头瞥别人一眼,已经占用了时间。多问便是多余。这种散淡,有助于各自维护自己的内心。
别处的塑像都是露天摆放,此处略微庄严,用水泥抹出一个台子。高约一米,四四方方,三面遮掩,一面冲外,犹如戏台。墙壁贴着一个“福”,里边端坐两尊像。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怀抱手杖,脸上都笑眯眯的,像隔壁的老爷爷老奶奶。塑像底座居然还写上名字:“土地奶奶”,证明不是凡人。旁边站一个财神塑像,戴着官帽,右手托金元宝,左手执一竖幅,上书“财神到”三个字。
塑像前面摆放着新鲜的水果。一束塑料假花。一束真花,名为水塔花,鲜红。真花很鲜艳,假花也很鲜艳。不仔细看,分不清谁真谁假。两个塑料酒杯。一瓶北大仓白酒,剩了半瓶,另外半瓶估计已祭洒在地。一个香炉,积满香灰,上面还插着香,但未点燃。一个铁桶,我在墓地见过这种铁桶,用来烧纸钱的,防火外溢。
榕树主干已有些歪斜,下面用很粗的铁管子支撑着。气根有的垂在半空,有的一条条粘连在树干上,七扭八歪,成为树干的一部分,仿佛绳索捆住了岁月。捆绑者和被捆绑者终究还是走到了一起,可体悟到“恨之切”与“爱之深”的关系。斑驳粗糙的树干上,几十片叶子正在长大。新绿,滴水一般。想到一个词:生生不息。
树干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子,上写:“只吃猫猫食品(食堂的菜太咸,请勿投喂)”。友人说,这棵树成了流浪猫的栖身之地。有些好心的学生经常来给它们喂食。爱护小动物的组织就专门挂了这个牌提醒。下面有一塑料盆,用来盛放猫食的。
抬头,树杈上有一只皮毛柔顺的花猫正低头瞅我。四目相对,我觉得它比我沉稳多了。它的前后左右,一定还有我看不见的生物:树根下的蚯蚓、不知名的昆虫、蝴蝶、蜻蜓、候鸟……古树犹如楼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众生在其庇护之下,平平静静过一辈子。树在,它们的家就在。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有人讨论在南方科技大学这样一个理性学府,保留着拜神之地,是否合适。官方的答复好像是为村民留下“守得住的乡愁”。其二,在树下烧香点火,对树木是否造成伤害。然而,我站在树下,默默地看著它,春风拂面,问题渐渐消失。学生们到食堂打饭,天天从树下走过。那就是他们的一部分,是校园中一以贯之的一个符号。农耕社会与现代社会边撕裂边融合,并非水火不容。火有时是水,偶尔点燃,小心翼翼界定在某个范围内,对树木何尝不是浇灌?
树木安好,心灵安好,人也安好。
这些神树眼睁睁看着城市一天天变化,终有一天也会死掉。人祸之外,还有台风、暴雨、虫蛀。它们的命运不一定比人类更好。它们一棵棵干枯、倒下之后,敬畏就结束了吗?
在一个城中村,我见到过一棵明显年幼的树。它仅仅两米高,站在人行道旁边,叶子也不似别的榕树那般油亮。瘦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但是树干上却系着两条红绸子。不用说,这是被寄予厚望的一棵树。假以时日,它也会成为居民心中的神树,树下也会摆出塑像。我忧心的是,这棵树周围的空间不大,地面被柏油封上,气根从树上垂下来,晃晃悠悠,寻寻觅觅,无法扎到地上。榕树能继续长大吗?周围人声嘈杂,空气污浊,它如何应对?它能否如那些百年老树一样从艰险中突围,傲视周围平庸的绿色植物?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王国华,河北阜城人,曾居长春十八载,现居深圳。“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曾获第五届广东省有为文学奖散文金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八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六届深圳十大佳著奖。已出版《街巷志:行走与书写》《书中风骨》等二十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