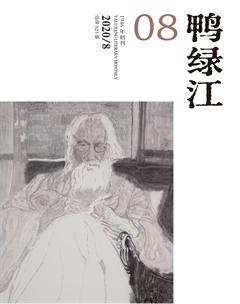箜篌(文本)
1
有雾。从马庄骑车到揽月桥,眉毛就白了。
这段路王彩虹骑了五年,闭着眼睛都能过去。有一次下大雪,骑不了车,步行,雪刺着双眼睁不开,她几乎是闭着眼睛走过去的。
揽月桥旁边是水印西堤,水印西堤旁边是香颂溪岸,香颂溪岸再过去呢就是橡树湾了——当然,堤、岸、湾是不存在的,都是小区名。王彩虹挺喜欢这些开发商绞尽脑汁取出的名字,念它们时,每个字在舌尖上轻轻跳跃后自己就蹦出来了。
王彩虹在橡树湾工作,准确地说,是橡树湾2区南幢601室。
这是王彩虹进城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格外珍惜。在此之前她也不是没上过班,她在仙女镇上的鞭炮厂卷过鞭炮,在农药厂干过包装工。怎么说呢,那些活儿都是死的,不用动脑子,每天坐在一只小方凳上,到下班屁股都不用挪一下,她所负责的就是方圆一平方米内的活儿。而现在呢,每天干什么、每个细节都是要动点脑筋的,并且,她管辖的范围从1平方米扩大到126平方米。
没错,王彩虹是个保姆。橡树湾2区南幢601室的保姆。
这么说,没有一点故弄玄虚的意思,因为对于这份工作,王彩虹充满了热情。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十个小时,下午可以休息一阵,周日也可以休息一天。每天下班后她骑四十来分钟车回家,再把家里的杂事收掇一下,晚饭后,王彩虹还会伏在饭桌上写一会儿,记一记第二天要做的事,或者突然想到的前一天被漏掉的事项。这时,她读初二的儿子就会觑过脑袋看一眼,鼻子里轻轻嗤一声。王彩虹便用手虚掩着,将几个东倒西歪的字涂成黑黑的一团。
进了大门,王彩虹就推着车步行了,小区里的路曲曲折折,不太适合骑车,不过,她挺喜欢的,走在四季常青的树丛中,脚是轻的。穿过一个紫藤架,过一道小木桥,再经过一小片矮冬青,就到楼下了。
她把车架好,不乘电梯,而是从楼梯爬上去。楼栋里仅一部电梯,这时是上班高峰,把电梯留给那些赶时间的人吧,她时间富余。一层层往上爬,每经过一个门口,王彩虹都会瞟一眼,脚步稍作停留——半开着的鞋柜、踢得东一只西一只的男式拖鞋、后帮被踩得凹下去的高跟鞋、蹭得发黑的脚垫、倒扣着的运动鞋、敞着口的垃圾桶等等,这些似乎都能透露门内的某种信息。
她感到气喘吁吁起来,倒不是体力不支,而是看多了那些摆放整齐或歪斜的鞋,幸福又忧伤。她索性停下来,趴在拐角处的窗台上歇着,不知道是外面的雾更浓了,还是自己吐出的热气模糊了玻璃,外面的一切显得极不真实——紫藤悬浮在半空,芭蕉叶像鱼一样游动。这时,王彩虹便看见了那个背影,像从水里钻上来一样,她贴近玻璃看着,直到背影被建筑物挡住了才直起身子。
继续向上,在一扇空荡而干净的门前停下来,601到了。她打开门,屋内阒静无声,和昨晚离开时没有任何变化,仿佛空气中飘漾的洗洁精气味还没来得及散去,从昨晚到早晨的这段时间被剪掉了,完好地衔接起来,王彩虹感觉自己并没有离开太久,只是刚刚走出门又返回来了一样。
她赶紧走到窗口,背影又看见了,远了些,她觉得背影不像是往远处走,而是往深水里潜入,慢慢地,连一点轮廓都看不清了。
背影是601的主人,陈笠,今年五十岁。和王彩虹的时间正好相反,陈笠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六点才能回到家中,常常是王彩虹刚进门,他披着衣服出门;晚上他一回来,王彩虹也要下班了。好像兩人在进行一场接力赛,而接力棒就是陈笠常年卧床的妻子胡老师。
王彩虹把钥匙放进口袋里,钥匙扣上的小玩意发出一点脆脆的乐声,第一次拿到钥匙时,王彩虹不知道这类似竖琴的小玩意是什么。箜篌,对方告诉她。王彩虹用手指轻轻拨了一下树脂上的小琴弦,又是脆脆一声。
2
王彩虹先去卧室看胡老师,对方闭着眼睛躺着,和王彩虹第一次见到时一样,一动不动。多年如一日,大概说的就是这意思。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卧床的,王彩虹并不十分清楚,大略知道一点是与脑颅出血有关,术后就这样了。王彩虹到来时,胡老师已经卧床几年了,刀口如一条蜈蚣伏在脑袋上,王彩虹第一次给胡老师洗头时吓了一跳,手摸上去像缝得粗糙的垒球。后来,头发长了,剪短,再长,再剪短,几次之后,蜈蚣就不见了,褪成白白的一道印子。
王彩虹的工作就是照顾胡老师,以及打扫这126平方米的卫生,下班前再做一顿简单的晚餐。
晚餐这一项是王彩虹自己主动加上去的,跟购物时的买一赠一一个意思,她觉得对方给出的薪水偏高了,她要对得住这个数字。王彩虹称陈笠陈老板,给她发薪水的就该叫老板,没错。陈笠被这个称呼弄得束手无策,几次令其改口均无效。她固执,他也随和,笑笑,随她。
陈笠的晚餐是简单的,一粥一菜,或两菜。王彩虹做好了,陈笠也回来了,如果是夏天,先盛出来冷一冷,陈笠到家了粥也半凉了。王彩虹是不留在这儿吃晚饭的,陈笠也不用客气,一是因为饭菜简单,二是希望她能多点时间回家。
上午通常用来打扫卫生,每个旮旯,绝不马虎;中午暖和的时候,王彩虹给胡老师擦洗身子——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要是在夏天,还好办,衣服单薄,穿起来比较方便,秋冬之后就麻烦了,好在不必每天擦洗的。王彩虹做这些时习惯先喊一声“胡老师”,当然,对方是不会应声的,连眼皮都不会动一下,只听得三个字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绕了一圈又噼里啪啦落在地板上。胡老师仰面躺着,嘴巴微张,下唇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牵扯着,脸上的皮肤是失去弹性的紧绷,暗灰,呈凝固的汤汁颜色。王彩虹第一次见时,胡老师就是这样的,五年过去了,还是这样,要不是导尿袋每天被淡黄色液体积满,跟死了是没什么区别的。
每隔两天会有一次大便,仍然是没征兆的,涂满了护垫,清洗时要脱下裤子,灰白的私处像芦花似的乱糟糟,很刺目。这个时候,王彩虹就会感到一阵难过,为胡老师,也为陈老板,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还不如死去。
在王彩虹之前,照顾胡老师的事都是陈笠来完成的,当然,也找过别的保姆,都做不来,嫌脏。陈笠要工作,还要照顾胡老师,每天像战斗一样,失控,焦躁,王彩虹到来后,才逐渐变得有序了,将他从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解救出来。
下午的时间王彩虹是要洗衣服的,除了刚刚给胡老师换下来的外,还有陈笠的,衬衫,外裤,或者内衣,原本都是陈笠自己囫囵地塞在洗衣机里,但王彩虹执意抢过来手洗——她不相信洗衣机能干好这些细致的活儿。王彩虹没洗过除丈夫之外别的男人的衣服,一开始,还略带羞涩,那些内衣和衬衫在手里搓揉的时候,脸会腾地红一阵。再后来,就不再脸红了,变得理所当然起来,甚至感到亲切。
傍晚,王彩虹要将前一天晾在阳台上的衣物收下来,叠整齐,分门别类放好。做完这些,离做晚餐还有一会儿,王彩虹便可以坐在沙发上发会呆,或者趴在阳台上眺望远处,目光在方块一样的群楼上慢慢跳跃,一直到达视线的极限。她知道在楼房消失的地方就是她的家了——一个叫马庄的地方,虽是村庄,却没了田地。那里住着她的丈夫、她的儿子,还有她的公公婆婆。他们都是老实人。丈夫在一家工厂里当搬运工,大概是白天把力气用尽了,回到家中总是一言不发。公公婆婆呢,一辈子都在种地,田亩被征用后他们变成不种地的农民了,这使他们无所适从,于是在离家很远的建筑工地附近开垦出一点地来,每天扛着农具步行过去,在地里消磨一天时光和力气。她的儿子呢,成绩平平,这一年开始叛逆,变得更不爱说话,能用鼻子代替的发音绝不用嘴。这是一个相对沉默的家,仿佛一切都潜在水下,幽暗,沉寂,时不时地涌动着水泡的破灭声。王彩虹觉得每个人都在水底憋着一口气,在离开家的那一瞬间才探出头来。
这也许也是王彩虹珍惜这份工作的原因吧,尤其是傍晚这段属于自己的时光,自由、轻盈、透明,她趴在栏杆上,像回到少女时代,对遥不可及的远处充满了幻想,看累了,就将目光落在小区里,落在那些郁郁葱葱的叶子上。有时,看走神了,忘了时间,直到陈笠出现在紫藤架下,才猛地一惊,但她并不急于离开,而是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近。王彩虹觉得这种感觉挺有意思的,她每天看着他出门,又等待着他归来。
3
陈笠喜欢花草,阳台上种了一些仙人掌和吊兰。餐桌上也有一只花瓶,一年四季插着花,春天康乃馨,夏天百合,秋天非洲菊,冬天就插蜡梅了。王彩虹到来后,花变成了蔬菜——青菜,洋葱,韭菜苔。王彩虹的意思是反正都开花,还能省下买花的钱。有一次洋葱开花了,弄得一屋子的辛辣气味。陈笠也不说什么,摇摇头,笑笑。再后来,他主动把萎掉的蔬菜扔了,给花瓶装一点清水,放在桌子中央,等待着王彩虹的蔬菜。
陈笠是乐器厂的琴师,胡老师卧床前他在民族乐器团,因为隔三岔五出差,不得已换了工作。
王彩虹听他弹过琴,回来早的话,他会在胡老师床边或书房里弹几曲。琴是古琴,幽静而旷远,如低吟,如倾述。一曲完了,陈笠便垂下两臂静坐着,看着床上的人发呆,期待什么奇迹似的。王彩虹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胡老师,她的手指,她的脸颊——不过,什么反应都没有,就连电视剧里常有的那种眼角滑出的泪水也看不到,真是令人绝望。这个时候,王彩虹会感到十分难过,心里有丝丝的疼,像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
她还能听到吗——陈笠突然幽幽说道,像在问王彩虹,又像自言自语。他将脑袋埋在手里,过了会儿,像个小孩一样抽噎起来。
王彩虹愣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第一次看见男人哭泣,那种不由自主的、压抑着的哭声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她走过去,迟疑着,最后还是将自己不太柔软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肩膀突然颤动起来,断断续续地,像珠子掉在地上一粒粒在弹跳。他反身握住王彩虹的手,把脸埋在这一双手里,仿佛接受某种恩典似的,哭得更大声了。
外面天黑了,起了风,有树叶被抽打在坚硬物体上。屋子里没有开灯,黑色无边无际,如辽阔海面。就这样,他们保持这个姿势好一会儿,当各种声音逐渐平息了,海浪把他们推到了岸边。刚刚过去的那一瞬间,竟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晚上骑车回去,王彩虹把钥匙挂在龙头上,颠簸的缘故,钥匙碰撞着箜篌小挂件,发出哔哔的声音。小挂件是陈笠厂里在一次民族乐器展上的小礼品,王彩虹问箜篌和竖琴发出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呢。当然,王彩虹也是随便一问,因为她连竖琴的声音都没听过。
竖琴的声音像是从水下发出的;而箜篌的声音,像是从澄净的水上发出来的。陈笠说。
秋天过去,陈笠要出一趟差,敦煌,有客户需要定制一款莫高窟壁画中古代箜篌,陈笠不得不亲自跑一趟。陈笠不在的几天,王彩虹需要24小时在这儿了,她在601的時间就更多了,虽然她对这个屋子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留下来过夜还是第一次。晚上,她在卫生间洗了澡,换上带来的干净衣服,躺在客房里的简易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远处有猫叫声,向着不可知的神秘之处叫唤,在一个个楼栋间彼此呼应。
王彩虹索性起来,先在阳台上坐了会儿,又去了陈笠的书房,除了挂在墙上的古琴外,还有一些她说不上名字的琴,王彩虹用手指轻轻拨了一下,沉闷的一声。再换一根弦,愈发沉闷。王彩虹就这样一件琴一件琴、一根弦一根弦地拨着,试图找到一个从清澈水面之上发出的声音。她在书房里待了很久,直到身子感到凉了才回到床上。这时电话突然叫响,是陈笠打来的,也没什么事,就是叮嘱将门窗关好,夜里降温了,要是床上冷,橱里还有被子。王彩虹“嗯嗯”应着,第一次这么晚和陈笠说话,第一次感到一种细致的关心。电话那头似乎风很大,像哨子似的。陈笠说敦煌干燥得很,风沙大,茫茫戈壁寸草不生,真不知道当年人们是怎么走过丝绸之路的……
挂了电话,王彩虹久久不能入眠,电话那头的声音,以及从陈笠嘴里蹦出的词语,莫高窟,丝绸之路,彩塑,箜篌,等等,王彩虹感到多么遥远和陌生啊,但这种陌生却使她难过又亲切。她把头埋在被子里,忍不住哭出声来。
4
陈笠出差刚回来,王彩虹的男人就出事了,他在搬运货物时被身后的卡车撞倒了,小腿骨折,需要住院。王彩虹向陈笠请了假,一周,两周,三周……每延长一点时间,她都感到十分不安,生怕他要换人,找别的保姆。她最后一次打电话延长请假时间时,有些吞吞吐吐,可临了时还是说了一句——要是等不及就找别的人吧。挂了电话后的王彩虹十分沮丧,同样,另一头的陈笠也很失落,他想,她是不是不打算再来了。
腿伤恢复得很不好,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不习惯把自己交给床,刚能下地,就偷偷干活儿了,他把家里的农具磨得锃亮,等王彩虹发现,骨折处已经肿起来了,骨头出现错位。他们为此争吵了一顿,两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吵起架来火力一点都不弱,接着,他年迈的父母也加入进来,他们的儿子也加入进来,到后来大家已经不知道起先为何而争吵的,每个人都显得精疲力尽,瘫坐在地上,像海啸之后一片狼藉。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了,所有人又回到了沉默之中,她的丈夫不得不把自己拴在床上,等待时光流逝。两个老人依旧去郊外开垦荒地,渐行渐远的身影不像是走向远处,而是走向地下;她的儿子也去学校了,什么时候离开的也无人知晓。
王彩虹推着自行车往外走,她还没想好要去哪里。路上的人行色匆匆,好像正在赶赴一件件重要的事,所有人都在忙碌,仿佛她是个局外人。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正站在超市门口吃着早饭。这个时候应该上课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王彩虹想起自己的儿子,想起他叛逆和倔强,心里沉甸甸的。她多么想上学啊,让知识改变命运,成为老师,成为医生,或者成为陈笠那样的琴师。她想起小时候,家庭条件差,总是最后一个缴全学费,作业本都是那种又黑又糙的回收纸做的,一写字,笔画就洇得粗粗的,笔尖在纸上停留的时间稍长就是一片墨迹,像山水画。纸面上还有一些小疙瘩,用手摸去,像盲文。她常常将它们一粒粒抠下来,是一截草梗,有时候是一团棉絮,还有一回竟是小甲虫的尸体。东西倒是抠下来了,作业本上却露出一个个小洞,让人非常沮丧。初中没毕业王彩虹就辍学了,等到儿子出生,对儿子说得最多的就是那句话:知识改变命运。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了。
王彩虹继续前行,视野里的绿色越来越少,冬天渐渐深了,阳光很透明,像蚕丝一样轻轻缠绕在手背。她把那串钥匙挂在车龙头上,钥匙和箜篌碰撞出清脆之声,叮,哔,铃……每一声都是透亮的,在蚕丝一样的光线上跳跃着。她在认真倾听,像从前站在黑暗中的倾听,期待着那一点划破黯淡萧条的日子里的乐声。
等王彩虹回过神来,发现已经来到橡树湾601的楼下,她抬头看六楼的阳台,胡老师和陈笠的衣服正沐浴在阳光下。她低下头,推着车便往回走,到了紫藤架下又折回来,反复几次,才架上车,往601走去。
王彩虹没有用钥匙开门,而是手在门上轻轻啄了一下。门突然开了,陈笠站在门内。两个人都怔怔地看着对方,似乎都不相信出现在眼前的一幕。一个多月不见,都憔悴了不少。如果这是电影或电视剧里的场景,一定是两个主人翁相拥而泣,久久不能平静。而实际情况是王彩虹突然说了一句,我来上班了,便走了进去。
5
日子缓缓向前流淌,像溪水分流后又汇合在了一起。
又有两个冬天过去了,胡老师仍然没有醒来,当然,也没有停止生命迹象。王彩虹每天骑着自行车赶到601,打扫,擦洗,做饭,然后在陈笠回来后离开,他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了如指掌。他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她洗,他的气味,她熟悉。
陈笠还在民族乐器厂工作,单位离家不远,步行过去。早晨吃一点昨晚剩下的稀饭,八点不到,王彩虹就来了,她总是披着一身阳光或雾气,再或者,是一阵风,陈笠总是从她身上看出外面的天气的。有时王彩虹还没到,他就出门了,不坐电梯,他也喜欢走楼梯了,保准能在楼梯上相遇。他们不需要像邻里之间客气地打个招呼,而是看一眼,或者笑一笑。他们太熟悉了,像一家人。
他越来越喜欢衬衫上阳光的味道,以及淡淡的洗衣液味道,就连洋葱开花时满屋子的辛辣味都使他感到舒服。是的,他们越来越习惯并依恋着彼此。好像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甚至更久。
601里的一切,阳台、卫生间、餐桌、沙发、琴,包括一动不动的胡老师,都成了他们共同生活的部分。他们已不再希望躺在床上的那个人能够醒来,但也害怕她某一天会死去。他们认真虔诚地伺候着,翻身、擦洗、更换衣服——小心翼翼的,仿佛那已不再是一具身躯,而是某个神灵,保佑着这珍贵的平静生活。
然而,床上的人还是死了。
灵堂是设在小区公共多功能厅的,那些天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人,亲戚、朋友、同事、等等,就连陈笠自己都难以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亲友。她的儿子也从国外回来了,仿佛这些年来一直等待着这一天。大家都为陈笠感到高兴,终于可以解放了,也不必再雇保姆来照顾了。丧事结束后大家和陈笠道別,包括陈笠的儿子,一切都结束了。
是的,一切都要结束了。
他们都发现对方头发白了很多,知道除了这几天的操劳之外,还有心里隐秘的悲伤。
王彩虹打算再做最后一次晚餐。她认真地淘米、切菜,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细致,陈笠也过来帮忙,给她递一根葱,或帮忙关上水龙头。两个人无声又缓慢地做着这一切,直到晚餐好了,王彩虹才开口说道——得走了。
陈笠看着她,正在盛粥的手迟疑在半空。半晌,才说,一起吃顿饭吧。
这是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谁都没有说话,各自低着头,只有轻轻地唆着粥的声音。窗外已暮色降临,黑暗像水一样包围过来,都忘记了开灯,当他们的视线从各自的碗里抬起来时,突然发现插在花瓶里的青菜开花了,金色,像小火苗一样在黑暗中跳跃。
菜花,还有这花瓶、桌布、椅子、壁灯、沙发、地砖、过道、墙角、天花板、阳台,以及他身上的气息——多么熟悉啊,王彩虹环顾着四周,眼睛有些潮湿。
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在桌子上,钥匙和小箜篌碰撞发出脆脆的一声,十分干净。
陈笠接过钥匙,在手掌里慢慢摩挲着,很久,开始拨动琴弦,每一个声音都在水面之上,一曲之后,他将箜篌从钥匙扣上取下来,送给了王彩虹。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家简介:
汤成难,生于1979年,江苏扬州人。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钟山》《上海文学》《作家》等。获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一届黄河文学双年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比邻而居》,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J先生》。另有小说集《月光宝盒》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