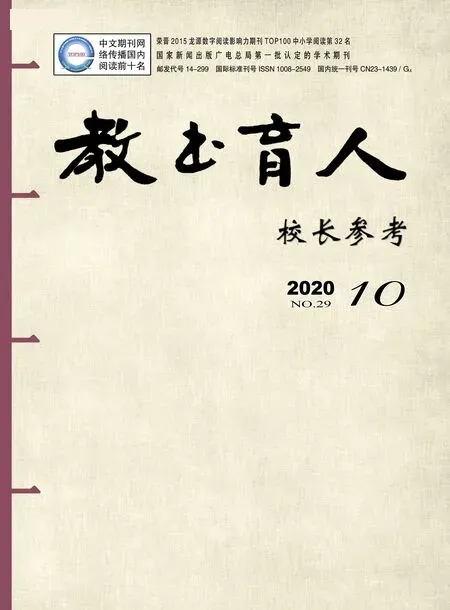基础教育研究应慎用“创新”
杨有平 (湖南湘钢一中教育集团)
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仔细品味,“回看来路,比较他路,眺望前路”这对于一线基础教育研究同样适用。在现阶段的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大师”很多、“专家”很多、“著作”很多,还有“创新”很多的怪现象,这既包括五花八门的教法创新、各式各样的学法创新,还有就连几千字的文章里都少不了几个创新,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此花开罢彼花上。
还记得在本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毕业论文提交栏里有一栏是要写“本文的创新之处”,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身入险境未可知,我和大家都从方法创新、视角创新、内容创新等方面把该栏填写得满满的,自我感觉新意满满。当进行论文一辩的时候,治学严谨的唐老师就告诉我,作为本科生,要慎用创新,本科知识多属于通识教育,专业知识涉及少且浅,没有那么多的创新可言,本科生都有这么多的创新,都能把很多问题进行创新性解决的话,设置研究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看着原本亲切的唐老师一下子变得如此认真严肃,那是后背冒汗的感觉,我至今依然记得。
后来,仔细一想,当时泛用“创新”一词,主要在于文献阅读不足所导致的无知。那次经历,使我意识到文献阅读的重要性。这也使我在工作之后始终坚持文献研究,每当写文时,总要查询一下相关论文与其他文献成果,有了这一过程,我才有敢写的底气。
现如今,翻阅各种杂志,我发现很多一线基础教育研究都存在我当年的那种滥用“创新”一词的行为,这其中不乏有很多中文核心期刊。其中,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研究成果有其创新之处,但值得肯定的是,那一定是几十年,有的甚至是几代人思考传承下来的精华。创新成果需要几十年、几代人才能得以呈现。可见,在基础教育研究中“创新”一词理应罕见,但如今为何却如此“常见”呢?我想,有的可能和我当初一样,源于缺乏文献研究,不顾来路,不看他路,结果导致自己迷路而产生的无畏行为,这迷路中的创新犹如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而有的则可能是被功利之心驱使下的行动,前段时间某深圳名师、“资深”阅读推广人的滑铁卢经历便是对基础教育功利之心盛行现象的真实投射。
何谓创新?创新既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独特性,还要有“竹树开花节节高”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创新绝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立性活动。这样仔细想来,在基础教育研究领域所出现的很多创新根本不是创新,如为了公开课而花里胡哨、吵吵闹闹的“创新”课堂,这种“创新”不可取,有些3 千余字不到就大谈“创新”的教研成果,这种创新“不可用”,有些妄自菲薄、网络搬客“创新”现象不可存。
创新何为?只有传承之后的创新才能叫真创新。创新是厚积而薄发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实现一定要经过博观而约取的传承,可以说创新是传承的结果。传承与创新,道通而为一,并行而不悖,二者无主从之分,但有先后之序。在基础教育研究里,先要有充分的文献研究才会有创新的成果。而目前一线教育研究最缺乏的就是研究意识,即我们所说的文献研究意识,也可以说是传承意识。
在当前的教研过程中,尤其是基础教育研究中,文献研究意识淡薄,很多人不会做甚至是不做文献研究是最普遍的问题。文献研究不同于文献堆积,文献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去粗取精、文化传承的过程,教师要在此过程增添自己的领悟。而写好文献研究并非易事,文献研究不是简单地把文献摘要和目录复制下来的体力劳动,它是脑力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传承性活动。一篇好的文献研究要坚持做到文要广全,研要透彻,究要根本,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你才能提出有支撑的“创新”。
可以说创新是积累与传承的“老子”,对于一线基础教育研究来讲,这种积累与传承便是文献研究。慎用创新,多一些积累与传承,这是我们一线教育研究不可丢弃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