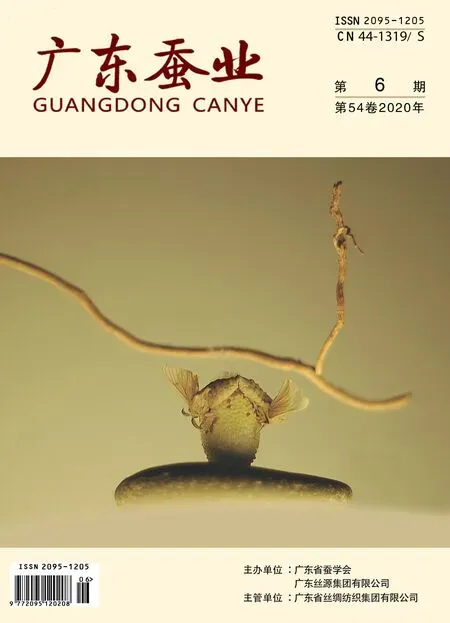电商助力农产品销售探究
何禹翰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重庆 402160)
党的在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工作的首要目标。2018年至今,中央陆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一系列文件,明确指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并将数字乡村确定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助力农产品销售,带动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民生问题,对完成2020年攻坚扶贫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1 农产品电商销售现状
1.1 发展速度快,高速增长
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截至2020年3月,农村网民总数约为2.55 亿人,全国网民总数占比28.2 %[1]。依托各大网络平台,农村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以淘宝为例,全国已建立了5 428 个淘宝村、镇,2 011 个农村电子商务合作社,农产品直播140 万场次,覆盖全国,带动了680 万人就业。至2019年年底,全国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零售额约为2 693.1 亿元,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长28.5 %。其中植物类农产品、动物类农产品和农资类产品的销售额分别为2 142.9 亿元、433.3 亿元和116.9 亿元。在物流方面,各大电商平台实现业务下沉,运输及配送服务不断完善,截至2020年3月,全国已建立55.6万个村镇直达配送点,农村快递网点增至3 万个,乡镇快递覆盖率达到96.6%[2]。
1.2 农产品电商分布呈阶梯型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产品电商销售额以东部地区最高,由东向西逐步递减,梯队层级较为明显。广东、北京、浙江地区电商销售额位列前三,占全国农村电商总销售额的47.7 %,与其他各省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电商产业链完整,网络基础设施完善,市场与源头衔接较为紧密。西部地区如新疆、宁夏等地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是电商经营观念保守,物流运输欠发达,无法形成完整的供应链,逐渐与东部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拉开了距离。
1.3 各大平台助力农产品销售
近年来,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各大电商平台加大农产品支持力度,阿里、京东、字节跳动等企业纷纷聚焦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各类农产品智能超市、App软件网上下单,配送到家服务完美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销售[3]。农产品销售由平台发售、直播带货等形式逐渐转向生产端销售模式。例如,重庆奉节脐橙园引入阿里巴巴“未来农场”管理系统,由农产品产地直供,通过区块链技术溯源,客户在下单之后能够全程监管农产品生产过程。拼多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线“抗疫农货”专区,以每单农产品订单补贴2 元运费的形式助力农产品销售;永辉“超级物种”以线下门店直销形式,直接连通近50 个贫困县农产品,大力支持了扶贫工作。
2 存在问题
2.1 农产品供应链机制薄弱
我国农产品资源丰富地区大多集中在西部,而农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东部。受空间距离的影响,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物流运输发展程度较低,供应链上下游结合不够紧密。同时,电商平台要求的标准化和农产品生产经营分散化相矛盾,上下游暂未形成利益联盟,难以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把控。就目前而言,农户生产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农产品质量好坏全靠农户的自觉性,无法通过统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
2.2 农产品品牌效应不明显
全国范围内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时间并不久,除了传统的农产品品牌,如烟台红富士苹果、新疆葡萄干、西湖龙井等,其余各地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名气不大,而且没有形成统一的产业联盟。在对外销售时,消费者认可度较低。农产品名气的传播仅限于购买者之间的互相推荐。受限于资金实力和经营理念,农户在推广自己的农产品时,并不注重产品品牌建设,未能有效结合当地民族民俗文化进行包装[4]。产品营销手段单一,仍然停留在“叫卖”“好酒不怕巷子深”等初级营销方式,然而这种营销方式无法引起现代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产品销售由线下转到线上之后,受到全国产品数量上和品种上的冲击,产品附加值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消费者无法区分有、无品牌的农产品之间的区别,在购买时随机性更强。这对单个地区农产品销售的稳定性并无助力。面对种类繁多又趋于同质的产品,产品品牌的意义尤为重要。
2.3 农村电商人才匮乏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城乡差距较大,村镇与城市相比,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相差巨大。相较于城市现代化的生活环境,受高等教育的人才不愿意留在农村务农,而与电商产业相关的物流配送、美工设计、数据分析、培训教育等专业人才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人才流失严重[5]。目前,各地区农村电商人才的培训主要是通过联合高等院校,以集训的方式,为农村培育电商人才。但这种培训方式主要是通过理论授课的方式,在培训方案的设计上,由于设计者对当地农村实际情况的把握不一定精准,培训内容与实际情况有时相差甚远。
3 农村电商发展的策略建议
3.1 整合农产品生产基地,完善供应链上下游协作
由政府引导,企业电商平台协作,共同制定农产品从选种到产出统一的行业标准;形成区域农产品生产规模化基地,改变以往小规模、家庭式农产品生产方式。如陕西韩城花椒产业发展,采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由过去农户个体经营转变为现代产业化生产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民增产增收[6]。各地区应制定本土特色农产品生产标准,严格把控农产品输出标准,由分散式经营转向集中式标准经营,引导农村电商有序地高质量发展。建立可持续机制,加强农村电商顶层规划设计,由政府建立区域数据共享中心,有方向、有目的、有条件地针对性输出农产品。加强供应链上下游利益联系,将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上下游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完善的绿色产业链。例如,浙江金华打造了“IAM”模式(互联网+农业+媒体),推动了当地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7]。
3.2 加强农产品品牌管理,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
互联网高速发展,为电商发展带来了新的营销思路。通过“网红带货”、短视频、生产基地网络直播等方式,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和社交满足感,有效建立一批本地农产品品牌,形成品牌效应,提高经济附加值。“网红”薇娅在首届丰收购物节时代言了河南省镇平县“荷叶茶”,仅用2小时就完成了近60 万元的销售额。加大与各大电商平台的合作,推广智慧化农业建设,打造一批明星产品,改变以往的营销手段,让消费者参与到农产品的生产当中来。在销售端要注重“小而精,精而美”,鼓励个性品牌的建设。如顺丰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让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甘孜产的松茸时,能够回溯每一颗松茸的采摘人员、地区、生长周期、装箱时间及分拣时间,消除了消费者对松茸质量的担忧,对甘孜松茸的品牌建立和传播有正向积极作用。江苏省泰州市2018年制定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建立了靖江肉脯、兴化大闸蟹、溱湖八鲜、泰州芋头等一系列特色农产品品牌,三年时间销售额超过6 000 万元,直接带动当地农民收入增长,深度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8]。
3.3 优化人才培养,鼓励电商人才返乡创业
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优秀的人才储备,农村电商人才振兴是实现农村电商发展的坚实后盾。一方面,针对不同基础的农村人员开展电商基础知识培训、运营管理培训、营销手段培训,提高当地电商人员的整体应用能力;加强农产品企业与各地高等院校的联系,加强实践教学,开展校企合作,通过实践训练,培养一批既懂得电子商务,又懂得农业产品的领军人才,通过“乡贤”效应,带领当地农民实现收入增长。另一方面,给与创业优惠和实行税收补贴政策,建立农村创业孵化基地,鼓励各类电商人才参与到当地电商建设当中,实现个人收入和心理需求的双重满足,通过需求和利益驱动,吸引一部分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的毕业生、创业群体落地生根;大力引进“智慧农业”人才,通过现代化技术的参与实现农产品培育最优化,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4 结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精准扶贫工作推进行之有效。在大力发展数字农村,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改变农民的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农村电商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