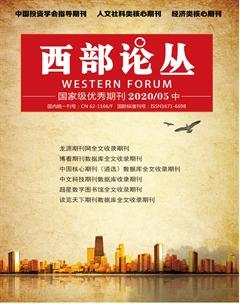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路径探析
秦元旭 李孝梅
摘 要:贵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在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为全国非遗保护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巨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本文在对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梳理的同时,提出了改善贵州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对贵州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发展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路径
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贵州少数民族同胞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和发展的。
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成功实践
(一)把立法和制度建设挺在前面
贵州省委、省政府重视依法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早在2002年2月,贵州就出台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11年2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后,贵州省加快了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于2012年3月通过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遺产保护条例》。条例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即“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1]条例还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原则。”[2]条例还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等等。
2014年贵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2014-2020年)》文件,标志着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也是全国31个省区中的第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到“十二五”期末贵州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深度调查,建设数据库。未来贵州还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和生产性保护,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加强理论研究,创造更多的文化精品。同时以活态保护为核心,完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土壤和条件。
2017年7月,贵州省文化厅、省经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贵州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整合传承群体、高校和企业的资源,搭建合作平台,促进传统工艺振兴,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出台,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与扎实的工作平台。
(二)政府积极作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博物馆模式的出现破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难题,它可以将不方便移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藏,尤其是20世纪以来流行的生态博物馆保护理念,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周边区域集中起来,对该区域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解决了弱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难的问题。
1998年10月,贵州省建立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标志着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7月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建成开馆并全年免费向市民开放,这是我国最早建成的省级综合类非遗馆。经过20余年的建设,贵州已形成了区域性博物馆、专题展览博物馆和传统民俗博物馆等三类非物质文化博物馆。充分发挥了博物馆在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传承及脱贫方面的作用。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自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全面启动。近年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工作成效显著,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数据库系统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渠道的拓展等工作进展顺利,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系统》。目前已初步建立了涵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地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市县级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栏等网络服务体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非遗保护数字化建设方面成绩显著,例如黎平县将“侗族大歌”列为数据库建设的重点项目,编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侗族大歌框架》和《侗族大歌数据库采集大纲》,已完成100余首大歌曲目视频收集;锦屏县制定了《锦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侗族刺绣>数字化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数字化建设内容,对《侗族刺绣》视频、图片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完成了数字化采集工作。[3][4]从江县到2015年已完成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项目及完善数据库建设的标准。目前仍在建设和完善的非遗数据库有国家级侗族大歌、珠郎娘美、瑶族药浴,省级芭沙成人礼四个项目。2018年5月28日,多彩贵州文化云平台启动运行,成为充分展示与传播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官方平台。
(三)民间力量的参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和活力
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贵州特定环境下,是少数民族各族群众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结晶,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内核所在,其发展和传承离不开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大众的参与,如果没有大众的参与少数民族非遗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在非遗的保护和发展中,非遗传承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非遗的精神内核所在。近年来,贵州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选拔、培训、政策扶持、身份认可和经济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常态化、制度化发展。并使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与脱贫攻击相结合,有力的助推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贵州省按照“十、百、千、万”培训计划分级分类分层培训非遗传承人群。先后举办了蜡染、刺绣、银饰、杂技、木雕、手工纸制作、土陶、都匀毛尖茶制作等传统手工技艺的培训。这些培训工作的实施,让非遗的保护传承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提高,开创了贵州非遗脱贫攻坚的新模式。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的基础上,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是中国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新思路。2016年5月,贵州省文化厅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治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建立了“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并在此框架下设立“创意贵州” ,以非遗扶贫就业工作坊、非遗小镇、非遗村落为载体,通过培训回访、传承人对话等项目,为非遗保护搭建平台。
万达小镇的成功建设对于丹寨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万达小镇像一个“聚宝盆”收纳了丹寨县各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括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6个省级非遗项目、16个州级非遗、145个县级非遗项目。民间文学贾里、石桥古法造纸、国春苗族银饰、苗族锦鸡舞、苗族蜡染、芒筒芦笙祭祀礼以及三大斗艺场馆(斗牛、斗鸡、斗鸟)、特色民族餐饮(卡拉斗鸡肉、苗王鱼、牛羊瘪、韭菜一汤等)、三座非遗小院(造纸小院、蜡染小院、鸟笼主题民宿小院)、民族文化特色业态(苗族银饰、苗族苗饰、苗医苗药等)均已入驻小镇。例如国家级皮纸制作传承人潘玉华,是万达小镇“纸会唱歌”小院的主要经营人,他开办了万达小镇内第一家纸皮研學基地,2013年,潘玉华研制了一套仿真造纸木质模型,将原有的上百道精细造纸工艺浓缩为浇纸浆、摆花、盖浆、烘干四个步骤,研学基地每年接待游客约8000人,为潘玉华一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贵州万达小镇的开发建设,对于构建贵州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塑造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品牌,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促进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万达小镇的开发成为民间力量参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发展的典型。
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贵州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许多做法和经验在全国推广,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贵州在全国来说仍然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道路还很长,再加上贵州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贵州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很大,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贵州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发展没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公众的非遗保护意识相对淡薄
少数民族非遗保护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赢得大多数公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其中。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公众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落后的农耕时代的产物,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格格不入,又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也就没有保护发展的必要了。
研究表明,不少公众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甚至是认同断裂。大部人无法准确了解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对非遗背后的精神追求、价值意义更是知之甚少。决策部门的公共决策有时存在相互矛盾,过渡追逐非遗带来的经济价值,而漠视非遗深层次的精神价值,不可避免的会影响甚至是误导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
(二)非遗传承人及其制度还存在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征就是它依附于个体、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活态”文化。[5]我们对非遗的保护不仅仅是对非遗作品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那些作为传承载体的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但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年轻群体热衷于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热衷于快速致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欣赏只是停留在好奇心的层面上,一旦在涉及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甚至财力去学习某项技艺时便打退堂鼓,致使能长期留在农村安心继承非遗传统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少之又少,非遗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地方性、广泛性和群众性,而传承人制度主要由政府主导,又必须从地方性的生产生活环境下剥离出来,不可避免的造成固化、造成主流与边缘的区隔、造成精英化,最终体制化、标准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参与性与活性也无从谈起。[6]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
虽然贵州省政府这些年持续加大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立法工作,为非遗保护营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法制保护环境,但由于贵州省内的少数民族居住比较分散,民族文化资源散落于民间,保护状况复杂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非遗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在浓厚的商业化氛围冲击下,再加上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使贵州省内时常出现一些民族民间文物被收购和盗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四)经费投入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普查到挖掘,从人员培训到资料整理,从规划保护到抢救利用,都需要资金作支撑。《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资金、项目上对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予支持。”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虽然贵州省省级财政安排了近3000万元的专项保护资金,但由于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分布广泛且分散,加大了对保护经费的需求数量,从全省的情况来看,总体投入仍显捉襟见肘,缺口很大。尤其在市(州)、县两财政,大多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仅是中央、省财政的补助资金,“等、靠、要”的思想严重。“专项经费不专”的问题在有些地方还大量存在。有些非遗保护的经费被下拨到市(州)、县以后被统筹到其他方面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7]这些乱象如得不到及时的改变和治理,必将对贵州民族地区非遗保护工作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
三、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