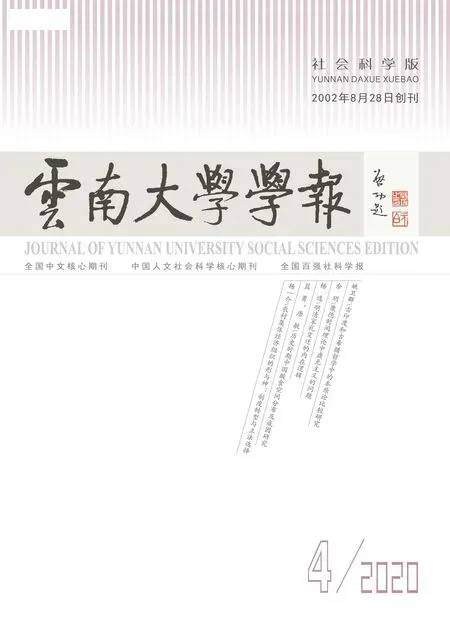康德时间理论中虚无主义的问题
——雅各比和海德格尔的诊断
余 玥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5]
国内学界关于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对时间问题在存在论上的关键地位虽已有大量研究,但并没有说明,历史地看,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并非首创性的,也没有充分顾及《纯粹理性批判》诞生不久后德国学界对之的批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完全没有理会雅各比的康德批判,虽然后者和他一样将时间问题置于康德哲学最为核心的地位上,并深刻影响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对时间及实在存在问题的看法。由此,对当时哲学有巨大影响的雅各比式康德时间哲学批判,以及海德格尔对之的评价间的异同,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意义体现为:虽然海德格尔与雅各比一样看到了客观实在性、先验想象力和时间的统一体对于康德式的基础存在论的关键意义,但与雅各比不同,1929年的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这里潜伏着虚无主义的不可持守性,他也未看到这一危机对于后康德哲学的中心性意义,而是将之视作一种向着“形而上学问题”的导引。正因为此,他才错误地做出了“康德是第一个和仅有的一个在调查时间维度的道路上行进了一段距离的人,或者,他是第一个和仅有的一个让时间现象逼迫着自己走了一程的人”(1)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23.的论断。本文首先结合康德的论述,分析雅各比对康德认识论中关键的“客观实在性”问题所进行的批判的两个层次,即先验客体和我思-时间层面的问题,然后结合康德时间理论在后康德时期德国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哲学中的发展,说明雅各比的历史影响,最后比较雅各比和海德格尔对康德认识论问题理解的异同,并指出后者同样面临的虚无主义的批评。这样一来,雅各比的康德批判的结构特征、历史影响和当代意义,就可以通过一种交互比较阐释的方式,被全面地勾勒出来。
一 作为虚无的思维构 造物的 “先验对象”
客观实在性是雅各比与海德格尔关注康德认识论的焦点。(2)海德格尔之后,客观实在性也处于康德研究的中心。I.Heidemann与海德格尔一样认为,在客观实在性与时间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他将这一实在性与“想象之物”(ens imaginarium)关联在一起加以讨论,因为它的实在性不再仅仅是主观的,而是与某种先验客体相关。然而这种先验客体“X”仅仅是想象的产物,而自身不过是虚无。参见I.Heidemann,Spontaneität und Zeitlichkeit.Ein Problem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Köln-Universitäts-Verlag,Köln 1958,S.63ff,S.48.又见I.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Hrsg.von J.Timmermann,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1998,A291/B347,A265/B321,A242/B300.本文中该文献以下采用夹注,仅标注文献页码。在B版演绎中,客观实在性意味着某种与一种对象相关的关系,在这种对象中,知识才有其意味和含义。(A155/B194)而在A版演绎中,康德对此的说法是:“当存在着纯粹先天概念的时候,那么这些概念虽然肯定不能包含经验性的东西,但它们必定是属于某可能经验的纯然先天条件,且这些可能经验的客观实在性仅能依据着此基础”(A95)。这里的对象指先验对象X,康德将之与物自身和先验客体放在一起构成一组概念,指示着“一种对我们来说不可认知的显像的基础”;(A380)而这里提到的“纯粹概念”,则是指此先验对象的概念,这一概念“就是能从根本上给我们所有的经验概念提供其与某对象的关系,即提供客观实在性的那种东西”。(A109)
先验对象X“既非材质,亦非某能思之本质自身”,(A380)它被康德叫作“那种关于一般某物的完全不确定的构想”。(A253)有趣的是,这样一种“某物”,也就是作为统觉的相关项来为感性直观中杂多的统一服务的东西,却“完全不能与感性的材料分隔开来”。(A250)这就是说,虽然康德表面上似乎把这个作为一般对象的“X”描述为孤立的,作为一个知性的“构想”,但背地里,他却将之带入了与感性的关系之中。鉴于感性与知性在康德那里的截然分别,就必须问,“X”显示出来的这双重性何以可能?康德认为,知识的必然性没有办法通过时空中的经验性素材搜集来保障,而只能通过:a.普遍必然的意识统一形态;b.先验对象才能实在地被确立。后者之所以必须被强调,是因为概念必须要有对象,包括统觉之本源统一这一概念也需要对象。(A104f.)但是,我们的知识怎么会与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一般对象”发生关联呢?唯一可能的解答是:这个对象并不真正独立于我们,而就是“我们的”统觉之统一的“相关项”。在统觉作为我们知识的最高能力和一切范畴的可能性基础的意义上,其相关项当然也是认识能力和综合能力的一般相关项。只有当“X”与我们知识的必然性结合在一起考虑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相关项本身已经与我们的思想关联的时候,它才能被说出。这里有两重意思;其一,只有从作为一切综合进程之关键的统觉中,才能导出这一一般对象“X”的可能作用;其二,反过来,这一对象却也保证着由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进行的综合的客观性,没有它,我们的认识就是随意的和悬空的。这一对象的作用因此始终根植在我们意识的必然综合进程中,与统觉不可分地构成我们知识的客观实在性的基础。统觉及其相关项也不需要额外的客观实在性的保障,因为它们就互为基础,互相保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什么康德说先验对象是一个“构想”(Gedanke),那是因为它与统觉“共同地”被设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先验对象对知识具有实在的作用,这就是说,它为我们提供某种源初的实在刺激,且先验对象的这一刺激作用根本不是一种外在于我们、与我们无关的东西的刺激作用,因为这种非感性的刺激完全是作为“自身意识”(即“我思”或统觉之本原统一)的自关联的相关项来发生作用的。
康德的以上论述引起了雅各比的极大反感。他反问:是否除了意识的运用和内在相关于意识的相关项之外,就再无实在性存在了?他认为,所谓的先验对象完全仅仅是一种被设想出来的“条件物”(eine ausgedachte Be-dingung),但自身却是一种“荒谬无物”(Unding): “(先验对象的)这个概念是一个极有问题的概念,它所依据的是全然主观的、我们独特的感性所从属于之的那种我们的思维的形式”,“且它被当作是一般现象的智性原因,只有借助它我们才能拥有那种与作为接受性的感性相关的东西”。(3)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 Werke Band 2.1,Hrsg.v.W.Jaeschke u.I.M.Piske,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2004,S.108f.这是对上述关于先验对象的双重意义的分析的总体结论。但这个结论却带出了雅各比更大的疑虑,即:“但此处,在最深的黑暗中,仍然潜藏着下述问题:这些原因究竟在何处存在?它与其作用的关联又是何种形式的呢?”(4)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 Werke Band 2.1,S.110.雅各比认为,这一疑难问题在A版关于(外部关系的)观念性的谬误推论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在那里,康德指出,一切物质存在者,只要它们必须在自身意识中被给出,就只能以与我们的感性不可分的表象被观察到。(A370)特定存在者的实在性也因此只存在于我们的感性之中。能保障此感性实在性是真正实在的,而非纯粹的知性设定而已的,是客体X,即一种似乎外在于我们的外部对象存在。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外部对象,我们既不能说它可能在,也不能说它可能不在,因为我们对其既无直观,亦无概念。这样的一种对象,一种逻辑上抽象的“荒谬无物”,怎么能成为感性实在性的真正保障呢?对于康德,显然只有依据感性的实在性,才能说这种对象也是实在的。然而后者的实在却又恰恰是感性实在性的原因,而不是其内容。这样一来,一个难以理解的循环就形成了:客观实在性仅仅来源于感性实在性并由其保障,这种感性实在性之所以实在有其外部原因,然而此原因的实在性却又只能在感性实在性之内被见及。这样的死循环对回答“原因在何处”的问题毫无帮助。因为假如这一原因的确是外在于我们存在的,那么它如何“实在地”作用于我们,而不是仅仅“被我们设想为”作用于我们的呢?反之,假若我们将这种作为外部存在的原因只理解为我们统觉的内部相关项而已,那么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谈论过任何外在于我们的存在者,这样一来,一切所谓的实在刺激,归根到底不都仅仅是一种完全属我的构想而已,其实并无其自身实在性吗? 无论上述假设中的哪一种,都对回答“原因与其作用的关联是何种形式的”这个问题毫无帮助。
雅各比认为,康德其实根本没有准备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回避了它。作为似乎外在于我们的无条件的存在者(Un-bedingtes)的先验对象,恰恰就是我们意识的实在条件物(Be-dingung),这件事情不是通过感性,而完全是通过我们的认识能力(统觉)规定下来的。是认识能力一方面把这个一般对象“X”转化成一个叫作“本体”的观念构想,另一方面又将之转化为感性的实项规定性。没有知性,源初的智性原因与主体性作用的关系就是不可设想的。而此处的知性绝非二者间的媒介而已,毋宁说,二者的联系本身就是知性的产物,换言之,所谓的“X”完全是知性自身为自身召唤出来的幽灵。对此,雅各比写道,知性自身必须就其自身“指出一个主体的‘X’和一个客体的‘X’”,“两个XX通过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将彼此设置为前提,每一个对另一个来说都是至为充分和圆满的,但仅仅是在如下意义上充分和圆满的,即,仅能以将这种交互作为前提的方式来说明此充分圆满:二者中没有一方能自诩优先于另一方,就好像在它哪一方内或为其自身来看,疑难会少一些似的”。(5)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 Werke Band 2.1,S.275f.这就是说,一方面,在康德那里的确存在着被预设出来的主体性前提和先行给出的客观确实性之间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其实在二者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两个“XX”就其自身而言不是别的,仅是“一种纯粹关系物,它存在,作为无规定者和须被规定者的交互规定,那就是说,作为没有限制者与须被限制者的交互限制活动,由此规定和限制出发,什么都根本没被设置,而只有一种完全纯粹的本质逻辑性得以敞现了”。(6)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 Werke Band 2.1,S.276f.雅各比因此揶揄到,所谓实在性,只不过是最高知性能力自身“变色龙般的颜色”而已。(7)G.Zöller认为,客观实在性有双重含义,即作为媒介(综合性意识)和作为客体。他进而论述了二者间的复杂关系。对他而言,客观实在性只有通过非经验性对象才可能,相反,意识在自身中拥有客观有效性,后者为经验性的客观实在性奠基。二者共同构成康德演绎的论述结构。与D.Henrich的主张相反(参见D.Henrich,Die Beweisstruktur von Kans transzendentaler Deduktion,in: Kant.Zur Bedeutung seiner Theorie von Erkennen und Handeln,hrsg.v.G.Prauss,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Köln 1973,S.90-104.),Zöller试图说明,即使在B版演绎中,客观实在性问题也是核心性的,而不是像Henrich说的那样,在那里只有意识的量性限制及客观有效性被强调了。参见G.Zöller,Theoretische Gegenstandbeziehung bei Kant.Zur systematischen Bedeutung der Termini objektive Realität“und objektive Gültigkeit”in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Walter de Gruyter,Berlin/New York 1984,S.119,132f,180f,117ff.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维度,意识的客观有效性维度就只会是主观的。
二 作为虚无的自我编织进程的时间性想象力
客观实在性问题在康德那里还与概念和范畴相关。有其先验含义的范畴被运用到经验直观上,为经验杂多的连接提供规则。对范畴而言,先验含义是“实在定义”(Realdefinition),因为此定义“不只做成一概念,而是明晰地同时造成此概念的客观实在性”。(A242f)具体而言,范畴与感性的连接是通过先验想象力成为可能的。正因如此,它在自身中就具有了双重向度:一方面朝向必须被预设的意识统一的主体思维相关项(朝向普遍必然的主体性条件),另一方面朝向感性的客观确定性的隐秘基础(朝向客观实在的效用)。
这样一种想象力的综合,康德在某处将之看得比在统觉中的综合层次上更低,认为它只是synthesis speciosa,而不是synthesis intellectualis,只能盲目地提供一些感性图像,而不能提供真正的概念。(A78/B104,A115,A120,B151) 但如果康德坚持他的看法,即:先验想象力的综合真的比统觉的综合在层次上低一些,因为前者中没有规则,那么,统觉又是如何提供出合规则性的呢?按康德的观点,这只能通过范畴的先验含义才可能。然而,这样的范畴又是怎样给感性形象赋予含义的呢?这又只能通过想象力才可能。事实上,无法在a.统觉及范畴在感性材料上的运用以及b.想象力的实际作用之间画出截然的界限,二者毋宁是彼此胶结的,也就是说,先验想象力不能仅仅是感性的,且也必须是一种知性能力,不仅是接受性的能力,也是主动性的能力。只有这样,它才能处于范畴经验运用之可能规定的根据地位上。它因此一方面关系到普遍必然的主体性条件,关系到“我思”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先验想象力也关系到一种客观的实在效用,这种效用不再体现为主观的时间图像,而体现为客观的时间图型。图型是对流动的诸图像的概念性萃取,是烙印在一切时间点上的普遍性的“总像”(Monogramm),它在较低的层面上作为感性概念的图形,将概念图像化;但在更高的层面上,图型还有纯粹知性概念的含义。这一概念图型尽管没有图像表现,也可以运用在现象上去规定和制约感性,并将意识的实在统一性带入现象之中,且不断地唤起它。在这个意义上,图型就是客观实在性的来源,因为它不会随主观时间图像的变化而变化,且只有通过它,一个概念才能获得其与实在对象相关的经验内容。
在康德那里,这样的图型化作用是通过时间得以可能的。这里的时间显然不能是主观经验中不断流逝着的时间,而必须是这条时间图像流的概念,是时间的时间,即时间自身,它也被康德与“实体”及持存性关联起来,以作为因果关联的客观有效性的内在结构概念:“时间自身并不流逝,而是在时间中的可变的特定存在在流逝。那自身不变动而保留着的时间,在现象中与特定存在中不变的东西,即实体相结合,只有在实体那里,且依据此时间,现象的时间顺序和同时存在才被规定下来”。(A144/B183) 这样的时间自身因此才是真正的根据,而时间的变换仅仅是时间自身的样态,这些样态从时间自身那里获得其持存的规则。只有在这里,先验想象力才将“在对时间关系的洞见中的内在意义”确定了下来,将所有当下的现象归摄入一种同一的且可重复的标准之下。也只有借助这种持存的时间,它才能将同一性的规定带入诸现象之中。因为正是时间综合着一切并按特定的规则认识且在自身中保存着一切。先验想象力因此就是设置和重复同一性的能力,而这也正是主体或统握性的“我思”的能力。这种能力所借助的时间,即作为诸时间结构统一性的时间,就既是接受性的,又是主动性的。雅各比非常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8)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S.313.因为这样的时间在康德那里是所有可能应用的基础和所有可能经验到的效用的原因。
这样一种同时作为基础与运用,原因与效果的、设置着同一和可重复的尺度的想象力,被雅各比称为“自因自果”(causa et effectus sui)。此种能力是生产性的,“它是存在的理由,第一因和一切表象的效能”,但同时也是再生产性,“它是认知的理由,第二因,是媒介及其目的”,但二者源初地为一,并共同组建着客观主体。(9)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S.266.通过想象力的同一作用(先验的生产能力)与重复作用(反思能力),客观实在性才被生产出来。这样的实在性因此也就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entia imaginaria)。时间性的想象力(或按雅各比的说法,感性与范畴间的织造工)使得感性摄取的综合成为可能,而其规则来自范畴的运用;但这种运用却正好就是作为知性的想象力的作用,这一作用与作为理性“我思”的作用在本质上相同,它为感性提供着被构想出来的源刺激。由此,在实在性问题上可以看出,“理性……依凭着知性,而知性依凭着想象力,而想象力依凭着感性,而感性复又依凭着作为先天直观能力的想象力,那么这样一种想象力最终又能依凭什么呢?显然只能依凭着虚无!”(10)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S.266.这就是说,一切实在性在这里其实都不过存在于想象出的烟雾中,也就是在那些现象中,“在那里,其实一无显现”。(11)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S.288.所谓真正的、创造性中的实在者其实仅是“一种智性的某物,它先于所有须被把握的东西,只去把握着把握而已”。(12)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S.286.想象力为着自身创造出的某似乎不同于自身的对象物设想,并由此宣称,自己是实在的。除了这一切,在我们的有限自身意识中就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了。(13)W.Metz在他的关于雅各比和康德的相关文章中深化了这一主题。参见W.Metz,Die Objektivität des Wissens,Jacobis Kritik an Kants theoretischer Philosophie,in: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Ein Wendepunkt der geistigen Bildung der Zeit,Hrsg.v.W.Jaeschke u.B.Sandkaulen,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2004,S.10.对于雅各比而言,时间的双重性在这里也构成一种对实在性问题的遮掩而不是回答。已经看到的是时间自身在诸时间中的统一和重复作用,而所有这些时间表象——雅各比将之比喻为海中的波浪——都是时间自身的变样。这就是说,时间自己刺激着自己,它“从一中变成多,又从多复归为一”,(14)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 Werke,S.309.翻来覆去都只有它自己。因而,其实所谓的抵抗力根本没有实在性,因为一切都是时间自己为自己创造出来、想象出来的现象而已,除此之外,只有虚无。一切都是在虚无中被想象出来的,而这种自我变现着的笼罩性的虚无,就是理性统一性自身。而这种看法是否合理,将在对雅各比自己的正面立论进行辨析之后,在下文第三和第四部分会得到简要分析。
三、时间构造原则和时间生成 原则的区分及其意义
雅各比力图在康德哲学内生的虚无主义中看到更高的存在论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了敞现此种维度,是应该更激进走得比康德的虚无主义更远,走向对于根据性的虚无的存在本身的追问,还是反过来,进行虚无主义的批判,让哲学不要像在康德哲学中那样极端?换言之,当康德对根源性的先验想象力进行论说并止步于此的时候,他到底是在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前退缩了,并且没有将对时间性先验想象力的追问贯彻下去,还是其实已经走得过分的远了?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雅各比与后康德哲学的关键不同点。而此种不同对理解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如费希特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雅各比的看法非常明确:康德走得过分遥远。或者,就算康德自己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自发生性的理性体系(它同时也是虚无主义的体系),他也已经将人们送到了门口。在时间问题上,雅各比认为,必须小心在先验想象力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时间自身”:那其实是一种根据性的存在的构造原则(principio compositionis),在其中一切都被同时设定,康德所专心论述的整个综合进程,作为彻头彻尾的自生产过程,从来不离此原则,而在那里其实根本没有实在的时间性起灭,只有无限的自重复的整体结构。但除此之外,雅各比认为,还有另外一种生成原则(principium generationis),它虽然也根据着存在,但并不属于对存在构造本身的追问,而仅是实际存在者链条的开展,在这里,通过我们的有限行动,才有真正的时间感的出现。它并不追问存在构造本身,而仅关注有限存在者的时间链条,关注行动中的实在时间感。(15)F.H.Jacobi,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Friedrich Heinerich Jacobi Werke,S.49ff.这一对双重原则的说明与雅各比的康德批判之间的关系参见W.Metz,Die Objektivität des Wissens,Jacobis Kritik an Kants theoretischer Philosophie,in: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Ein Wendepunkt der geistigen Bildung der Zeit,Hrsg.v.W.Jaeschke u.B.Sandkaulen,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2004,S.10.此外,对雅各比的时间学说的详细研究,以及其与雅各比对“根据”与“原因”进行区分的关系参见B.Sandkaulen,Grund und Ursache.Die Vernunftkritik Jacobis,Wilhelm Fink Verlag,München 2000,S.133-228.我们相信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进行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进行追问,也并不意味着需要解释存在者整体之存在是如何有限化自身的。因为这种对存在在自身中的有限化活动的解释,是将非历时性的根据原则,内在地引入了历时的实际存在者的原因—结果链条,从而必然导致时间性有限存在者的非时间化(永恒化),导致所谓的有限存在不过成为无限根据自身的变样和表现,这也将导致对有限者之为有限者的消灭和虚无主义的产生。而这正是事情的讽刺性所在:我们本来是力图说明时间性的有限存在者之为有限存在者的根据,为此,我们力图追思根据性存在的自身有限化进程,但却因为根据的非时间性,反而使得有限之为有限的实在性被遮蔽和遗忘了。在康德那里,事情就是这样走向极端的。
在这个意义上,雅各比主张区分根据(Grund)与原因(Ursache)。这种区分从布鲁诺的著作《原因、本原与太一》中就已被主张,后来叔本华在《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也再次被重复。但雅各比引入此种区分的目标,在于区分a.根据层面的无时间性构成原则与b.原因-结果层面的时间性生成原则。当因果律被看成是理论知识的最核心规律时,它就是一般现象能够得到恒定认识的根据,因此,在理论科学和认识论上所谈的原因,其实乃是构成性的原因和原则。相反,当因果关系被放在实践哲学的层面而在实际境遇中开展出来的时候,则我的行动乃是其行动后果的原因,但这种原因只能在我的自由感受中被感到,且在实际的行为进程中发生。虽然此种自由因不能被解释,但它可以被相信并且在行动的时间性进程中被察觉。换言之,雅各比主张,时间的生成原则,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而与构造性和生产性的想象力所依赖的“时间自身”的结构相去甚远。这种实践性的时间活动,也不能用康德式的方式,被理解为可以用自然因果律去类比自由作为原因而产生作用的那种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康德,雅各比倾向于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说明。但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休谟认为这种(不包含严格和必然因果律承诺的)因果关系乃是出于人的心灵的习惯,而雅各比却主张某种“决断性的实在论”,他认为实在的有限者的自由此在不能仅仅是一个观念而已,而必须在感觉和理性的统一性中、在自由实践活动的时间性展开被察觉到和追寻到。这种自由此在,就是雅各比在先验存在论(而非康德式的先验逻辑)上所说的“人格”存在。而康德哲学的虚无主义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混淆了根据与原因,构造原则与生成原则,从而将与有限人格者的行动相关的生成性时间,看成是在现象界与构造因果律所需的时间概念具有一致性的东西。雅各比认为,必须从这种被认识论所认定的时间性现象上的一致性中退出去,退到本源的、非认识论的、始终有限时间感受中去,才能真正体验到此在的鲜活存在。
对于雅各比以上区分的意义,需要结合雅各比与康德论争的背景及影响略加评述。当康德将时间作为知识论的最关键建构原则,并将这种建构原则的关键放在时间自身的持存上时,他的确没有办法避免以下嫌疑,即将实在因果关系的发生简单地放到了纯然的自刺激和自生成作用的主体理性结构中加以解释。换言之,他没有有效消除将诸时间的发生和时间本身混同起来的风险,因为时间一方面是ens qua ens perceptum(作为知觉物的物)的实在性保障,另一方面又是ens qua ens cogitans(作为思维物的物)的同一性和可重复性的标准。这两方面的成形都完全依靠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相关项也很难避免被认为是被自我意识所思及和设定的。当二者被视为一体的时候,很明显,时间性的中介进程,就与时间的内在永恒根据成为一回事。这也将导致根据律和中介律的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对于整个后康德哲学来说,都是最为关键的,运用今日的术语,它也可以被称为某种关键性的“曲行论论证”,只不过这种论证所涉及的,其实是纯粹观念的综合和交互解释机制而已,这样一来,不要说外在事物,就连有限者的实在时间感和自由感,也都可能被观念化和结构化,而消融在一片人类知识建构之网中了。正因如此,当代对康德理论哲学的强知识论解读中,出现的情况就是: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变成了知识要素,情感、神圣者或自然生成物,都只有派生性的地位了。
用后康德哲学的发展来验证以上所述,可举费希特为例。费希特显然想要比康德走得更远,走向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论。他为此首先引入了一种远比康德体系更为彻底的观念论体系,并彻底取消了物自身的暧昧地位。他盛赞雅各比为“我们时代最清明的头脑”,正是因为雅各比看到先验想象力与先验统觉为自身预设对象的能力,而费希特则将之进一步引入其“自我”与“非我”的设定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物自身”完全是自我设定出的自身被动性,这种被动性源出于自我无限的主动能力。(16)J.G.Fichte,Zweite Einleitung in die Wissenschaftslehre für Leser,die schon ein philosophisches System haben,in: Fichtes Werke,Auswahl in sechs Bänden,Dritter Band,Hrsg.v.F.Medicus,Verlag von Felix Meiner Verlag in Leipzig,Leipzig seit 1911,S.52ff,S.64ff.在这种不仅止于有限存在者的有限性(Endlichkeit)构成分析,而是深入到了存在(“我在”)活动的有限化(Verendlichung)的哲思中,时间分析也具有了与在康德那里的不同面目,它现在可以与自我(也即一切有限存在者所源自的识在—存在整体的活动)对自身设定进程的反思性直观关联起来,一方面使得这一进程的每一步规定、每一种有限存在者的特定外显图像都得到真正的充实,而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无限进展着的充实活动的特定形式,它又标明着一切理论性哲思的智性目的,即追思正有限化自身的“我思-我在”真实发生性整体。(17)费希特论时间的这两种作用(1.作为自我与非我的设定与反设定活动的实在综合进程及有限物的实在成形进程,2.作为此一现实进程的整体形式及自我有限化活动之复归全然我在的完满理想)。参见J.G.Fichte,Grundriβ des Eigentümlich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 in Rücksicht auf das theoretische Vermögen als Handschrift für seine Zuhörer,in: Fichtes Werke,Auswahl in sechs Bänden,Erster Band,Hrsg.v.F.Medicus,Verlag von Felix Meiner Verlag in Leipzig,Leipzig seit 1911,S.598ff.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超越了康德时间学说所达到的地步,因为康德止步于对在时间中的有限性存在者的分析,而费希特却通过揭示的时间在无限自我中的双重性(有限的实在时间充实与无限的智性时间形式)的统一性,进展到了一种内在于存在(绝对主体存在)追问之中的有限此在发生学内。
四 与海德格尔对康德理解相比较
费希特的这种比康德更为激进的论述当然遭到了雅各比更为激烈的反对。因为在这里,除了无限自我意识性存在的自设定活动之外,根本看不到任何作为实在有限存在者的有限存在者的地位,雅各比在后来著名的《致费希特书》中,明确表达了对此的不满。但费希特的这条道路却是被海德格尔所接续的。令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关于康德的讨论与雅各比有着近乎结构上的一致,但他却对此从来未置一辞。在少数提及雅各比的文本如《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他只是用一句话表示了对雅各比鄙夷而已:虽然雅各比与康德和费希特等争论的核心议题,即是否应该追问时间性的有限存在者的存在根据并由此赢获时间的源初视域,本该是他自己最为关心的。当然,鉴于海德格尔与德国观念论的密切关系,受到雅各比的间接影响,也是可能的。无论如何,重要的在于二者思想的比较,即:虽然二者都同样看到了康德时间理论那里的虚无主义,但究竟是要克服之还是推进之,二者所持见解完全不同。
首先来看雅各比和海德格尔对康德理解的异同。与雅各比将先验对象看作虚无主义病症的表征一样,海德格尔也将之解释为作为“某物”的“虚无”,(18)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122f.但对于后者而言,这种“虚无”却具有关键性的积极意义,此意义在于:人的本源能力正是向着和关联着这种虚无展开和成就自身的,其进程本身就是人的自身有限化的时间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纯粹知性就是先验统觉之统一的源初性“自持”(Sich-vorhalten)(19)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79.,而先验对象与统觉共同地被设置:按照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二者是“同时”处于一种有限存在者的可能经验的发生关系之中。(20)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118ff.在前文论述雅各比时已经十分清楚,先验对象与统觉以“结对”方式出现,而这种“结对”方式来源于主体本身的理性结构需要,因此仅仅是主体以一种自因自果的自身行动建构和编织出来的。但非常不同的是,雅各比试图从这种主体性的存在建构论中脱身,因为说穿了,这种论证的实在基础必定只有依赖主体自身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刺激才能得以成立,而海德格尔——如同费希特曾试着去做的那样——却想要深入到此种主体存在建构的虚无主义基底中去,并认为存在的真正展现恰恰不是在实在论上,而是在此虚无处境之中。换言之,如果康德所许诺的“客观实在性”对于雅各比而言不啻是一场骗局的话,那么它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就是康德哲学面对此在根据的虚无处境而软弱退步的标志:康德想要通过保留诸如“先验对象”这些语词,来遮盖此在处于虚无基底之上且在时间中绽放自身的事实,从而让人们好似还可以安心地生活在某种不可知的实在基础之上似的。但其实,这一基础乃是通过此在的能在才被建构出来的,除此之外,别无实在的基础。
海德格尔之所以将第一康德书视为对《存在与时间》的开启,(21)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234f,S.239.正是因为他从康德的哲学人类学计划之中,看到了更为根本的、根植于有限性存在者之中的存在问题的急迫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费希特一样不满陷于对存在者的“这样那样的、或可能或现实的本质和存在”(22)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223.的有限规定,而不去追问存在自身分环勾连的时间性展开结构的做法。只有在后者的层面上,存在“与”时间的根据性关联才得以阐释。(23)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239ff,S.242.追问存在问题,就必须深入到一种真正时间性的形而上学之中,去思索有限者源自存在整体的自受限的活动。这一活动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从虚无中生成存在者的活动:“存在者的存在只有在这时才根本是可理解的——并且其中潜藏着超越者的至深的有限性——即当此在在其本质的根据中进入虚无的时候。这一进入虚无的自身保持不是什么随意的、任性尝试进行的对虚无的思考,而是一种发生,这一发生处于一切在已然存在者之中的自身现身的基底处,它必须在根据此在的内在可能性而做出的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分析中被得以揭明。”(24)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238,S.283ff.海德格尔由此为形而上学引入了其虚无主义的基调,并走向了他对根据性的“无”的长时间追思。
如上所反复强调的,此种追思必须在此在的时间性绽出状态中得以理解,这就是海德格尔为什么要敏锐地将“统觉”“先验想象力”与“时间”放在一个层面上来处理的原因。(25)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81.同雅各比一样,海德格尔所分析的时间性的“图型—图像”的第一层含义,(26)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96ff就体现在时间作为感性综合机制的意义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在纯粹知性图型上看到任何经验的或数学的图像,但它毕竟会被带入某种“纯粹图像”之中去,因此也仍然是一种“图型—图像”,它并不“高于”感性层次的先验想象力,而是与之同源。(27)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104,S.146f.但还有第二层含义上的“图型—图像”,即不仅是在感性的接受性层面,而且也是在知性的主动性层面出现的“图型—图像”。先验想象力的时间图型兼具这双重的意义,因此,与雅各比一样,海德格尔也主张,作为诸时间结构统一性的时间,就既是接受性的,又是主动性的。(28)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189,192f,194,196.正因如此,海德格尔才十分睿智地说道,尽管理性在康德那里不能被放在时间形式之下,但理性其实也是时间性的,(29)海德格尔之后,H.Holzhey与I.Heidemann也强调过时间的这双重特性,前者强调时间与自身刺激在康德那里的关联以及时间和我思的关系(参见H.Holzhey,Kants Erfahrungsbegriff.Quellengeschichtliche und bedeutungsanalytische Untersuchungen,Schwabe & CO.Verlag,Basel/Stuttgart 1970,S.238-243.),而后者虽然认为我思与时间必须一定程度上拉开距离来看待,但时间在同时具有上述双重性的意义上,与思维是二而一的关系,“思思化时间,时间时化思”(参见I.Heidemann,Spontaneität und Zeitlichkeit.Ein Problem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Klner Universitäts-Verlag,Köln 1958,S.252.)。因为这样的时间在康德那里是智性的,也是先验想象力、范畴的先验含义以及客观实在性的秘密的真正核心,是所有可能应用的基础和所有可能经验到的效用的原因。海德格尔因此判定,它是理解在康德那里Metaphysica generalis(一般形而上学,即存在论)之真正秘密的钥匙,(30)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111,S.127ff.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性的想象力,后来被海德格尔称为作为感性与理性能力之根的“第三种根本能力”,此种能力就是时间性此在通过自身在内部刺激自身而生成自身的能力。按照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自身刺激作用的解释,时间刺激着表象对象的概念并使其生成,换言之,时间就是“让……对象化的内在可能”。(31)M.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Frankfurt 1991,S.188ff.但这种自刺激作用,却是只有在面对此在在世的根据性的虚无时,才能够以一种顶峰状态被见及。这种根据性的虚无,在雅各比看来,就是真正实在基础的欠缺,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本真性此在绽现自身的契机。
雅各比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分析虽然相似,但二人之后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假如雅各比本人知晓海德格尔的学说,那么很可能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已经和费希特以及谢林等人一样走得太远,走向了作为存在论的虚无主义,在其中,时间的非时间性的存在根据,即那种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同时绽放出来的本源时间,将与实在时间内有生有灭的有限存在者序列混淆起来,它们将作为有差异的本源统一和唯一的“存在存在存在”的空虚运动而被给予。此处如果考虑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著名批判,或能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阿多诺将海德格尔视为费希特的同路人,(32)T.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1966,S.72.认为其存在学说乃是与费希特的自我学说一样完全的自生成和自设定的自说自话的空洞学说,缺乏真正的实在性。其论证的关键在于,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论的需求,乃是存在为自身创造出来的空洞需求。阿多诺批评道,海德格尔只代表康德以来的德国观念性哲学的晚期阶段,这一哲学将自身的科学方法作为自因,力图依此创造出一切,却始终亏欠着实在特定存在。海德格尔哲学与他所厌恶的那些名字“一样都属于一种高度发达的信贷体系。每一个概念都是从另一个概念借出来的。这样一种自我生产的悬空状态,是对那种自以为基础稳固的哲学姿态的嘲讽”,(33)T.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1966,S.81f.而当人们要求这样一种对存在之存在的存在的言辞的实际给付的时候,海德格尔就从虚无的小径快速跑开,完全不去管他还欠负着实在有限存在者的东西了。这种批评是否恰当,不能仅在当代哲学领域讨论中被判定,而应该放在哲学的问题史进展中被衡量。在这个意义上,重提雅各比对康德、费希特及后康德哲学其他人物的“虚无主义”批判,在今日就格外地显示出其重要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