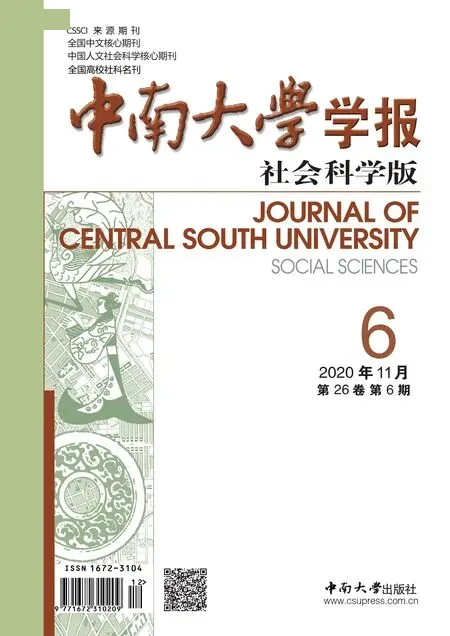正义与辩护——论莱纳·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
刘光斌
正义与辩护——论莱纳·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
刘光斌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西方社会情境的变化产生了不正义,其原有的社会正义原则难以适用,再加上全球化引发的不正义,这些需要正义理论做出新的回应。针对这些问题,莱纳·弗斯特在挖掘英美政治理论传统中的正义理论资源、采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正义批判理论以解决社会中的不正义。他从理性的人具有基本的辩护权利出发,把正义与辩护结合起来,分析了社会中存在的不正义及其权力问题,以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为目标。莱纳·弗斯特把正义批判理论的应用情境从国内扩展到全球,探讨了国内正义与跨国正义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种符合跨国最低限度正义要求的基本的辩护结构,从而深化了正义批判理论研究。莱纳·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对当今社会问题做了理论回应,代表了批判理论当代发展的新态势,推动了对正义批判理论的研究。
莱纳·弗斯特;正义批判理论;辩护
莱纳·弗斯特(Rainer Forst)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旗手,近年来随着弗斯特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他的学术思想基本形成,其学术成就得到了业界的认可,2012年他获得德国的“莱布尼茨奖”。弗斯特一直关注正义问题,并将正义问题置于当前西方社会现实情境和当代正义批判理论交锋中进行考察,他把自己的批判理论视为当代正义批判理论的一种形态,明确“提出了第三种关于正义批判理论的替代理论”[1](310),以区别于霍耐特(Honneth)和弗雷泽(Fraser)的正义批判理论。对弗斯特的研究,国内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力图完整地呈现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认为他从分析社会中的不正义(injustice)出发提出了一种作为辩护(justification)的正义批判理论,了解其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判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了解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关于正义批判理论的争论。
一、正义情境的变化和理论资源
弗斯特一直关注正义主题,在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都能找到有关正义的论述。为什么弗斯特会对正义主题情有独钟呢?原因在于弗斯特是为了从理论上回应已经变化了的正义情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弗斯特敏锐地注意到正义情境的变化,德国社会以及西方社会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正义;二是弗斯特受英美政治理论传统和德法理论传统影响深远,他找到了解释不正义的理论资源,从而构建了辩护理论。正义情境的变化要求在理论上对出现的不正义做出回应。弗斯特提出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以回应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矛盾和不正义,并吸收各种理论资源不断完善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
弗斯特指出:“正义的情境通常首先是不正义的情境,关于正义的论述必须从批判性分析这些不正义中建构。”[2](314−315)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新变化,产生了新的不正义,也提出了新的正义理论诉求,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新变化。现代西方社会不再依据阶级进行划分,身份认同和各种形式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不正义得以呈现,关于性、宗教少数群体遭受歧视、两性关系、少数群体权利等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弗斯特指出:“今天,西方社会中的宗教歧视通常是以世俗的方式来界定的,如性别平等、安全问题和民主决策。”[3](117)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反对不正义的斗争,并要求从理论上对结构压迫、集体身份做出新的解释,从理论上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二是分配不再居于社会正义的中心位置。早期的理论家把分配视为正义的中心,认为正义应该优先关注物品的分配,尤其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配置。弗斯特指出通过再分配政策来减轻不正义是件好事,但它并没有充分改变不正义的情况,正义的最基本原则不是要求分配某些商品的特定模式,相反,它要求以最合理的方式进行分配,这需要把分配和权力关系结合起来。因此,弗斯特认为:“任何对分配正义感兴趣的人都必须首先回答政治问题,即权力问题。”[3](111)不仅如此,还需要从理论上对正义做出多维理论解释,以此回应人们争取除了分配之外的与权力有关的斗争。三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能把正义的运用仅仅限制在领土国的那种有限的政治共同体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和跨国生产不断扩大、美国的单边主义、全球变暖、全球治理、全球贫困、环境恶化等问题突出,导致跨国社会运动兴起。跨国社会运动反映了人们对正义的诉求已经突破以领土国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的范围。这需要正义理论突破其传统适用的领土国政治共同体的范围,并对当代社会存在的不正义进行多层次的理解。正如弗斯特所说,“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理解不再只存在于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形式”[3](120)。他认为对正义的分析应该适用当地的、国家的、地区的和全球的具体情境,因此,“正义的情境总是一种具体的辩护情境”[2](314)。
弗斯特为正义辩护的理论主要受到英美政治理论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首先,英美政治理论传统对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影响较大,并促使他直接参与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正义理论争论中。罗尔斯(Rawls)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对于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认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不平等地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正义论》的出版标志着美国规范主义政治学说和道德哲学的复兴,一度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广泛而又持续的学术影响。围绕正义主题以及“正当与善”关系的争论,西方社会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著名的学者诸如诺齐克(Nozick)、桑德尔(Sandel)、麦金太尔(MacIntyre)、金里卡(Kymlicka)、泰勒(Taylor)、沃尔泽(Walzer)等人都参与了这场争论,使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得以持续发酵。弗斯特对正义问题的关注明显受到英美政治传统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就直接讨论了英美学者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问题上的争论。弗斯特1991至1992年在美国访学期间接受了罗尔斯的指导,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弗斯特1993年在哈贝马斯(Habermas)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1994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正义的情境——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一书。在该书中他吸收了罗尔斯正义论的许多观点,认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安排应该体现公正等,并关注到围绕罗尔斯正义理论展开的理论争论。他不仅分析了桑德尔、麦金太尔等人与罗尔斯的争论,还指出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实质是“‘情境遗忘’的自由义务论与‘情境迷恋’的社群主义理论之争”[4](5)。弗斯特指出两者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正义的情境问题,他认为自由主义存在无视具体情境的缺陷,社群主义存在沉湎于具体情境的缺陷。在他看来,两种政治传统各执一端都不能解释正义规范既内在于情境又超越情境的问题。弗斯特认为必须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关于“正当与善”的问题置于具体情境中进行考察,要求人们在具体情境中提供辩护理由。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及其当代发展对弗斯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弗斯特明确表明自己的批判理论目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目标是一致的。弗斯特指出阿多诺(Adorno)等第一代学者在确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贡献,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实现了“哲学和社会学传统的综合”[3](107),代表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强调霍耐特争取为承认而斗争的范式再次实现了批判理论的变革。弗斯特认为他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对“辩护关系”[3](107)的批判,并指出尽管批判理论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都试图分析阻止社会合理秩序形成的原因。(2)弗斯特使用了批判理论方法,批判性地审视理性概念的“非理性”及其支持统治的方面。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及其代表的统治现象进行批判,之后哈贝马斯揭示了交往理性代表的规范性潜力的一面。霍耐特认为:“虽然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性概念,但它们最终都归结为同一个观点——也就是说,转向一种自由的合作实践不应该来自情感纽带、成员关系或赞同,而是来自理性的洞察力。”[5](28)弗斯特接受了霍耐特的观点,他认为批判理论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属于历史地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反思形式”[6](7),这种理性代表着一种解放力量。批判理论必须对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保持批判立场,并且同样能够以反身或自我批判的方式提供批判的标准。弗斯特认为,为了避免工具理性概念,必须从话语辩护的意义上理解“理性”,这意味着理性不仅成为规范辩护的问题,而且表明获得辩护的规范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3)弗斯特明确提到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对他的正义批判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事实上,弗斯特的辩护理论继承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他接受了哈贝马斯关于主体间的关系、平等参与对话等观点。在与霍耐特关于正义批判理论的对话中,他明确提出了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第三代批判理论对弗斯特影响较大。弗斯特明确提到他把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看成是其分析正义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工具”[3](109),“我试图将话语理论和承认理论整合到辩护范式中”[3](108)。可见,弗斯特坚持了批判理论的目标,从理性的思考出发,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中构建了他的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
弗斯特认为英美政治传统和欧陆哲学之间虽然存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但仍然是可以对话的。他说:“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些观点中最有成效的仍然是对话,无论是罗尔斯学派、哈贝马斯学派、阿伦特学派还是福柯学派。尤其是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把最好的批判工具结合起来。”[3](116)从对话的层面看,如果说英美政治传统促使弗斯特关注正义问题的话,那么当代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对他产生了直接影响,尤其是批判理论为弗斯特提供了方法论,也就是弗斯特所说的“法兰克福学派工具”[3](109)。总之,弗斯特在立足西方社会现实正义情境的基础上把批判理论与正义主题结合起来,从最初对英美正义观点的阐释和正义理论的评析,转向采用批判理论方法提出并完善自己独具特色的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
二、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
弗斯特把自己的批判理论视为正义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旨趣一样,意在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他指出:“批判理论探讨的是一种理性的形式,一种处于历史地位的、正常的、正当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公正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内部(或外部)存在的权力关系会阻止这样一种秩序的出现?”[7](225)具体来说,弗斯特采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分析社会内部或外部存在的权力关系以探讨公正的社会秩序。
弗斯特主张批判理论方法探讨的是一种理性的形式,他认为“批判理论方法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它避免了这些片面的、非辩证的选 择”[7](226)。从论证方法看,弗斯特采用理性建构主义方法将正义与辩护联系起来,他指出:“鉴于我将理性实践重构为一种建构性的正当性实践,在辩护性平等中建构辩护性,正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这种建构性与辩护性的话语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将正义概念程序化,并以正确的方式将正义与辩护联系起来。”[7](234)弗斯特采用批判理论方法,认为批判原则作为理性的原则构成了正义批判理论的基础。首先,弗斯特认为理性的首要方面是辩护原则。他说:“理性必须在其所有的事业中接受批判,并且不能通过任何禁止来限制批判的自由。”[8](13)弗斯特认为辩护原则构成了理性或实践理性的核心,其中理性的人为了解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次,弗斯特主张保证人们的对话权和辩护权。“理性的存在取决于这种自由,即没有独裁权力,但其主张绝不仅是自由公民的同意,而且是每个公民都必须能够表达自己的保留意见,甚至否决权,并且不退缩。”[8](13)作为理性的人是能自由地提供理由、能够为自己辩护的人,是能够进行主体间对话的人。因此,应该保证每个人都有参与对话的权利,所有参与和服从相关规范的人都必须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必须拥有辩护权,给予所有其他人平等的辩护权利。这种辩护权利对任何不符合辩护要求的规范和做法,对可以相互辩护的规范保留否决的权利。再次,弗斯特提出了符合理性辩护要求的两个标准。理性的人们之间进行辩护,怎样才能判断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呢?弗斯特认为这就需要分析理性辩护所涉及的有效性标准。在他看来,有效性标准是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是相互性标准,它要求提出的主张不能由单方面决定,必须通过辩护被所有人接受,这适用于所有客观性的主张,无论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有效性标准是普遍性标准,它与规范性要求相关,规范要求必须得到每一个理性人的承认、得到每一个理性人的普遍接受,并适用于所有人。有效性标准既是规范正当性的标准,也是规范权威性的标准。
在完成上述方法论的准备工作之后,弗斯特从社会中存在的主要不正义出发开始了正义批判理论的论证。弗斯特认为正义批判理论基于对不正义及其深层根源的全面分析。他指出:“正义的情境通常首先是不正义的情境。”[2](314)这些不正义存在多种表现形式,比如经济上的剥削和剥夺、文化承认的缺乏等都可以看成是不正义的表现形式。面对这些不正义,现有的正义批判理论者提出了各自的方案,比如,弗雷泽主张通过再分配解决经济不平等,霍耐特主张通过争取主体间的承认来实现正义要求。弗斯特认为极端的不平等和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支配和剥削体系的结果,仅仅关注分配正义是不够的,因为存在把人变成仅仅是物品的索取者和接受者而不是要求以合理方式进行分配的参与者的问题。在他看来,正义要求分配以合理的方式进行,所有受到影响的人们能够恰当地参与到分配过程之中,并有机会影响分配的结果。弗斯特承认“错误承认”是不正义的现象,但他认为错误承认不仅表现为人们不能获得主体间的承认,而且表现为不能在相互性和普遍性上得到证明。与上述两种解决不正义的方案不同,弗斯特主张把不正义与权力结合起来,不正义首先是权力引起的不正义,权力的行使必须获得有效辩护,从而把正义与辩护结合起来。
弗斯特明确指出正义的首要问题是权力的问题。他说:“要推翻一个复杂的不公正体系,我们需要从第一个公正问题开始:权力分配问题。因此,权力是所有商品中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元善(metagood)。如果你不改变权力系统,你就不会真正改变不正义的状况。”[8](248)他认为不正义与统治密切相关,专断的统治是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统治,没有正当的理由,人们反抗不正义时,必须反对这种统治的形式。由此,他认为政治和社会正义的首要问题是权力问题。弗斯特探讨了阻止公正社会秩序产生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的行使要有正当的理由,也就是说,必须把权力与辩护结合起来。“如果你愿意,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内部的辩护关系。权力,被理解为个人有效的‘辩护权’,是更高层次的正义之善:它要求和提供辩护权以及拒绝虚假合法性的‘辩护权’。这相当于在关于正义的辩论中主张‘政治转向’,并主张将正义批判理论作为辩护关系的批判。”[9](45)权力必须得到辩护,是弗斯特为解决不正义问题提供的方案。他说:“从现在开始,从我们所处的权力关系开始,但它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提出了解放的问题。”[7](226)这也意味着必须为人们的基本辩护权利提供制度安排。关于权力问题是正义的首要问题的说法也意味着社会基本结构必须获得辩护理由的支持。
弗斯特认为正义批判理论不仅要着眼于商品分配中的正义,而且要着眼于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的“基本结构”正义。他指出:“政治和社会正义是一个制度基础结构的规范问题,声称是相互性和普遍性有效的。因此,在这样一个框架内有一个最高原则——相互性和普遍性的辩护原则——该框架规定,每一项对商品、权利或自由的推定有效的主张都必须得到辩护,并以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方式得到辩护,其中一方不得向其他方提出其否认的主张,任何一方不得简单地将其理由强加给其他方,而必须以讨论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排除参与方。”[9](44)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任何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重要德性。”[10](1)弗斯特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正义应该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中,他指出正义批判理论的主要目标是使不正义的受害者能够建立一个不再剥夺和侵犯其基本辩护权利的政治结构,这也是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弗斯特指出该基本结构应该符合基本的正义要求和最大的正义要求。“基本正义要求建立合理化证明的基本结构,即其中所有成员都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力来决定他们要生活其下的制度。”[1](313)基本正义要求为每个人的基本辩护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弗斯特还提出:“最大的正义意味着建立充分得到证明的基本结构,即一种基本结构赋予那些公正社会中的公民所不能相互剥夺的权利、生活机会以及各种产品。”[1](313)在最大正义中,人们不会遭受任何结构性的社会不正义,而是过一种真正的、完全融入社会的生活。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基本正义是最大正义的基础。我们将完全不同和相互竞争的安排产生的社会制度称之为公正或公平的,取决于所有受影响的人是否都能以适当的方式参与这些安排,并有足够的机会影响因为这些安排而产生的那些结果。总之,在正义的语境中,批判理论要求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是可以超越辩护的,批判理论是对所有这些制度、规则或实践的批判,只有那些受影响的人自己才能为自己的基本社会结构辩护。
三、从国内正义到跨国正义
根据上述分析,弗斯特采用批判理论方法对理性概念进行重新思考,构建了自己的正义批判理论,将不正义与正义,权力与辩护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着眼于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的“基本结构”的正义。正义的目的是创造合理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要求创造一种基本的正义结构。在弗斯特看来,正义是从对非正义的反思开始的,那么什么才是正义批判理论适用的社会情境呢?弗斯特认为在存在专制统治威胁的地方,在社会环境正在退化或可能退化到统治环境的地方,才是正义的适当场所。他认为地方的、国家的、国际的和全球的领域都能成为正义应用的具体情境,其中他主要研究了国内正义和跨国正义。
在《正义的情境》一书中,弗斯特为了解决“情境遗忘”的自由义务论与‘情境迷恋’的社群主义理论之争,他提出了正义理论既存在情境限制又超越具体情境的主张。弗斯特区分了社会中存在的四种规范情境:伦理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他认为每一类共同体都有相应的规范要求,不能将任何特定共同体绝对化,只有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些情境结合起来的社会才可以称之为公正社会。弗斯特认为正义原则就是一般的得到公平辩护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反映了所有受影响者的利益、要求和价值。“正义理论不能绝对化这些维度中的一个,并据此塑造其他维度;正义通过按照普遍合理的规范实施伦理认同、平等权利、政治成员资格和道德尊重,来维持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在道德尊重的最低标准下,正义承认道德人需要保护、给予他们一般权利、个人自由和政治自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自主地得到辩护的社会基本结构。”[4](240)弗斯特指出只有在具体的道德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情境中,人们的道德身份、法人或公民身份、个人身份和平等身份才能确定下来,它们构成了正义的前提条件。处于正义理论中心的人不仅是道德人、法人、公民,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具有道德上、法律上、政治上的自主的人。人们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为他们自己的权利提供辩护理由,正义理论在考虑这些规范层面时,受具体情境限制又超越情境,而不是将任何特定层面绝对化。弗斯特认为只有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些情境结合起来的社会才可以称之为公正社会,这个社会基本结构得到了合理辩护,能够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11]。
弗斯特后来开始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辩护理论来区分辩论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情境和其中的辩护原则,就可以得出一个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正义情境理论。在弗斯特最初的著作中,他把辩护的情境主要设想为特定共同体和领土国家。在《辩护的权利》一书中,他把正义批判理论的情境从国内情境扩展至全球情境中,把国内正义扩展至跨国正义。弗斯特认为正义要求人们反对统治,批判权力关系,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多重统治的事实。“正义的各种情境——地方、国家、国际和全球——是通过它们所产生的不公正而联系在一起的,正义理论不能对这种相互联系视而不见。”[8](257)多重统治的事实要求人们必须考虑多重情境中的权力关系,因此,只是单一地追求国内公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不合适的。弗斯特认为必须将正义情境从领土国扩展到全球领域,他指出:“除非我们能够现实地、批判地审视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各种复杂的控制关系,否则我们在超越国家边界的正义问题上就不能有所进步。”[12](88)
弗斯特从全球性的不正义角度出发分析跨国正义。如果跨国正义原则的讨论从分析全球情境中的不正义开始的话,那么不正义的情境可以视为一个复杂的权力和统治系统,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地方精英等是这些权力和统治的行使者。从被统治国家的视角来看,人们处于一种多重统治之中,多数情况下,他们被自己的政府、精英或军阀所统治,而这些政府、精英或军阀有可能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全球参与者所统治。弗斯特认为正义必须要求处理好各种层次的统治和权力关系,对不正义的判断不同于对人类需要或不平等的道德判断,因为不正义意味着将不对称的社会关系视为无法辩护的。因此,正义的情境就是人们进行辩护的具体情境。在正义的情境下,社会规范以及它们理应获得辩护的制度和实践对每个受这些规范、制度和实践影响和制约的人都具有普遍有效性,因此,这些辩护标准必须是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标准。弗斯特认为人作为自主行为者受到尊重,有权不受某些对他们来说不合理的行为或制度规范的约束,每个人都有提供辩护理由的权利。
弗斯特认为实现跨国正义的关键是要厘清跨国正义与国内正义的关系。弗斯特指出在一个普遍多元伦理观念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背景下,全球正义应该拥有一个普遍的基础。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公民自己对特定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行自主的政治建构的可能性。这基本上是以权利的道德建构为前提的,权利以适当抽象的形式被视为人权,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其辩护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国内和跨国宽容的基础,同时也标志着其限度。”[13](272)弗斯特认为,如果公民不能从义务论角度被视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就不会尊重他人的辩护权利,那么权利就缺乏规范基础;如果不以相互的和普遍的标准看待辩护权利,那么辩护权利也只能是一种片面的辩护权利。因此,不管是跨国正义还是国内正义,都必须以公民具有符合相互的和普遍的标准的辩护权利为基础。弗斯特指出:“跨国正义理论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辩护权,以结束内外支配的恶性循环,因此,跨国正义理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结合各种正义情境。”[8](259)首先,国内正义中的基本辩护权利为跨国正义理论提供了基础。“由于基本辩护权利是作为具有辩护能力和不可拒绝地要求辩护的自主的道德人而受到尊重的基本道德权利,因此该权利所处的主要情境是影响其他人的道德行为的情境。在这里,根据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标准,辩护原则要求基于不能被合理拒绝的理由采取行动。”[8](261)事实上,只有在国内社会及其基本结构的情境中,公民依据他们在政治社会和秩序中的道德成员地位,作为直接的法律和政治权威与权力的主体,使基本的辩护权利变成了一种基本的政治权利,并基于他们自己的基本利益和要求为自己辩护。其次,如果没有跨国正义的概念,就不能设想一个国内正义目标。弗斯特主要分析了两个理由:(1)将国内正义情境视为排他的和绝对优先的位置,可能导致不公正。例如,在某些国家从与其他国家的不正义关系中获益的情况下,无论是直接政治、军事统治关系,还是经济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都不能把国家内部正义建立在跨国外部不正义的基础上。因此,需要把正义原则范围从国内正义原则扩展成跨国正义原则。(2)从弱势国家的角度来看,在妨碍尝试和争取内部正义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受到跨国情境影响,因而建立国家内部正义是不可能的。
在弗斯特看来,国内正义和跨国正义是相互影响的。为了打破多重内部和外部统治的恶性循环,并在特定国家内和在国际系统中建立政治自治,需要一项最低限度跨国正义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处在多重统治社会中的成员有权合法地要求必要资源,以便在其政治共同体内建立(最低限度)合理的民主秩序,并使该共同体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大致)享有平等地位。”[8](263−264)跨国最低限度正义旨在在国内社会内部和国际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基本的辩护结构,这是克服内部和外部两种相互关联的统治形式的主要途径。确立最低限度正义的目标是改变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全球系统,以便创造条件使各国在或多或少已制度化的决策程序中具有同等的影响力,这些程序的力量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系统并结束对独裁政权的支持。此外,必须在所有社会中实现和保障基本人权,特别是最低限度的社会标准,以便确保公民和精英能够发挥影响,以实现内部民主化和外部民主化,并在最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
四、结语
一是弗斯特回应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弗斯特注意到德国社会以及西方社会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的理论诉求。弗斯特注意到围绕社会不正义产生的斗争形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再分配不再是社会正义的中心。弗斯特认为社会正义的首要问题是权力问题,需要把政治领域的权力问题置于社会正义的优先位置,通过改变不正义的权力系统才能实现社会正义。不仅如此,他还把对不正义及权力统治的思考从国内情境中扩展至全球化情境中,把国内正义扩展至跨国正义。可见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回应了西方社会和全球化中的现实问题并提供了理论方案。
二是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反映了当代批判理论政治伦理转向的新态势。法兰克福学派自哈贝马斯、霍耐特以来,主要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和政治关系,权力、统治、自由与民主已经成为当代批判理论研究的主题,反映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受批判理论的这种影响,弗斯特指出:“我很早就明白,我必须致力于研究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什么是公正的社会,自由意味着什么,等等。”[3](106)可见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与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有学者指出:“他成功地发展了一种反身正义理论,并由此给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新的动力。”[14](212)
三是弗斯特提出了自己的正义批判理论范式。首先,弗斯特积极参与弗雷泽和霍耐特围绕承认和再分配展开的争论。一方面,弗斯特指出通过再分配政策来减轻不正义是件好事,但它没有充分改变不正义的情况,“恕我对弗雷泽不敬,政治维度转变成了‘正义的主人维度’”[1](319)。另一方面,弗斯特认为承认不能解释所有经济不正义,“不正义似乎并不主要与承认问题相联系”[1](315),因此以承认为标准令人生疑,“关于承认的标准是否足以识别合理的正义(或公正承认的)诉求的问题,我有些疑问”[1](315)。其次,弗斯特明确提出了第三种关于正义批判理论的替代理论,即一种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他认为理性的人必须拥有辩护权利且遵循理性辩护要求的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标准。弗斯特指出社会不正义的首要问题是权力问题,即权力的合法性必须获得有效的辩护,一个公正的社会基本结构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中获得辩护,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种获得辩护的基本结构。
当然,弗斯特的正义批判理论也遭到学界批判,反映出其理论的不足。首先,对普遍规范的论证基础的质疑。霍耐特在黑格尔承认传统的基础上,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提出承认规范要求,批判弗斯特从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自主个人出发分析普遍规范的证成,“不能简单地利用普遍共识和互惠共识的标准”[15](416)。其次,在超验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立场上模糊不清。一方面弗斯特认为辩护原则具有普遍规范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立足于具体的社会情境。穆勒(Müller)指出:“这种模糊立场的最深层原因是弗斯特希望避免形而上学的主张,并提出一种完全世俗化的正义理论。”[16](1052)再次,缺乏对权力的物质利益基础的分析。弗斯特主要强调对权力的规范论证,认为权力必须获得合理辩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权力的物质利益基础及其产生的统治效应的分析。可见弗斯特正义批判理论的理论不足已经引起人们反思,并产生了一些争论。可以预见随着弗斯特学术影响力的扩大,围绕弗斯特的学术争论还将进一步扩大,这些需要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1] 凯文·奥尔森. 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 高静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OLSON K.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disputes[M]. Trans. GAO Jingyu.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2] OLSON K.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Nancy fraser debates her critics[M]. UK: Verso, 2008.
[3] BROWNING G, PROKHOVNIK R, DIMOVA- COOKSON M.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ists[M]. UK: Palgrave Macmillan,2012.
[4] FORST R. Contexts of Justice: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M]. Trans. M M J. Farrell.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5] HONNETH A. Pathologies of Reason: On the legacy of critical theory[M]. Trans. Ingram J 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FORST R. Justification and critique: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politics[M]. Trans. CRONIN 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7] BARGU B, BOTTICI C.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Essays in honor of nancy fraser[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8] FORST R. The right to justification: Elements of a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justice[M]. Trans. FLYNN J.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ERMAN E, NÄSSTRÖM S. Political equality in transnational democracy[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0]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M]. Trans. HE Huaiho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8.
[11] 刘光斌. 论哈贝马斯的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理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5): 1−6. LIU Guangbin. On Habermas’ theory of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7, 23(5): 1−6.
[12] BUCKINX B, TREJO-MATHYS J, WALIGORE T. Domination and Global Political Justice: Conceptual,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J].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3] FORST R. Toleration in conflict: Past and present[M]. Trans. CRONI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4] KIPPER KNUT. Contemplating Rainer Forst’sand——Book review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7, 41(1): 207−213.
[15] PETHERBRIDGE D, HONNETH A. Critical essays: With a reply by Axel Honneth[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8.
[16] MÜLLER, SUÁREZ F. Justifying the right to justification: An analysis of Rainer Forst’s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Justice[J].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2013, 39(10): 1049−1068.
Justice and justification: On Rainer Forst’ critical theory of justice
LIU Gu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The changes in western social context have resulted in injustice, its original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are hard to apply, and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injustice, all of which require new responses from justice theo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Forst propose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stice on the basis of excavating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justice in the tradition of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and adopting the method of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fact that rational people have the basic right for justification, he combines justice with justific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justice and power problems in the society, aiming at establishing a just social order. Forst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context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stice from domestic to global,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justice and transnational justice, and constructs a basic defense structure that meet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transnational justice, thus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stice. Forst's critical theory of justice has made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reflected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and promoted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of justice.
Rainer Forst; critical theory of justice; justification
D0
A

1672-3104(2020)06−0033−09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06.004
2019−06−09;
2020−03−2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诺依曼与哈贝马斯法治国理论的比较研究”(18YJC720026)
刘光斌,湖南洞口人,哲学博士,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联系邮箱:liuguangbin2006@163.com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