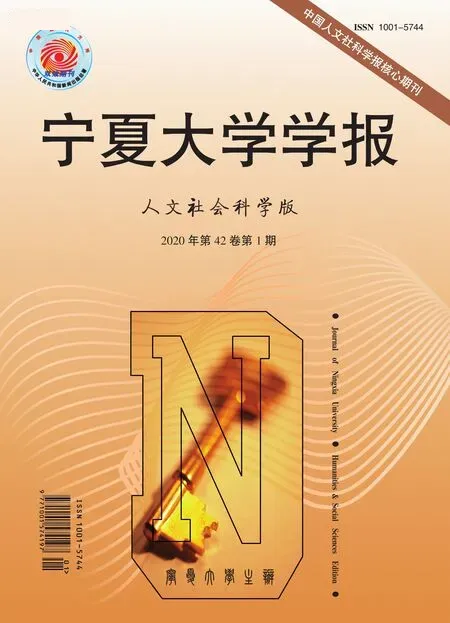宗白华与钱锺书诗画论比较
郑易焜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诗画论在美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上,都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关注。20 世纪,宗白华与钱锺书都受到中国传统旧学与西方哲学、美学影响,亦同将视野投入诗画研究上。宗白华有《唐人诗歌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专论唐诗,又有《诗与画的分界》《中国诗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论诗画关系;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中专论旧诗篇目极多,《七缀集》中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管锥编》中对“谢赫六法”的阐释,于诗画关系有许多新见。通览二人著述可见,二人诗画论确有相近之处,但也有些许不同,甚乃扞格,这和二人的治学方法、经历及教育背景乃至学术兴趣都息息相关。通过对二人诗画论的比较,厘清一些问题,有助于探究两位20 世纪著名的美学、文学研究学者思想上的差异。
一 “谢赫六法”引发的不同阐释
南朝是人物画与山水画勃兴时期,梁代谢赫的《古画品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其不仅品评人物画作,划分品第,还提出了“六法”,被后代画家奉为圭臬。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六法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1]后之学者包括宗白华对“六法”的断句,也主要依据于张彦远的断法。
宗白华在阐释“六法”时,最注重“气韵生动”,以“气韵”“生动”二词连缀,不可分割,他先解释“气韵”,认为“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与和谐”[2]。在此,宗白华将绘画、建筑、园林、雕塑打通一气,指出它们其中都潜伏着“音乐感”。在解释“生动”时,宗白华亦将绘画、雕塑、舞蹈等结合而论,认为它们都体现出“动”的要素,是“虎虎有生气”的,故而要想达到“气韵生动”,需要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将主体的情感移接到客体上去。宗白华给予气韵生动最高的评价,甚至说:“气韵生动,这是绘画创作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的境界,也是绘画批评的主要标准。”[3]
不论宗白华用“节奏与和谐”抑或“虎虎有生气”来解释“气韵生动”的概念内涵,其主要落脚点始终是在“动”字上,这是宗白华文艺美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王德胜认为:“宗白华美学之于艺术问题的把握,根本上就是建立在生命与运动关系的本体性思考基础上。”[4]“动”不但是生命的存在形式,也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宗白华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一文中详细阐明了“动”与中国一切艺术的关系,并以“舞”作为代表:
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天地是舞,是诗(诗者天地之心),是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中国绘画境界的特点建筑在这上面。[5]
“舞”之所以能成为“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便在于它是飞动的,蕴含着生命的律动与节奏,同样,中国画的特点也是在此。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又说:“美与美术……表现的是生命内核,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6]将美术与生命由“动”联系起来,画幅中飞动的物象,使美术作品有区别于简单的几何图像,构成有生命的艺术。
宗白华揭橥“动”是生命的内核,以此建构自己审美批评体系,是故十分推重蕴藏生命力的,具备感人的力量的作品,他在对“骨法用笔”的解释上,便以此作为论说的焦点。如果说“气韵生动”为绘画创作最高境界,那么“骨力”“骨法”便是画作的内在精神。艺术家创造形象,需要把握其内部核心,体现艺术家对创作形象的深切认知与评价。宗白华进一步阐发道:“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出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7]这就要求主体倾入自身情感进行创作,使欣赏者为之感动。在《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一文中宗白华也说:“就是要靠‘骨法用笔’……就是宁出之以泼辣,粗壮,骠悍,超脱,沉郁顿挫,酣畅淋漓,而不要‘谨细’。”[8]画作需要展现出主体的性情与精神,骨力须体现在用笔上,因此,宁肯用富有力量的手笔来创作,体现出“动感”,也不要“谨细”,“谨细”则意味着循矩,失去真我。
然而“动”是需要空间的,宗白华从论“骨法用笔”推及到山水画的画法,也是对“经营位置”的一个阐释。他将中国画与西方画进行对比,尤其提到了“空间”一词,认为中国山水画具有“以大观小”的特点,即不从固定角度刻画山水,而是“飘瞥上下四方”[9],这与西方的“透视”画法有明显区别。宗白华指出:“一件表现生动的艺术品,必然地同时表现空间感。因为一切动作以空间为条件,为间架。”[10]宗白华对于“空间”的论述,在他文章里亦俯拾即是,如《中国诗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宗白华特地拈出了宋画家郭熙的“三远法”与西洋“透视画法”进行对比,提出了三远法不是几何空间,而是艺术空间,其意在说明中国画家心中的宇宙自然意识,心灵是能够“创化”的,只有心灵空静,才能追求无尽的空间。
要言之,“动”与“空间”是宗白华画论乃至审美理论的核心所在。将《易经》中“鼎卦”解为中国空间之象,将革卦解为时间生命之象,体现了宗白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入研究与继承,由此引申到文艺批评上,把“六法”抽绎为表现“生命的动”和“空间”二重属性,也是他审美理论的精度概括。
相较于宗白华,钱锺书对“六法”的阐释,体现他素来不拘惯常之见。开始钱锺书便指出人们历来断句之误: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按当作如此句读标点……脱如彦远所读,每“法”胥以四字俪属而成一词,则“是也”岂须六见乎?[11]
在钱锺书看来,传讹之由当追溯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那里,按照文法,若依张彦远那般断句,“是也”只需出现一次,何须反复出现六次?钱锺书认为“气韵生动”“应物象形”等还能勉强凑合到一处,“骨法用笔”属于四字截搭而成,是万万不能连缀相属的,依此断句乃是“文理不通,固无止境”。
钱锺书将“气韵”与“生动”二词分开,这般就形成了一个判断句,“生动”是解释“气韵”的,而“气韵”仅指画像中的人而言,两词不能截搭一处。钱锺书又追根溯源,提到六朝是人物画的鼎盛时期,山水画还不足以与人物画相抗衡,是以谢赫品评的不过是人物、花鸟画,绝非山水画。即:“故知赫推陆、卫,着眼只在人物,山水草木,匪所思存,‘气韵’仅以品人物画。”[12]为此他还特地引用西方学者对“气韵生动”的翻译进一步论说:
古希腊谈艺,评泊雕刻绘画,最重“活力”和“生气”(enargeia),可以骑驿通邮。旧见西人译“六法”,悠谬如梦寐醉呓,译此法为“具节奏之生命力”(rhythmic vitality)者有之,为“心灵调和因而产生生命之活动”(la consonance de l’esprit engendre le movement de la vie)者有之……其遵奉吾国传讹,以两语截搭,不宜深责也,其强饰不解以为玄解,亦不足怪也,若其睹灯而不悟是火,数典忘祖,则诚堪悯嗤矣。[13]
此一段话中“数典忘祖”之语几乎是直斥。依钱锺书看来,在六朝时,气韵本不是能涵盖一切中国画的,更多地指的是人物画、花鸟画,而谢赫所言的“生动”,本来只是说“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竟一翻变成了“节奏”“心灵调和产生生命活动”。再观宗白华,他不仅仅用“气韵生动”这四字涵盖了几乎一切中国画(尤重山水画),将两个词连缀起来,奉为绘画的最高目标和境界,还将绘画与舞蹈书法结合,着重强调了“节奏”和“动”,这不正是钱锺书所讥讽的西方翻译家,他们以西方审美方法强加到中国文艺美学批评上,最终造成了“睹灯而不悟是火”的局面吗?
由画人物像引出,钱锺书除了对“气韵”进行大段阐释外,还着重申明了自己对“骨法”的理解:
“骨法”之“骨”,非仅指画中人像之骨相,亦隐比画图之构成于人物之形体。画之有“笔”犹体之有“骨”,则不特比画像于真人,抑且径视画法如人之赋形也……诗文评所谓“神韵说”,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之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剌之人。[14]
前文所述,宗白华谈“骨法”所标举的力量、精神,其最终仍落到“动”与“生命”上,相较之下,钱锺书论“骨法”时,则就是将其视作一种用笔之法,全然没有宗白华所强调的“精神”。钱锺书认为五代后画作中出现“没骨法”,乃是直接用彩色作画代替墨笔勾勒,而在六朝时则重视勾勒描骨的画法,这也是为何谢赫强调通过“用笔”来凸显“骨法”。在此,钱锺书欲打通文艺间界限,他认为“骨法”不仅指人物画之“骨相”,乃至画图构于人物之形体,甚至“骨法”可由画联系到诗,诗评亦如画法,都是将作品视为“人”,这是他的一大创见。其实早在钱锺书二十七岁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便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总结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15]。并在下文举出《易·系辞》的“近取诸身”,《文心雕龙》中所说的“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等相论证,最终指出:“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16]这也是“人化”的文艺评论真正的内涵。
钱锺书以历史考证的方法,从时代背景、文艺风气入手力图还原“六法”本来面目,此种严谨实证,旁搜博引,颇带有乾嘉治学的影子。他并不热切追随西方人的见解,而是立足于所获得的证据材料,遵循事物演进的自身逻辑规律来下结论。我们也能看到,他虽批判西人译文的“梦寐醉呓”,但见解却不狭束。从对“六法”评论中引出的文艺批评中共通的“人化”思想,亦体现了钱锺书的治学方法,即各学科之间的贯通融合。在《美的生理学》一文中钱锺书就说在钻研文献之余,“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重”[17]。这种将文艺与生理乃至心理学糅合一处的治学路数,颇新耳目,也扩充了文艺批评的研究范围。
对比钱、宗二人之说,实无对错之分。他们阐释角度,甚至关注范围都有所不同。宗白华品评画重点是在山水画,而钱锺书关注重点却是在人物画。宗白华论画时推崇空间、流动之美,这也是建立在以“中国透视法”为基础的山水画上的,以“高远、深远、平远”为原则,山水画中体现出一种空间的意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宗白华错误理解了谢赫的原意。其实,在六朝时山水画已然开始发展,甚至也出现了不少关于山水画的批评,譬如宗炳的《画山水序》一文主要就是论如何山水布色,得自然之体势的,梁元帝的《山水松石格》谈及运“人情”入山水画中,不过他们的论说更似是一篇闲散小文,倒不类谢赫总结的“六法”如此明确系统。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总结:“道释人物外,以山水名者,则有宗炳、王微,其余名家可考者,至三十余人之多。”[18]亦可见山水画在当时之盛况。
二 以“虚”论诗画的联系与以“实”论诗画区别
中国诗画关系前人已有了足够多的论述,最为有名的当属苏轼“诗画相通论”,《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9]钱锺书与宗白华二人也都对中国诗画间关系有一系列论述,区别在于,宗白华以“虚”“空”为主要着眼点,将中国传统的诗画联系起来,而钱锺书则是以“实”,区别诗与画:
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里,表现着同样的意境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盛唐王、孟派的诗,固多空花水月禅境;北宋词人空中荡漾,绵渺无际;就是南宋词人姜白石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周草窗的“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也能以空虚衬托实景……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中见流行,于流行中见空寂”。[20]
这段话非常鲜明地展现了宗白华审美思想,于最后一句话的两个词语就能见其一斑,即“流行”与“空寂”。“流行”可理解为“动”,“空寂”的“空”代表着空间,前文已经论及这是宗白华审美理论的核心,就在这段话中,结合“流行”“空寂”言之,宗白华主要却是想说明“虚无”。有着足够的空间,又有流动的景象,这种追光摄影,难以捉摸说透的意味,正能将中国画与中国诗统摄一起,宗白华认为这是“唯道集虚,体用不二”在艺术境界上的体现。
在这篇文章中,宗白华多次引古代画家、文学家的评论,甚至引用庄子原文,意在表明中国的艺术境界得自于“虚”“空”。艺术家的创造,源自心灵的造化,在艺术创造之前,心灵是“空”的,所以能容纳万物,发挥各种可能,即苏轼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于宋元的山水花鸟画来说,一切自然景物生命,是要集中于一片虚无缥缈,无边无际上,故而观中国画能见到“宇宙流行”。相比于中国画,西洋画则未免太实一些。举唐诗例子,宗白华有意回避了盛唐边塞诗,中唐写实叙事诗,专门拈出了王孟“空花水月”一般的禅境;举宋词例,北宋词有如苏轼、黄庭坚、周邦彦等,并非空中荡漾,就是南宋词中的辛弃疾、吴文英,一豪壮,一密丽,也绝非能用绵渺无际能概括之。宗白华将其置于一边,主要仍是举姜夔、周密这般具有空灵的词风的词人词作例子,可见他对“虚”“空”有多么偏爱。
宗白华一再地将目光投向抒情诗中的写景之作,这些诗作往往描绘一个如画般的景象,没有表达作者情感的句子,但情感却若隐若现流露其中,宗白华以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实是“充满了诗的气氛和情调”[21]。而宋元山水画里的每一线条,每一形状,也都表现出画家情感的寄寓。画与诗都描绘了景象,但同时艺术性地加工景象,使欣赏者沉浸其中体味作品背后的主人情感,诗与画便通过“虚”“空”建立了关系,宗白华论诗画的联系便在此处。
宗白华以“虚”建立诗画联系,钱锺书则以“实”对诗画加以区别。收于《七缀集》的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在第一节便提到常听说中国诗与画融合一致,这是一个“统一的错觉”。在下文里,他将中国画分为南宗和北宗,并指出“南宗”是中国画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流派,“神韵”恰巧是中国旧诗和旧画所共有的,南宗删繁就简,体现神韵是中国旧画的一个主流,但神韵诗却不是。为此,钱锺书特地举了王维的例子,因为他既是“南宗画”的创始人,又是神韵诗派中的宗师,比如王维的《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仅仅四句二十个字,风神摇曳,悠扬之至,与初唐王绩的诗《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洋洋洒洒二十四句两相对比,所述之事几乎一样,写法却大为不同。可以说,王维“删繁就简”,得于笔墨外的意趣,正与南宗画的道理是相同的,所谓“是同一艺术原理在两门不同艺术里的体现了”[22]。
然而,神韵诗仅仅只是中国旧诗中的一条支流,远没有南宗画在画史中影响深远,中国旧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一种“实”的风格,钱锺书在此精辟论述道: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论画时重视王世贞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论诗时却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因此,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23]
那么何谓“实”?说的即是旧诗中那些说理议论叙事详尽,写景周密安排的作品,这类风格的作品以杜甫诗体现得最为明显,与那些神韵诗作大相径庭。确如钱锺书所说,尽管一些主张“神韵”诗的诗人如袁枚,他们并不觉得杜甫诗有多好,但仍然口不应心地为之附议,因为这样的诗作才是传统诗中的正统。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思想中,忠君爱国、温柔敦厚不仅是评判品行的一条标准,甚至还成为评判诗文的一条标准。早在先秦孔子便以“温柔敦厚”来阐释诗教,正是从为人与作诗两方面来说的。就是写诗欲讽谏,也得“主文而谲谏”,要委婉地进行讽刺,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后来在诗文评论中,从宋代张戒到清代叶燮、沈德潜都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甚至诗的评论也影响到词,清代常州派一再强调的“比兴寄托”“蕴藉”,都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他们非常重视诗的实际内容,而杜甫诗大量的现实篇章,忠君爱国的情怀,都可以成为儒家诗教的“典范”,是以杜诗千百年来被尊崇,旧诗写“实”压倒了写“虚”一头,也就不难理解。
可以看到,钱锺书、宗白华论诗画关系根本差异,即讨论究竟是以“虚”关联二者,还是以“实”将二者彻底区分开。显然,宗白华论诗画大多在二者联系,而钱锺书则着眼于二者之间的区别。
当然,论诗画关系,二人亦有相同之处,譬如对莱辛《拉奥孔》基本问题分析上,二人几乎是一致的。宗白华虽努力建立诗与画的联系,但他也不否认诗与画是有区别的,指出诗与画不能相代且不必相代,毕竟文学艺术与造型艺术表现范围有着较大的差异。宗白华更多地受到了《拉奥孔》观点的影响,例如举王昌龄《初日》一诗和门采尔油画为例,认为诗里面写光景的跳跃,是画作无法表现传达的。即诗歌能表现出时间上的接续性,强调的是“动作”,而画只能截取物象的某一时段,体现的是“形态”。
钱锺书《读拉奥孔》一文,对这些都有阐述,他同样详述了画只能表现“片刻”这一核心问题,即宗白华提到的“最丰满的一刹那”。不过,相比于宗白华围绕着《拉奥孔》中美学原理进行阐释,钱锺书对《拉奥孔》中的观点又有许多扩充之处,他不但详述“富于包孕的片刻”的运用原则,还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在文字艺术里同样可以应用[24]。从而由画引申到文学作品上来,钱锺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回末起波”即是类似手法,又认为莱辛表述其实不够确切,“演变活动”不能够成为划分诗与画的唯一标准。诗歌中往往运用大量的修辞,不但表现出新奇的且与现实相违的景象,还会故意造成色彩上的矛盾,让读者产生错综的幻象,然而却是作者的心理映射,这些画作实难传达,由此,“诗歌的画”转移为“物质的画”便会遇到重重困境。
三 治学思路与审美取向——二人诗画论差异的根本原因
宗白华、钱锺书的诗画论都有深刻见解,就对“谢赫六法”的阐释和对诗画关系的论证来看,二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宗白华深受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与西方哲学思想对比,突出儒道思想在文艺上的重要性,主要源于他对《易经》的深入研究。宗白华强调“生生之为易”,指出事物的变易生化不仅是空间地位上的移动,而是其性质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25]发展绵延于时间,中国的“历律哲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带有先民独特的哲学思辨,与西方“几何空间”“纯粹时间”的哲学体系不同。宗白华为了说明中西哲学的本质差异,以此来推论中国传统审美理念的形成,特用中国古代对“数理”的认识与西方进行对比。《易经》是以数理为基础,但却不是纯粹为了计算,“数”只是为“立象尽意”[26],这就与西方将数学发展为科学判若两途。同时,宗白华吸收了道家“虚静”“空”思想的影响,以老子“大象无形”阐说开去,将“太空”“太虚”“混茫”的形而上学的“道”,视为永恒创化的原理,“道”既是空虚的,又能浑融万物。《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中宗白华写道:“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心灵。”[27]“万境”即为万事万物,“觉心”乃是体察事物一颗空且静的“心”,意即庄子所谓“心止于符”的心斋,我与物两相浑融,这也是中国艺术的境界。静观万象,得“空灵”之境,即“虚”,再由空灵到实,宗白华论“实”总是建立在“虚”上。
另一方面,宗白华又受到西方哲学家影响。他早年去德国留学,系统地学习过哲学、美学课程。十八、十九世纪,随着西方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美学开始渗入理性主义思潮,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哲学,以科学的精神与形而上学、神学分道扬镳,其社会静力和动力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了社会关系。而康德哲学中关于天才和想象力的论述,叔本华论“感性的直观”,直到狄尔泰的“体验美学”,都是非理性的,宗白华显然是从这一路继承而下。由宗白华对欧氏几何学和笛卡儿解析几何分析中可以发现,他认为希腊哲学家建立几何学迈进了一大步,但最终却作茧自缚,哲学因而走向了“纯逻辑”“纯数理”“纯科学化”的路线。欧氏几何论证严密,宗白华在《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笔记中,归纳了欧氏几何的三种证法,任何命题,必经其一种证立后,才得为定理。而对笛卡儿的解析几何,宗白华指出,其中的精髓乃是将图形转化为代数,自此以往,一切图形、图案皆可以用数来表示,即“西学化空间、数为点线”。在字里行间,他隐隐地透露出自己并不欣赏绝对理性主义的倾向。
宗白华正是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非理性”哲学思想中构建自己的“生命美学”体系。他对儒家孔孟、《易经》都有引述,从中探究中国古代的审美理念,并以此作为自己美学理念的根基,其治学方法并非是以考据、训诂、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汉学。建立在“虚空”与“生动”上的审美,使得宗白华对盛唐中表现俊秀明逸境界的诗作十分推崇,他确实不喜中晚唐诗,直言:“晚唐诗坛充满着颓废、堕落及不可救药的暮气”[28]。这是仅就晚唐诗的思想层面来说的。事实上,晚唐诗那些描写衰飒氛围的诗句有时颇为生动传神,味在“咸酸之外”。观宗白华自己的旧诗,极少发表议论,而纯从景色下笔,如“叠叠云岚烟树杪,湾湾流水夕阳中”“春雨苔痕明屐齿,秋风落叶响棋枰”“渚上归舟携冷月,江边野渡逐残梅”[29],诗中的“夕阳”“秋风”“冷月”“残梅”等意象构成一幅萧疏空寂的画面,实与大历及晚唐诗写景之作如出一辙,其诗所写,正可以通过画描绘出来。
相比于宗白华,钱锺书同样有丰富留学经历,他曾赴牛津大学学习英文,并对外文著作有广泛的涉猎。钱锺书回忆了儿诗从父亲读经史古文的经过,谓:“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30]博览经史,再兼通别集,年少时打下的旧学底子,给他日后的治学兴趣、方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诚然,钱锺书的治学方法是“打通”,即打通古今与中外,甚乃各学科的界限,论证问题时往往旁征博引。然而钱锺书终究自称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他的两本代表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皆是以古人“段落评点式”的方法写成,与乾嘉旧学实有一脉相通之意,且看他在《谈艺录》中对黄遵宪的论述:
学人每过信黄公度《杂感》第二首“我手写吾口”一时快意大言,不省手指有巧拙习不习之殊,口齿有敏钝调不调之别……随园每将“性灵”与“学问”对举,至称“学荒翻得性灵出”,即不免割裂之弊……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31]
此段就“我手写吾口”发之,实是强调学问之重。钱锺书对于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说反复辩驳,对袁枚割裂性灵与学问之间关系也很不满意,而认为性灵当从学问之中出,两相浑化而俱忘,是以钱锺书最重于“学”,这也是其承乾嘉治学之精神所在。《谈艺录》开篇即从江西诗派宗主黄庭坚诗补注入手,体现了其对“以学征诗”的重视。尽管他对一些宋诗很不待见,批评宋人“资书为诗”,斥这些作品为“押韵的文件”,但只因这些诗人把编排典故当作写诗,一味追求以学问为诗,作品没有自己的性情。《宋诗选注》中选的宋诗,大多都是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忧国伤民情怀的作品,这种内容充实、学养深厚又颇能表现作家自身特点的诗,即性灵与学问“化而相忘”,方是钱锺书最为推崇的。
而在画论中,米开朗琪罗曾有“画以心而不以手”之论,钱锺书颇不认同,指出大家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正在于其能得手应心,只有“真积力久,学化于才”[32],方能熟能生巧。同样也是一再申明“学”的重要。其所考论往往穷根溯源,牵引西方理论入内,其实正是学力功夫的体现。
宗白华将诗画等量齐观,认为两者间能互相扩充,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钱锺书则表现出对诗歌独特的偏爱,他赞同莱辛所说,诗歌的表现要比绘画广阔。钱氏论诗与画都将“学”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才”与“学”是相辅相成的。
综上所述,宗白华是以他独特的视角来审视诗画,他以“虚”及“生命”“动”等概念来阐释二者联系,体现他对中国哲学深入理解,并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两相调和。钱锺书虽亦有留学经历,但他对于汉学浸润更深,论诗画更多的是将二者放置在其自有的学术史上,加以区别。钱锺书将“学”与“实”看作旧诗的主流,将画亦视为“由学习得”,重在还原考辨而非以艺术审美理论分析,便与宗白华的诗画论有了显著差异。